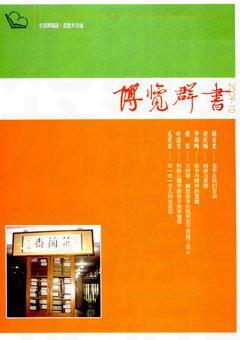80年代影响过我的几本理论书
赵 勇
我认为,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10本书是: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浩然:《艳阳天》(农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9年版。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1989年版。
我从读研究生开始选择文艺学(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起因或许是我在大学阶段已培养出一种理论兴趣。那个阶段虽然读的理论书并不是很多,但有几本也足以让我终生受益。比如,大学四年级时,我买回了丹纳的《艺术哲学》,一读便不忍释手。我不知道究竟是丹纳写得通透,还是傅雷译得漂亮,反正读这本书没有让我意识到理论的艰涩,反而饱尝了阅读快感。但我当时并不清楚丹纳的底细,直到我读研究生,学到了那个“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我才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丹纳会采用那么一种思路和写法。许多年以后我思考中国的体育问题,居然也想到了这本书。因为丹纳分析古希腊人对完美身体的追求,既鞭辟入里又诗意盎然,让人不由得生出追模之心。
上研究生的第一学期,我读到了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那是1988年初,不久就要回家过年了,但我依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本书细读了一遍。放寒假时我回到我教了两年书的学校转悠,有老师问我,这学期读到了什么好书,我脱口说出了杰姆逊的名字。那个年代,杰姆逊还没在中国火起来;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也不明就里。老实说,我读杰姆逊时,对他讲述的东西也是半懂不懂,但是那个活色生香的后现代主义却如同磁铁,牢牢吸引住了我的目光,让我觉得理论原来也可以如此这般地新鲜刺激。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始在中国大热,我也开始一本一本地搜集与后现代主义话题相关的书籍。而杰姆逊这本书则摆在案头,成为我不时翻阅一下温习一番的著作。
我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不光是我的启蒙读物,很可能也是许多学者手中《圣经》一般的爱物。我曾听说过有学者翻烂一本又买一本的故事,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威力。许多年之后我读萨特,记住他说的一句话:“香蕉似乎是刚摘下来的时候味道更好:精神产品亦然,应该就地消费。”他的意思是说,书也要读那些刚刚新鲜出炉的东西。验之于杰姆逊的这本书,此言不虚。如今,这本书依然是专业人士进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殿堂的通道之一,但今天的人们还会感觉到它的强大冲击力吗?我觉得有点悬。
那一时期,我也读了萨特的一些书,但《存在与虚无》太厚,读起来很费劲;《萨特研究》中萨特本人的作品与文章又太少,读起来不过瘾。真正让我受益的是萨特的另一本书——《想象心理学》。那是一本运用现象学的哲学框架去思考心理学问题的美学著作,初读如同天书,但我还是把它啃下来了,且读了不止一两遍。读这本书说起来有些偶然。80年代的山东也有个评论刊物,名叫《文学评论家》,那上面似乎设了个书评栏目。有一天杨守森老师对我说,萨特有本新书刚上市,你是不是可以写文章评它一下。杨老师既是高我一届的大师兄,又代表刊物向我约稿,我自然没有不写之理。于是我立马把这本书买回来,立即开读。直到自认为把这本书差不多读懂了,才写出一篇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当其时也,姜静楠先生也在为《文学评论家》做事,他想让我写一篇比较山东作家与山西作家的文章,我自然又拍着胸脯应承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去了编辑部后被安排在同一期刊物上。我拿到刊物时,见有两篇习作同时面世,自然大喜过望。再一细瞧,写萨特那篇署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肖力”。问其故,才弄清楚事情原委:编辑部害怕一期发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太扎眼,就决定给我起个笔名。而这个笔名起得也并非毫无来由。他们在“赵勇”两字身上各剜两块腱子肉,就做成了所谓的“肖力”。看来一期发两篇还是有好处可捞的,不仅产量上去了,还能混到笔名。赚了。
写萨特的文章虽用笔名发表,似乎是妾身未明,但那本书的核心思想却让我很是受用。尤其是萨特把艺术作品界定成一种“非现实”时,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艺术的真谛。为了把“现实”与“非现实”的关系说清楚,萨特举了个例子。他说:“女人身上的高度的美将那种对她的欲望扼杀掉了。事实上,当我们所赞美的那个非现实的‘她本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同时处在审美的水平与肉体占有水平上的。要对她有所欲望,我们就必须忘掉她是美的,因为欲望也就是沉湎在现存的核心之中,也就是沉湎在那种最偶然的也是荒唐的东西之中。”萨特就是萨特,大概也只有萨特能打出这种比方。——这是我后来又读了萨特的一些传记资料时得出的结论。
80年代是美学大热的年代,我在求书若渴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年代,自然也就成了美学热的俘虏。80年代中后期,美学热似已退潮,但对于我来说,阅读美学书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书、心理学著作仿佛才刚刚开始。当时有几套大型的丛书许多人都不陌生(比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我也加入到搜集、阅读它们的行列,乐此不疲。甘阳说他翻译的《人论》几年之内印了24万册,我当时就认真读过卡西尔的这本书。后来我到北师大求学,听说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当年曾与他的弟子们一道细读过《艺术问题》与《情感与形式》,而苏珊·朗格的这两本书恰好也是我当年仔细琢磨的读物。还有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阐述出来的“异质同构”说,似乎也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成为我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我阅读美学理论的私人记忆中,有两本小书很不起眼,但对我来说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此二书均出自日本学者今道友信之手,名为《关于爱》和《关于美》。《关于爱》主要谈论现代人如何陷入了爱的危机,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因为通过技术力量,现代人可以极度压缩过程,尽快得到他所需要的结果,但这恰恰破坏了爱的基础。如今所谓的“闪婚”、“速配”似乎已证明了今道友信的预言。《关于美》中出现了一个概念——文化体验,那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原始体验的复制性体验,但这种体验似乎已成我们的常态。在西方学者那里,今道友信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而我阅读了更多的西方理论书后,甚至觉得作者有可能是一个“二道贩子”。但在80年代后期,他的书却让我醍醐灌顶。或许正是通过他,我才接通了马尔库塞、本雅明和阿多诺等人的思想。
在美学热的余威中,我还读过一本“反美学”的书——刘东的《西方的丑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此书在1986年就已面世,但我当时却没有买到。三年之后我从图书馆中把它借出来,方才感受到它的震撼。也许是作者的年轻气盛让其写作充满了青春朝气,也许是我曾经苦思冥想的东西忽然有了答案(用接受美学的话说是它满足了我的“期待视野”),总之,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它的冲击之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此之前,我已写过论悲剧“不快感”之类的文章。也接触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但我的思考充其量只是“烧”到了八九十度,而刘东却一下子把它提升到了沸点。我欣喜若狂地摘抄了书中的一些段落,并在读书笔记后面隆重记下了读完这本书的日期:1989年4月5日。很可能是这次阅读印象太深,200i年我逛旧书摊时偶遇此书,立即决定将它买下。2007年,《西方的丑学》落脚北大出版社再版,害得我又买回来一本。
《西方的丑学》不仅让我拥有了一种审丑的眼光,而且似乎也终结了我阅读美学著作的热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美、审美、美学等等,往往是脆弱的。它们经常是一触即溃。
于是,90年代来临之后,我便开始一点一点地挣扎出美学的伏击圈,一路审丑,心情大坏,以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本文编辑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