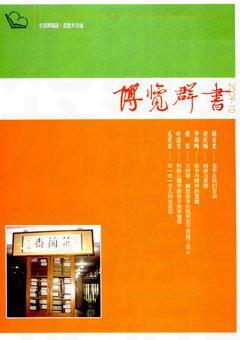我的青少年阅读小史
聂 尔
我认为,60年来影响国人的10本书是: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版。
《毛主席诗词》,毛泽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红岩》,罗文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青春之歌》,杨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水浒全传》,施耐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十万个为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我的少年阅读期刚好与1970年代重叠。9岁时我读了第一本“成人读物”。那本书当时就不晓得名字,因为封面没有了;后来也一直没弄清楚。但故事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这是稍长大知道有一个东北抗日联军后明白的。无论什么样的故事,只要是一个故事,就可以将少年迷住。它并非只将我一个人迷住了,因为我曾将那故事“有偿地”讲给小学三年级班上几乎所有男生,我看见他们的双眼一律放出了迷恋之光。这是第一本读物带来的启示。
随后在整个1970年代,我读了能够到手的几乎所有的书。它们可称为当时的“流行读物”,但却只有少数不是禁书。那些书统统加在一起,应该也就20多本。它们就是1970年代普通下层民间社会的图书存量。我很不愿意罗列那些书的书名,因为它们是我的同代人的共同读物,没有人不知道它们。我们的阅读别无选择,只是我不知道那是无选择的阅读。
阅读是快乐的。偷来的阅读更加快乐。坏书也能带来阅读的快乐,前提是不知道有好书的存在。现在返回头去,只须看一眼,就知道它们确实是坏书无疑。我还真的这样做了,因为太容易了。我在谷歌上敲入一个书名,立刻就看见了它那令人羞愧的样子。
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期的阅读史感到痛惜和愤怒。这种愤怒曾在1970年代末燃烧在我的心头。那是“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我读到刘心武等人的作品和登载在《外国文艺》杂志上的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我朦胧地明白我是在“瞒和骗的文艺”(这就是当时的官方用语)中长大的。我不曾料到,在远离愤怒的任何时候再进行一次认真地回顾,仍能唤回这种愤怒。我说任何时候,是因为我想起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书店里我也曾发现过我的那些少年读物,它们排列成一个不知羞耻的方阵,试图再次欺瞒世人。但我想它到底没有能够成功吧。不过它们化身为影视剧的形象可能已经取得部分的成功。
我是在惊醒于“瞒和骗的文艺”之后进入1980年代的。噩梦已然结束,我的青年时代站立在了1980年代的晨光中。因此,愤怒并非是无止境的。相反,1980年代的阅读是始终伴随着惊喜的。原来,竟然可以沿着文学史的长廊走进无限的阅读之中。从《诗经》《楚辞》到鲁迅巴金,尽管阶级斗争仍被写成文学史发展的主线,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人尚未被允许从僵尸状态中复活过来,但对此前一无所知有现今又处于最饥渴年龄的青年,也已经足够了。何况还有实际早已存在现在又被允许重印的大量外国文学名著,以及当代日新月异的新创作。
北岛的有政治意味的抒情诗,舒婷的爱情诗,顾城童话一般的诗歌,也就是整个艨胧诗派的诗,不顾上一代人反对的声浪,走进了我们热烈的情怀和用于大量摘抄的笔记本上。那种诗的迷醉,除非也用朦胧诗的诗行,否则无法有效和有力地表达出来。我的教授们,他们是被解放到讲台上的先秦文学专家唐诗专家和《红楼梦》专家,他们用困惑的目光看几眼顾城的只有八行的小诗《弧线》,然后又无奈地将它丢至一边。1985年,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一各环揣文学梦的社会青年,而“新时期文学”也已发展到它的十年高潮期的中点——这一年我记得有人曾称其为文学爆炸年,就在这一年我重返母校的时候,我的古典文学教授向我提出的正是关于上述小诗读得懂与“读不懂”的问题。我毫无歉意地承认我是读得懂这首诗的。现在我忍不住将这首诗再抄一遍:
弧线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我因这首诗而见证了1980年代文学史的一个社会化细节,因此它异常触目而美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与1985年相关的阅读记忆还有更多,在这一年及其附近,出现了一批闻所未闻令人震惊的作家和作品,它们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梁》,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一批小说,等等。通过对这些小说的阅读,通过拿这些小说与袁可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对照,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了,中国文学已经迅速走出了“文革”后一度悲壮而荒凉的草莽期。也许这一判断过于乐观了,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感觉。
必须提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书曾在80年代初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的阅读指南。被选入这套书中的许多著名作品的片断,比起后来它们整体出版的样子,曾经给过我们更多的遐想和更激动的神往之忱。这套书不仅是如我这样僻处一隅的文学青年们,同时也是那些后来成为或已经成为大作家的人们,一律奉为写作范本的教科书。当然,写作的范本远不止这一本,除了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还有海明威、福克纳这类因其显著的风格化文体而能够直接引发人们模仿冲动的现代小说家,还有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百年孤独》的魔幻风味据说是本土资源与西方现代文学技巧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我先是在当时的《长篇小说》杂志上糊里糊涂地但却又是心醉神迷地读了《百年孤独》,后来读到莫言的《红高粱》时,立刻就无师自通地认定,他是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启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阅读状态:阅读和写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读的是一样的书。因为读得太少和精神上刚获解放,而导致任何一部新奇之作都指示着一种新的可实践的令人惊叹的文学可能性。
这样的阅读,在进入90年代以后,便不复存在了。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时代的变化再次告诉我们,人的阅读只能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之中进行。
本文编辑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