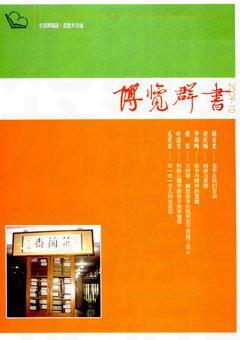听祖父讲名士黄侃趣事(一)
陆 昕
一
黄侃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黄侃9岁时,即每日读经过干字,早慧,人呼为圣童。当时,其父黄云鹄(字翔云)应江宁尊经书院山长之聘讲学,黄侃居家读书。某日,家中资用匮乏,母亲命他写信。黄侃于信中告知家事后,在书末作一诗,云:
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
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黄云鹄曾署四川茶道,故诗中称此。黄云鹄得书后置于案头。一日,黄云鹄密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过访,见诗,诧为奇才,以女许之,即黄侃原配夫人。
黄云鹄得知乡里人呼黄侃为圣童后,即作书诫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治天趣,亦不可忽。”
“借诗文以治天趣”,在那个时代,黄云鹄能注意及此是不易的。天趣不仅培养个性,对黄侃日后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黄侃是年13岁。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在蕲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侃的性格如何向极端发展呢?我的祖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训诂学家陆宗达,曾师从黄侃多年并有着深厚的情谊,师生间几乎无话不谈。祖父有时在家中缅怀往事,说到黄侃时道:
“季刚先生那可是一位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人。
“比如他曾对我说,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
“又有一回,他去考秀才。在考场里住着时,有一天他瞧见另一个考试的人弄只鸭子,架口锅在那里煮。季刚先生一瞧,心里登时来气了,心想,你是赶考来了还是吃鸭子来了。当时他没言声儿也没动作,在一旁冷眼瞧着,看那人忙着添柴烧火。一直等着鸭子熟了就要起锅了,他冷不丁过去,飞起一脚,把人家那鸭子锅给踹翻了,汤汤水水撒了一地。那人急眼了,揪着他要打。季刚先生说,‘甭管你怎么样,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
祖父又曾谈道:“季刚先生孝母是有名的。他跟我聊起过,少年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弄头驴,让他母亲横坐在上头,他牵着,在他家的那个大花园里遛,称为‘孝顺。直到有一天他母亲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说‘儿呀,你别“孝顺”我了,你把我“孝顺”得受不了了。”
我想黄侃的本意大概是相当于今人的饭后散步、消食。不过一位老太太吃完饭就坐在毛驴背上来回颠,大约不会怎么舒坦。黄侃所以如此做,我猜想一是自以为这是孝顺,为母亲消食,二来是要在那个瞧不起他们母子的旧家庭里显示显示,带有某种示威的意思。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音韵学家俞敏生前与我闲谈时,曾论道:“像黄季刚这种庶出的子女,在旧家庭里一般是很受压迫的。所以庶出子女在那种压力下,常常会变作两种性格。一种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甘受压迫求一个温饱。另一种便是拼命反抗,桀骜不驯,使性任气处处叛逆。我觉着黄季刚反封建反得走火入魔了,所以有了那么多常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脾气。”
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黄侃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派出的捕快已经出发,正在途中,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
黄侃返日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章太炎题其后。黄侃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
二
黄侃的个性确实超出常人之外。他最讲究饮食,喜吃美味,人所共知。祖父曾提起,黄侃因参加同盟会在日本流亡时,某日,听说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汤芗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处宴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可他不请自去。用他的原话是,“到那天我自己就去了,一进门,那些人见是我,先吓了一跳,然后又装的挺热乎的。我也不说什么,脱下鞋入座就吃。等吃完了,我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我赶紧跑了。”
黄侃为一代国学大师,还是一位身体力行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老同盟会会员。这都与他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身于饱学的官宦世家,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他少年丧父又因庶出而受歧视,几至失学。这种艰难厄境,反使他得到了两点好处:一是有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反封建意识,尽管这种反抗后来因逐渐变为个人的任性而走火入魔;二是因几乎失学而努力求学。有趣的是,黄侃的革命生涯与其学术活动是同时并行的。黄侃18岁那年,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办文普通学堂,黄侃入学习新学,同学中有宋教仁、查光佛、董用武(即董必武)等。那时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通过宋教仁与黄侃相识,大家因为意气相投往来甚密。
黄侃因其父与张之洞有旧交,去见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见后,认为黄侃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当年(1905)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10年(宣统二年)秋,湖北革命党人准备大举起事,密函促黄侃归国定大计。黄侃当即返国至湖北,分析形势后,他认为时机并未成熟,不宜轻举,并要党人先办好报纸,鼓吹革命,激扬民气。他自己则奔走于鄂皖八县,组织民众,定名为“孝义会”,宣讲民族大义,号召民众反对君主专制。革命党人詹大悲在汉口出版《大江报》。1911年,黄侃到汉口,为《大江报》撰写了一篇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笔名“奇谈”。这篇讨清檄文刊出后震动一时,清政府随即传讯詹大悲、何海鸣二人(詹为《大江报》主笔,何为副主笔,均是革命党人)。后二人被收押,报馆封闭。武昌起义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并发动新军光复汉口,成立汉口军政分府,黄侃亦至军政府主事。不久,清兵南下,革命军势孤,詹大悲等赴上海招募军队,黄侃则回蕲舂发动孝义会,以北上牵制清军。不想,攻打县城计划惊动了当地豪绅。他们请驻防清军前来捕人。黄侃等人躲过清军围捕,辗转赴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急流勇退,不再过问政治。推想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窃,而清政府的一批大僚,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民国官员,不少革命党人受到排斥,有些人如詹大悲等竟被杀害。也有些革命党人忙于争权夺利,个别党
人竟然叛变革命,如黄侃的知友、曾被清政府羁押狱中的胡瑛便投奔袁世凯去了。黄侃觉得政治黑暗,遂生厌恶之心,乃绝计隐退。二是黄侃参加革命本没带什么私心,初衷是推翻中国两千年之君主专制制度。目的既已达到,则可以脱去重负,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1906年(光绪二十二年),孙中山派人将章太炎迎赴日本。章太炎至日本后,即入同盟会,主持《民报》社。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逾万人,纷纷至章太炎先生门下请业。某日,黄侃亦随众人谒拜,登堂入室后,一抬头,忽见壁间悬有章太炎手书,其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虽是东汉戴良语,但章太炎书此悬于壁间,其性情秉性可见。当下黄侃颇以章太炎矜持难近,不愿复往。谁知不久章太炎竟亲自作书邀见黄侃,颇出黄侃意外。
原来章太炎看到了黄侃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后,以为黄侃为天下奇才。因此黄侃乃与章太炎交往日密。时刘师培亦居东京,与黄侃常相往来。第二年秋,黄侃将归国省亲,章太炎知道后即谓之曰:“务学莫如求师,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即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笔者注)治舆地非不精,然查君意实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先生(即清末经学家孙诒让——笔者注)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了,沉吟未语。章太炎此时又说:“如君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后大喜,第二日即执贽至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是日相追随,学问大进。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黄侃在北大教书的情形,冯友兰在《三松堂文集》自序中曾提到“当时北大中文系(门),有一位很叫座的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课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冯友兰肄业于北大中国哲学门——笔者注)。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会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人都高声跟着念,当时成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冯友兰先生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又提到“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许多的轶闻趣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的一所房子中,他们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与吴承仕同为章门弟子,在章太炎的心目中,弟子中有四大金刚。据吴承仕自己称:“这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夏(即钱玄同)及本人,且太炎先生封黄侃为天王。”黄、吴二人交谊很好。
1919年,黄侃应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之邀离南京南下。后又于1926年再赴北平,授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兼中国大学及民国大学课。
吴承仕此时正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为系主任。据杨明德撰“检斋(吴承仕的字)先生在师大”(见《昊承仕同志诞生百年纪念文集》)一文,可知黄侃二次赴平,是应吴承仕之邀,来师大国文系讲授小学。黄侃不负朋友之托,讲课十分卖力,使学生们获益匪浅。杨先生文中所说培养了陆宗达和任化远为关门弟子也是实情。祖父曾亲口对我说,他是在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通过吴检斋认识了季刚先生,并登门求教,结为师徒。至于黄侃与钱玄同间的龃龉,倒也并非空穴来风。我家藏有黄侃与我祖父的手札数十通,其中一通的内容便涉及到与钱的关系。
黄侃于信中说到与钱先生“与彼既经诟淬不便从假”,可知他在师大任教时对钱先生有所责难,应是事实。关于黄、钱二人因何不和,祖父曾依稀对我提起,“大概是有一次在太炎先生处,章、黄、钱三人闲谈。谈话中季刚先生忽然责怪钱不该去搞注音字母,季刚先生大概以为钱喜欢标新立异追逐潮流,钱当然极口辩解,季刚先生本来就比较爱使气,结果俩人越闹越僵,最后钱涨红了脸,大声嚷,‘我就要搞注音字母!我就要搞注音字母!到了儿还是太炎先生给劝开了。”所以黄、钱二人在师大任教时互相不和可能是事实。而黄侃与吴承仕的不和,我的看法是,怕是南学生的误会而起。
三
黄侃天资颖悟,后天刻苦,在学习上与章太炎“转相启发者”多矣,而且在为人行事上有其不可更改的原则,有这样的事可为例证。
黄侃在东京投章太炎门下时,即与刘师培(字申叔)相识,刘师培学识渊博,异乎寻常学者,三人往复论学,甚乐。但刘师培品行较差,初为革命党人,后为清大僚端方收买,遂有背叛行径。辛亥后,袁世凯窃得果实,且谋称帝。刘师培此时又依附袁世凯,成立“筹安会”,为袁称帝大作舆论准备。
1915年秋日,刘师培于京召集知名学者,动员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黄侃与刘师培平素关系最好,邀在首列。黄侃去后,刘师培向众人阐明袁世凯当皇帝之意。一时众学者出乎意外,一则惧袁之淫威,二则碍于刘之情面,面面相觑,计无所出。忽黄侃先生挺身而出,嗔目叫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而去。学界众人亦随之而退。所以,章太炎赞道:“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
刘师培虽然名节不好,但学识甚佳。所以辛亥后,革命党人有人提议惩治刘师培叛徒行径时,章太炎曾为开解之,谓“为中国留读书种子”。黄侃在这点上大概也得了章太炎的遗传,因为他后来看到袁世凯呜呼哀哉后刘师培一落千丈穷居北京时,又生怜悯,乃言与蔡元培,延其于北京大学授课。此后二人时相过从,往复论学,后乃有拜师之事。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经过,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祖父的回忆:
“有一次,季刚先生去刘师培家,见刘先生正与一位北大学生对话,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多半却支支吾吾。学生离去后,季刚先生便问他为什么不认真回答问题。刘先生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随后他便感叹起‘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申叔时患肺结核且已至晚期——笔者注)季刚先生说:‘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先生抚摸着季刚先生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季刚先生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果然正式去拜师,登门受业。当时许多人都很奇怪,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二人在学界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小学上黄甚于刘。但季刚先生却常说他受益于刘先生颇多。(见《量守庐学记·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
另一种是杨伯峻先生的回忆:
“1932年春天,季刚师又全家来到北京(当时改名北平)。我叔父(即杨树达——笔者注)叫我去拜他为师。礼节是,到他家,用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我本不想磕头,但是先叔说:‘季刚学问好的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可。我出于无奈,只好去季刚师家。季刚师一听我去了,便叫到上房里去坐。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上,说明拜师的诚心,跪下去磕了一个头。季刚师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是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谈呢?我猜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从上面所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黄侃有这样几个特点:
头一样是革命党人的气节始终不变,风骨傲然。
第二样是不因人废言。刘师培名节不好,但学问好,故仍为其谋北大之教职。
第三样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黄侃与刘师培本在师友之间,学问各有所精。黄侃自觉经学不如刘师培,即屈己而拜师,并非人人皆能做到的易事。
我家藏有黄侃手写一纸条,夹于其所批点《尔雅义疏》中。纸条上所书为某字之注释,最后两句为“忆昔申叔师亦未明此义,以之问侃,侃未能解。今此字义虽明,而师殁已数年,不觉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