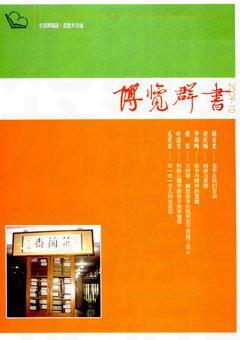关于舒芜的两点事实
秋 水
8月18日,被指为“文坛犹大”的舒芜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旅,终于不需要面对千夫所指而独自远行了。对于生者而言,如何看待这位作家的行为并给今人以警醒,却是一个需要辨析的话题。1952年就主动反戈一击
长期以来,对于舒芜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集中在1955年是舒芜主动交出那些信件为逐步升级的胡风批判提供炮弹,还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以核对原文的名义拿走,之后导致了形势的骤然巨变。然而,学者李辉等人发现,如果说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其合理性在内,那么,他早在1952年的行为,则纯属主动反戈一击。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武汉的《长江日报》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照《讲话》,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为自己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9月25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显然,舒芜的自责与揭露,使胡风十分被动,他被指为“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面临一场公开大批判。9月6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胡风先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5个问题进行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
时过境迁之后,舒芜以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真心想帮助胡风”来为自己辩解。显然,这一理由难以令人信服。此时的舒芜身在南宁,没有人逼迫他写这样夸大其辞、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舒芜的反戈一击显然只是出于政治上“站队”的需要,以免受胡风失势的连累。换言之,如果是真正的帮助,舒芜大可以选择更符合道德伦理、尺度把握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对有恩于自己的胡风在报刊上公开进行诬蔑。另一方面,如果舒芜只是自己“求进步”,他大可以只检讨自己而不连累他人。舒芜的“自我检讨”,在主观上有卖友以求自保,迎合权力执掌者的故意,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踩着胡风、路翎等人上岸”的作用。从后来的事实看,舒芜公开发表了这两篇文章之后,离开了南宁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北京,一时又成了风云人物,可谓得偿所愿。至于他后来难逃反右厄运,却非他本人最初所能预想到的结果。
舒芜1955年的行为在其行为方式上有着一贯的连续性。其时,《人民日报》早在1954年12月16日发表了周扬的宣言和口号《我们必须战斗》。1955年1月,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毛泽东对此做了批判,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历时几个月之后,调子越来越高。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思想界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此时的胡风,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舒芜不仅再度撰文批判胡风搞“宗派主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以核对原文的名义,从他那里拿走了胡风40年代给他的信。这一事件成为了胡风事件的转折点。很快,舒芜“整理”出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毛泽东审阅。于是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公布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成为胡风问题性质起根本变化的标志。对于胡风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5月16日,胡风在家中被捕。接着,全国2100多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相对于1952年的反戈一击,舒芜1955年交出胡风书信,并为《人民日报》公布这些信件做断章取义的“注解”的行为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舒芜以“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为自己辩解是荒唐的。对于当时已经愈演愈烈的“批胡”,舒芜积极参与其中。以其在1952年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政治敏感性,他不可能“幼稚”到不知道自己落井下石的行为将会使胡风雪上加霜。正如复旦大学副教授张业松质问的那样,如果舒芜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那么他想把胡风搞成怎样?
晚年的“反思”轻描淡写
当年加罪胡风元凶之一的周扬,与胡风劫后重逢时,见面便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这旬意味深长的话,显然有着明显的自我开脱的意味。而舒芜晚年尽管有所反思,曾在《回归五四》序言中写到:“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但是,无论是舒芜后来对自己行为的辩解,还是他对待往事的态度,都在有意无意之间避重就轻,推脱责任。没有人把“胡风集团”冤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舒芜个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舒芜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就必须“卖友求荣”,迎合权力,更不意味着他可以开将私人信件用于政治迫害的先河。当人们将这一冤案的发生归咎于制度以及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同时,作为事件的经历者,事后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检验自己的言行。但是,舒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有着切肤之痛的贾植芳、何满子等人一直对其不能原谅。
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浪潮中,巴金也是参与者之一。当时,和胡风已有2 O年深交的巴金“大义灭亲”,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奋勇当先”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胡檄文。30多年以后,巴金在《随想录》中以沉痛的心情重新回顾与胡风的交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并非始作俑者的巴金,表现出了比舒芜更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自责,而直接引发“胡风集团”冤案的舒芜,在事隔多年回首这一往事时,不仅没有对自己进行精神和道德上的严厉拷问,反而为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行为多方辩解,并一直回避为胡风信件做“注解”的详情。尽管他晚年对于自己的过往有一定的反思并提出回归五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舒芜显然缺乏巴金那样的道德自觉。
毫无疑问,舒芜的人性悲剧,乃是严酷的社会形势以及过于严密且高度组织化的制度使然——他自己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即使面对着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个人仍有选择的余地而并非仅仅只有一条路。一旦作出选择,就必须承担这一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后果。在700多人召开文联主席团会议与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声讨胡风,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处罚胡风的决议之后,被舒芜指责在课堂上不积极传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吕荧,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上台发言为胡风辩护并遭到张光年的揪打。如果说舒芜在1952年和1955年的行为别无选择,那么,人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吕荧的行为?在黑与白之间,诚然存在着一个过渡的灰色地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黑白之间并无任何界线可言。在对待胡风的态度上,舒芜和吕荧构成了黑与白的两极,而类似巴金这样的批判者,则是中间的灰色。舒芜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保持沉默并显示出轻描淡写的悔意,他也可以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划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但是,这无法改变他抱着道德负数而终的事实。他和他生前所做的一切,将存留于历史的记载,接受严厉审判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