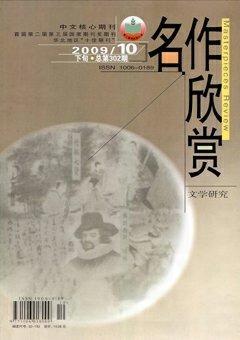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对话色彩探析
刘 彬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巴赫金 对话色彩
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充满对话色彩。具体表现在:1.树立黑人女性主体形象,建构对话主体;2.呼唤—应答模式,唤起对话意向;3.双声性语言和多重叙事模式,营造对话情境;4.文本之间的意指,拓展对话空间。平等的对话精神是对种族性别话语的权威性的修正,表达了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作家的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原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思想家巴赫金认为,“不深究各种言语体裁的对话性及其不同变体,就无法认识各种语言语体,各种思想观念性格调(流派的和世界观的不同格调)和各种社会性格调的复杂性……长篇小说热心于发挥这些基本体裁的潜在能力(主要是对话潜力)”①。美国学者Marilyn·S·Mobley指出,“对话性是美国黑人表意传统固有的特色”②。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梅·G·亨德森(Mae G Herderson)也提出,“黑人女性写作富有特色同时又具有启示意义的就是其对话性”③。托妮·莫里森在重申自己的叙事意图时曾说:“把书写与口述文学结合起来,可以让读者静静地读故事,同时也可以听故事……(在文本中)建构一种可以听得见的对话。”由此看出,莫里森叙事意图之一是在其文本中搭建对话结构。她通过树立对话主体、架构对话框架、营造对话氛围,拓展对话空间来发挥小说的对话潜力,在对话中探求黑人女性了解自我、了解世界、实现身份认同的途径,帮助黑人女性摆脱种族性别的桎梏,赋予她们全面而完整的形象,创立内心是黑人和女性的具有权威性的叙述者,实现了对种族性别文化,对历史现状的思考、探讨与责问。
一、树立黑人女性主体形象,建构对话主体
巴赫金说:“不能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沉默无语的认识客体……一个人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只有他本人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和议论中才能揭示出来……”④这是对人的意识的独立性的重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小说对黑人女性主体身份的塑造是否定和缺席的。黑人女性的境遇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她们发号施令。白人妇女说‘去干这个。白人女孩儿说‘把这个给我拿来。白人男人说‘过来。黑人男人说‘躺下。她们唯一不需要听从命令的是孩子和她们自己。她们忍受着一切……”⑤莫里森深知语言包含着某种政治文化述求,“人与语言的较量也是努力摆脱种族化,性别化束缚的斗争”⑥。因此,她致力于打破黑人女性沉默无语的客体性,赋予她们自我言说的权利和自我定义的能力,建立她们言说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莫里森曾鲜明地表达过赋予黑人女性话语权的决心:“我们不再是伊萨克·笛尼森的‘本质的诸方面,也不是康拉德的无法言说者,我们是自己叙述的主体,见证并参与了自己的经历……我们不是他者。”⑦黑人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就是拥有了某种身份与权利。莫里森以开放性的艺术思维,把黑人女性直接放置在各种事物与问题的冲突的中心,赋予她们声音,并与周围的声音产生碰撞与争辩。
从《最蓝的眼睛》开始莫里森就赋予了黑人女性言说权利。它是黑人女性克劳迪娅讲述的关于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故事。讲述人参与了故事,使得故事具有可信性,而故事的可信性反过来又建立了讲述人的权威性,可信性与权威性恰恰帮助树立了黑人女性的主体性。《所罗门之歌》让黑人女性在黑人男性的故事中发出了有力的声音。派特拉领唱的“所罗门之歌”不仅成为串接故事的主线之一,还是黑人男性寻找自我的文化基石。尽管她的声音遭到来自以小麦肯为代表的性别话语的压制,但它顽强地唱响在小说的始终。
长期以来,主流文学所建构的黑人女性有四种客体化形象:女保姆、女家长、福利母亲和生育机器以及无耻的荡妇和妓女。莫里森颠覆了这种程式化的刻画,塑造出叛逆的女性形象。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塑造了富于同情、宽容、忠诚、反叛的三个妓女芝娜、麦莉、波兰。她们甚至敢让所有的男人包括白人男子置身于她们蔑视的眼光之中,成为她们恼怒的对象,有一次甚至把一个男人从窗口丢了出去,显示出强烈的反抗精神。《秀拉》中的秀拉一改以往文学中那种对白人社会既恨又怕,只能出于恐惧而自卫的黑人形象,成为一个只恨不怕,敢于怀着仇恨而进攻的撒旦,成为“底层”黑人社区居民们心目中倾慕的独立、大胆和自由精神的化身。
通过对黑人女性内心挣扎和冲突的意识的描写,莫里森拉近了读者与黑人女性人物的距离,建立了人物的真实性。正如艾丽斯·沃克说的:“只有当一个故事的所有方面都放在一起时,当它们所有不同的含义形成了一种新的意义时,我才相信内容的真实性。”⑧也就是说,唯有丰富和多面才有人物与事件的可信。小说《宠儿》描绘了主人公塞丝矛盾的内心。她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弑婴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唯一的选择,因而拒绝向不理解她的行为的黑人社区解释;同时,她又时时被一种内疚折磨。这种内疚驱使她在宠儿出现后不断地向她解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应该辩解与无须辩解的念头始终纠缠着她,这种矛盾就像隐蔽的论辩,呈现出对话的泛音。
二、呼唤—应答模式,唤起对话意向
“召唤—应答”模式是非洲口述传统和美国黑人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即说者与听者之间积极平等的对话关系。莫里森曾指出:“如果说我的作品忠实于美国黑人文化中的美学传统的话,那么我必然会让它们有意识地表现其美学形式的各种特征……这些美学特征包括:召唤—回应模式……”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召唤—应答模式揭示了作者、读者、文本之间潜在的多重的互动关系,它不仅是生成与参与性的,还是对话的……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类似于艺术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那种潜在的互动关系。⑨莫里森曾如此阐述呼唤—应答模式的重要性:“黑人牧师布道时让会众开口说话,引导他们加入到自己的布道中。文学也应该慎重地引导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东西并做出回应。听众适时的回应让音乐家的演奏更加激昂。一本书也应有这样的效果。既然我可以自由支配文字符号,我就有责任为读者的参与提供地点和空间。因为,作家或说者和听者之间那种充满情感的互动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⑩
莫里森的小说通过开放式结尾、事物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支离破碎的讲述片段等方式给读者留下大量的阐释空间,引导读者带着自己的阅读体验加入到创作的叙事行为中,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宠儿》中的主人公塞丝的弑婴事件激起了不同声音对它的回忆,叙述、评价,这些声音分为几类:1.主人公塞丝;2.塞丝的亲人及朋友;3.她远离的黑人社区;4.白人群体。这些声音互相补充,读者只有重新拼贴这些零散的独立的叙述与评价,才得以对迷失的故事加以重新组构。《秀拉》中的很多事件也都是点到为止,保持着神秘的状态。比如,秀拉的祖母埃娃截肢的真相,秀拉是否真的眼睁睁地冷漠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火烧死,她为什么这么做?《所罗门之歌》的结尾,“奶人”那纵身一跃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成功起飞还是坠地死去?这些疑惑都需要读者掩卷之余严肃的思索。
召唤—应答模式不仅连接读者和文本,也架起人物与人物、人物与族群间的沟通桥梁。《所罗门之歌》中,派特拉吟唱的“所罗门之歌”既统领情节又召唤自由。这首歌被多次唱起,引起了倾听与被倾听两种强烈的关系行为。第一次在开篇,派特拉目睹保险公司收费员史密斯从医院飞行而唱。围观的人群有几个互相碰碰臂肘,悄悄笑着,其余的人像在听无声电影中起着理解和说明主题的钢琴曲。这首以飞翔为主题的歌俨然是这次飞行的伴奏;第二次在派特拉家,她领唱,她的女儿瑞芭和外孙女夏甲配合着旋律,附和着唱出一个短乐句,三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交响乐。适逢小麦肯经过,歌声勾起了他对田野、野火鸡、长斑点的野兽等有关南方故乡的记忆。这种记忆就是对歌谣中隐含的黑人文化的一种无声的回应;第三次在偏远乡村沙理玛由一群黑人女孩在游戏中唱起。歌声让他突然顿悟。于是,他决定乘她们高歌时用笔把它记录下来。没有纸和笔,就用心听并铭刻在记忆中。这个举动表明在长期的召唤后,他终于对这首黑人文化之歌做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应。
召唤—应答模式与身份认同呈现对应关系。奶人无视他人召唤时正是他困惑于自我身份之时。他自小与黑人族群疏远,与族群中其他人不同。比如,他的一条腿比较短,他喜欢在街上逆着人群走。作为族群的边缘人,他无法捕捉黑人话语中深层内涵。只有学会倾听并且能够回应族群中不同声音时他才获得自我。因为倾听才是了解自我与世界的唯一途径。
三、双声性语言和多重叙事模式,营造对话情境
“双声性的话语同时为两个说话者服务,同时表达两种意图:言说者的直接意图,折射出来的作者意图……存在两个声音,两个意义,两种表述……双声性话语总是带有内在对话性。”{11}“黑人性以西方主流语言的形式出场,即在表面语言符号一致的编码下以差异性的黑人英语表述来体现……”{12}这是一种“以双重声音为基本特征的言说方式”{13}。在戏仿或模仿时,黑人作家在标准英语中添加具有黑人性的语义和表达意图。这种语言“强调‘重新比喻表达法,或是‘重复及差异,或是‘作为对话的转义”{14}。也就是说,话语的直接或原本或字面意义和填加在其上的言外之意或这个话语所折射出来的隐含之意之间,或者说,标准英语和黑人英语之间呈现对话关系。简言之,小说中的黑人用语和叙述者最初的标准英语构成的双重声音之间充满对话。
莫里森“描述了一种具有双重声音的文本,美国黑人读者通过解码读出文本的隐义,而白人读者也认为他们达到了同样的目的”{15}。她在标准英语中添加具有“黑人性”的语义意图和表意方式,实践了黑人英语方言和标准英语的重叠,实现了黑人口述传统和英语书写传统的结合。这首先表现在大量口语化语言中。且看《秀拉》开篇:“本来嘛,这地方原也算不上什么城镇,只不过是个居民点……一个玩笑。一个拿黑鬼开心的玩笑。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只不过是一个拿黑鬼开心的玩笑……也许那里倒真是天堂的底部哩。”{16}这种具有强烈倾诉性的口语化表述意欲在倾诉者和倾听者之间建立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应关系。
同音字替换,重新命名,修正权威话语等是语言的双声性的另一种表现。莫里森小说中很多人名取自《圣经》,但同时又被赋予独特的文本意义,体现了同音同形异义的表意关系。《所罗门之歌》中的派特拉的名字取自《圣经·新约》中的那位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政治家,但派特拉一点也不残忍;相反,她是小说中的道德向导,临死前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爱更多的人。其中的黑人因“慈悲医院”拒绝黑人病人重新命名它为“不慈医院”,“主道干线”被修改为“非医生大街”。《乐园》中黑人小镇黑文镇(Haven)形音近似天堂Heaven,表达了黑人意欲把这块土地建设成天堂的美好愿望。
《最蓝的眼睛》采用“双重的,互相置换的叙事结构”{17}。它体现在:既有克劳迪娅的叙述,也有作者型全知叙述声音的补充和修正;既是佩特拉的故事,也是克劳迪娅的故事,两者对身体美的态度,身份追寻过程,所处家庭环境,最终结局等都形成强烈对比。小说开篇用不同的排版形式引用了一节白人儿童初级读本中对典型的白人家庭的描述。先是标准的语言:“这就是那座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Here is the house. It is green and white. It has a red door)第二段是不规则但勉强能读的句子:“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Here is the houseit is green and whiteit has a red door)第三段则是混乱不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串符号:“Hereisthehouseitisgreenandwhiteithasareddoor.”相同的文字符号不同的排列奠定了标准英语与非标准英语并置的框架,显示对主流话语的刻意修正。这段标准文字在随后的章节中反复出现,每每与紧接而来的或是黑人家庭的贫寒状况或是黑人英语构成的日常对话形成强烈比照。这种对比突出了黑人处于权力话语下忍受的生存的疲惫和心灵的煎熬。
莫里森的创作渐渐倾向多重叙事,即赋予小说中众多声音独立性和充分价值。《乐园》成功地运用了多重叙事,从各个女性叙述者类似记忆的片段化描写来重现个人历史、社会事件、群体经历。修道院的女性康索拉塔、玛维斯、帕拉斯、塞内卡、佳佳等的名字相继被用作第二到第五章的标题,这些章节的故事情节就是她们各自的意识与经历。在叙述结构上,小说明显存在鲁比镇——男性乌托邦社会的象征和女修道院——女性乌托邦社会的象征——两个对立的声音。这些或集体或个人的声音互相弥补、参照、支撑,又各自保持独立性,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主题,即黑人女性身份主体的建立,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共时性的对话关系。
四、文本的表意传统,拓展对话空间
非裔美国文艺评论家小亨利·路易·盖茨证实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存在着表意(signifying)倾向,体现在语言、意象的使用和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文本的表意指“非裔作家对存在于传统中的同一主题的修订和更改”{18},这使得个体创作与前文本产生意义互释,建立了以互文指涉的方式与前文本进行有意无意前后相连的互动语境,从而打破了单个文本自给自足的封闭局面,同一主题跨越历史时空,体现了空间的共时性而不是时间的延续性的创作原则。
“在风格和感受方面,托妮·莫里森是拉尔夫·艾里森的直系后裔……合法的继承人。”{19}艾里森的《无形人》和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是用不同的语篇方式对身份问题的思索。艾里森把身份探讨放置在超越种族之上,他通过一个黑人的经历反映了普遍意义上人的存在与身份问题,他认为“无形”的状态适用于普遍意义上所有的人。“无形人”在地下室经过反省,决定结束蛰伏期,伺机再次回到地面,开始他为身份与自我的奔波之旅。这意味着他的身份困惑依然存在。《所罗门之歌》从种族文化历史追叙的角度继续身份问题的探讨,在认同传统文化对身份确定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莫里森还强调黑人族群的作用。主人公“奶人”最终在南方的黑人族群中确定身份。“奶人”身份的确认俨然是超越时空对《无形人》中遗留的困惑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莫里森对在性别种族话语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群体的身份与归属的思考填补了艾里森在身份问题的探讨中遗留下的空白。表意关系同时延伸到具体人物和章节中。《最蓝的眼睛》中的布莱得拉夫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无形人》中特布拉德的影子。特布拉德(Trueblood)意味着纯正的血统,一个真正的黑人男人,他在梦中与女儿发生性关系,致使女儿怀孕。乱伦的故事在《最蓝的眼睛》中继续上演。布莱得拉夫是唯一爱佩特拉的人。一次醉酒回来,他看见女儿在洗碗。在愧疚激起的强烈父爱的感情包围下,他奸污了她,试图使女儿摆脱无人爱怜的状态。但是,布莱得拉夫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他的行为负责呢?如果说,艾里森仅仅停留在“怎样”这个过程,莫里森则在明处落墨“怎样”,暗处却落笔在“为什么”。通过回顾布莱得拉夫苦难的童年和青少年,莫里森剖析了“为什么”。通过深层原因的追问,读者得以感受到种族压迫给黑人带来的精神压迫和情感的异化。
“不同表述(言语作品)之间的涵义联系,则获得了对话性质(或至少是对话色彩)……只要它们稍微涉及同一个主题(思想),彼此便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对话关系。”{20}莫里森通过对共同主题的继承与超越进入了与他人文本的对话关系中。
结 语
莫里森在作品中赋予黑人女性对话主体的身份,引入具有强烈互动对话色彩的呼唤—应答模式,使用双声性语言和多重叙述模式创建对话条件和环境,通过互文性拓展文本之间的对话空间。“平等对话正是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和策略。”{21}黑人女性努力发出声音,追求平等的对话关系。她们耐心地倾听他者的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个体的和群体的声音并给以积极的回应,与其他声音形成同意或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的对话关系。正是通过创建一个由不同声音共存的多元的理想的对话境界,通过与他者的平等交流对话,黑人女性才得以受到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话语声音的诱惑、威胁、折磨或安抚,其人格也开始逐渐形成,其自我才能发展,才能避免走向个人主义的浪漫化和理想化。而通过对话关系彰显的平等精神消解了种族性别话语的权威性,推动了莫里森笔下众多人物对自我的觉醒和身份的重建。把黑人女性的声音从幕后推到台前,建立黑人女性言说的权威性,彰显黑人女性的平等对话意识,是对种族性别话语的修正,表达了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作家的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本文系2008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美国黑人民俗文化与黑人文学的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课题号:08C381
作者简介:刘彬,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20}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第120页,第318页。
② 《所罗门之歌》新论(New Essays on Song of Soloman),ed.Valerie Smith,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④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③⑦⑧ 周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话意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1),第102页-第107页。
⑤{18} 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陈苏东译,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页,第4页。
⑥{21} 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第154页。
⑨ 嵇敏:《〈娇女〉的“召唤—回应模式”及其黑人美学思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4),第90页-第97页。
⑩ Toni Morrison , “Rootedness: TheAncestorasFoundation,”
in Black Women Writers(1950-1980): A Critical Evaluation,ed. Mari Evan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1984,341.
{11}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Essays, Austin: U. of Texas Press, 1981,324.
{12}{13}{14} 程锡麟:《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第200页,第202页。
{15}{17}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第148页。
{16} 莫里森:《秀拉》,胡允恒译,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58页,第137页-第139页。
{18} 朱小琳:《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第4页。
{19} Charles Johnson, Being Race: Black Writing since 1970,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Press, 1988, 102.
(Dialogic Structure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责任编辑: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