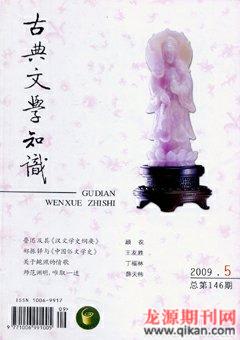祝祷类文体
吴承学 刘湘兰
古人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心存敬畏,当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自然现象时,就要祈求神灵的庇护。因此古人非常重视祭礼,祭祀的范围很广。根据祭祀的时间和对象不同,祭祀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尔雅•释天》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在祭祀过程中,由司祝与神祇进行沟通,代表人意,达之于天,用于祈福禳灾。《周官》记载大祝所作“六辞”,有祠、命、诰、会、祷、诔。古代的人们除向上天神灵祈求庇佑之外,他们还利用神灵的威力对彼此的盟约进行约束,由此产生的文体形式为盟誓文。祝、盟的共同点都是人类向上天神灵祈祷,都要取信于神灵,都是人与神相沟通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将此二类文体并称为“祝盟”。除了祝盟之外,中国古代用于人神交流的文体还有很多,如嘏辞、祝辞、祝香文、冠辞、愿文告、修、祈、报、辟、谒、上梁文、宝瓶文等,皆用于向神灵祝愿祈福,我们把这些文体统称为“祝祷”类文体。祝祷类文体的特点是表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神明某些现实而具体的诉求,是功利性很强的“信仰”。祝祷文体风格庄重严肃,往往采用四六韵文形式。研究祝祷文体,对了解古代文学与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一定价值。本文重点介绍祝文、诅文、盟誓文、玉牒文、斋词、上梁文等文体。
祝文 诅文
祝文是祭司飨神之辞,《说文》云:“祝,祭主赞词者。”《周礼•春官》记载,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郑氏注云:“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祭司主持祭祀时作的祝文,要求文字庄重典雅,不容易写好。刘勰也说“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这些讲究文采修辞的祭司,也是最早掌握文学语言的群体之一。刘勰《文心雕龙•祝盟》又说:“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他把祝文看成是楚辞一些作品的源头。的确,祝文是早期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祝文,非常简单朴素,但其实用色彩与感情色彩都非常强烈。如《礼记•郊特牲》记载的相传为伊耆氏时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人们在祈求大自然的神灵庇佑,风调雨顺,使土不崩坍,水不泛滥,农田不生虫害,不长野草,反映了早期农耕时代人们的质朴而美好的愿望。
任昉《文章缘起》以董仲舒《祝日蚀文》为最早以“祝文”命名并形成独立文体的文章。祝文文体有一个从口头向文字转化的过程。文字形态的祝文,更为注重文采与修辞。所以后代的祝文,文辞趋于繁复典雅。梁江淹《萧太傅东耕祝文》:
敬祝先穑曰:摄提方春,黍稷未华。灼烁发云,昭耀开霞。地煦景暧,山艳水波。侧闻农政,实惟民天。竞秬献岁,务畎上年。有渰疎润,兴雨导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劳。命彼倌人,税于青皋。羽旗衔蕤,雄戟燿毫。呈典缁耦,献礼翠坛。宜民宜稼,克降祈年。愿灵之降,解佩停銮。神之行兮气为,神之坐兮烟为盖。使嘉谷与玄鬯,永争光而无沬哉。(《江文通集》卷三)
这是江淹为萧道成往东郊籍田而作的祝文。此祝文是向谷神祈福,希望这一年来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祝文与“蜡祝辞”相似,但明显讲究文采。
由于祭祀时所用的文辞用于人类与天地山川神祇之间的沟通交流,有些祝文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如“祷文”(或“祈文”)与“祠文”(或“报赛文”),祷文是向神告事求福之文,而祠文则是得福之后,用器物报答神灵庇佑之恩时所用的文辞。这就是郑玄所谓“求福曰祷,得求曰祠”。再如“祝辞”与“嘏辞”,据《礼记•礼运》记载:“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郑注:“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换句话说,祝是主人向神或先祖请求庇佑之文,嘏则是神和先祖向后人致福之文,祝辞与嘏辞是人神交流的文辞。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是以司祝作为中介,传达人神旨意。因为祝辞与嘏辞作文的指向性是对应的,二者所体现的情感特色也相互对应。《礼运》又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之语,郑注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义也。”孔疏曰:“首,犹本也。孝子告神,以孝为首。神告孝子,以慈为首。各本祝嘏之义也。”也就是说,人向神乞求赐福的时候,要本着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孝心;而神灵赐福于人类时,也要体现如父母般的慈爱之情。
与祝文相近的还有不少文体。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总结祝文之辞,还有告、修、祈、报、辟、谒诸体,如“祈雨文”、“祈晴文”、“谢雨文”都属于祝文。此外,还有如用于祭奠山川神祇,祈福禳灾的祭文,如韩愈《潮州祭神文》、白居易《祭庐山文》等。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此类祭文归入“祝文”类,以区别那些专用于丧葬送死之祭文。
如果说祝文用于祈福,诅文则恰恰相反,是用于诅咒仇敌的。费经虞曰:“祝为祷神之辞,又诅祝与咒同,西域之咒实即此也。”(《雅伦》卷八)诅文用于陈述仇敌的罪恶,请神灵降祸于仇敌。王兆芳《文体通释》“诅”条说:“诅者,(俗作“咒”)也,诅也,神加殃,沮事也。郑子曰:谓祝(读为“”)之使沮败。诗曰: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周官》诅祝掌盟诅。主于人罪恶,请神加祸,源出黄帝《祝(读为“”)邪文》(《轩辕记》目),流有秦王《诅楚文》。”《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射杀颍考叔。郑庄公无法讨伐公孙阏,于是在军中用豕、犬、鸡三牲诅之于神,希望神鬼杀之。现存诅文最著名的是《诅楚文》,内容为秦王陈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的罪恶,祈求天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城。
盟誓
盟誓是古代很重要的一种应用文体,是王与诸侯或诸侯之间向神灵发誓共同遵守某种协议时,向神灵陈说的誓辞。盟与誓有区别,先秦时代多用誓,很少用盟。如《穀梁传》言“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刘勰曰:“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文心雕┝•祝盟》)可知夏商周三代之时,常用誓来保证信誉,而且誓的形式很简单,只是口头约定,便可“结言而退”。这样的誓文都很短小,且有简单的格式,多以“所不……者,有如……”行文,带有诅咒发愿的色彩。
盟的出现与兴盛是周王室日趋衰落,诸侯之间彼此缺乏诚信所致,如徐师曾所言:“周衰,人鲜忠信,于是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而盟繁兴,然俄而渝败者多矣。”(《文体明辨》)由于缺乏诚信,诸侯之间的约定必须依靠神灵来约束双方,由此举行杀牲歃血,诅于鬼神的仪式。这种盟的行为包含了誓、诅的内容。盟的形式趋于复杂。在盟誓的仪式中,将盟誓的文辞载之于册,称为载书、载辞,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盟誓文。
后期的盟文内容要丰富得多,如刘勰所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刘勰概括了盟誓文的写作要求和内容要素:先说明盟誓之缘起,以叙危机为主;其次是奖励忠孝之士,表明共存亡之决心;最后请上天神灵作证,发誓诅咒,违誓者必当人神共戮。作者必须要有真诚之心,用恳切之辞,盟誓文才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晋刘琨《与段匹盟文》是盟誓文的代表作品:
天不静晋,难集上邦,四方豪杰,是焉扇动。乃凭陵于诸夏,俾天子播越震荡,罔有攸底;二虏交侵,区夏将冺;神人乏主,苍生无归;百罹备臻,死丧相枕;肌肤甚于锋镝,骸骨暴于草莽;千里无烟火之庐,列城有兵旷之邑。兹所以痛心疾首,仰诉皇穹者也。臣琨蒙国宠灵,叨窃台岳;臣世効忠节,忝荷公辅。大惧丑类猾夏,王旅陨首丧元。古先哲王,贻厥后训。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临之以神明,结之以盟誓。故齐桓会于召陵,而群后加恭;晋文盟于践上,而诸侯滋顺。如臣等介在遐鄙,而与主相去迥辽。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剪夷二寇。有加难于,琨必救;加难于琨,亦如之。缱绻齐契,披布胸怀,书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坠军旅,无其遗育。
行文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刘勰盛赞曰“刘琨铁誓,精贯霏霜”(《文心雕龙•盟誓》)。
誓,不仅用于盟会,也有用于誓师或誓众的,是出征之前的誓言,以激励士气,强化军纪。在《尚书》中就有《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诸篇,可见源头久远。后世如唐德宗《移京西戎兵备关东誓文》等,也是誓师之作。誓师与盟誓虽然同样请神明作证,但目的不同。
玉牒文(附:符命)
王之绩说:“玉牒之名,实始汉武。”(《铁立文起》)吴曾祺也说:“本告天之文,书之于简,而封之,以玉为饰,故名玉牒。”(《文体刍言》)玉牒文是古代帝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其内容往往秘而不宣。《史记•孝武本纪》:“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为何玉牒文显得很神秘呢?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郊禅》记载:“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现存的玉牒文有唐玄宗的《封泰山玉牒文》和宋真宗的《封祀玉牒文》。其文字典雅,篇幅短小,内容先向上天追述祖宗功业,再提出国泰民安的愿望,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因而内容空洞乏味。如宋真宗《封祀玉牒文》:
维大宋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启运大同,维宋受命。太祖开阶,功成治定。太宗膺图,重熙累盛。粤维冲人,丕承列圣。寅恭奉天,忧劳听政。一纪于兹,四隩来暨。玄贶殊尤,祯符章示。储庆发祥,清净可致。时和年丰,群生咸遂。爰荷顾怀,敢忘继志。佥议大封,聿伸昭事。躬陟乔岳,对越上玄;率礼祗肃,备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绥黎元,懋建皇极;天禄无疆,灵休允迪;万乘其昌,永保纯锡。
封禅之后,帝王将此告天之文藏于盒中,用金泥封之,饰以宝玉,所谓“泥金检玉”、“金泥银绳”,因而名之玉牒文。
符命并不是人神交通的文体,但与玉牒文关系密切,故附于此。符命的原意是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作为文体的符命则是是臣子上书帝王,夸耀帝王功绩,列叙各种祥瑞之物象,盛赞帝王之兴乃是顺应天命的文章。正如柳宗元《贞符》所言,符命意在“推古瑞物以配天命”。也就是说,当某地出现某种祥瑞之物如龙、凤、麒麟时,当时人会认为这是上天在赞颂皇帝的美德,说明皇帝的政权是符合天命的。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元代郝经《续后汉书》认为,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凤凰来仪等皆为祥瑞之事,都是据事而书,并没有推引天地神祇作为符命。所谓符命之说,皆是汉儒附会之言。
除了为阿谀美化帝王而作的符命外,还有讨论封禅仪式的封禅文也属于符命一类。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封禅文是臣子上书帝王讨论封禅之事的文书。现存最早的是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此后又有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邯郸淳《受命述》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皆是推美功德,以为符命;其行文风格都讲究闳衍侈大,铺张华丽。
由于玉牒文是帝王封禅告天之文,人们在讨论玉牒文时,往往要提到封禅文,也有人直接将玉牒文称为封禅文。但是封禅文与玉牒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封禅文是建议君王举行封禅仪式的文书,由大臣撰写。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其临死之前的遗著,是建议汉武帝封禅的文章。而玉牒文则是帝王封禅过程中,向上天祈福的文辞。
斋词
斋词是供斋醮时诵读的文辞,用于释、道宗教仪式。由于宗教仪式多样,各种场合所用的文辞有各自特定的名称,如斋词、愿文、醮辞、赞飨文、叹道文、表(露香)、告牒、解语等等。薛凤昌《文体论》认为这些文体“名虽异,实相同”。从使用目的来看,这些文体都是释、道二教向神灵忏过祈福时所用;从语体而言,这些文体或散行,或骈俪,而以四六文为主。因此为了避免文体分类太过烦琐,本文将这些小文体统归入“斋词”类加以讨论。
斋词虽然只用于宗教仪式,但并不只是佛道中人才能写作斋词。唐宋时期宗教风气很盛,上行下效,当时许多文人都有斋词的创作,欧阳修在《内制集序》一文中说:“今学士所作文书多矣,至于青辞斋文,必用老子浮图之说;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可见当时写作斋辞的风气很盛。
青词为道教特有的文体,是道士上奏天庭、征召神灵的符箓,因为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青词”之名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就已出现,据唐李肇《翰林志》云:“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书,谓之青词。”青词又名“绿章”,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九“朱书御札”条云:“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家科仪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为青词绿章,即为青词,谓以绿纸为表章也。”青词的语言以骈俪为主,要求华丽典雅。内容则不过是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又有称“密词”者,通用于佛教与道教,性质与青词相同,只不过抒写不用绿纸而已。
由于宗教的特殊性,更因为斋词是向神灵忏过祈福之词,较之世俗文体而言,斋词的写作有更严格的规定和禁忌。许多道书对此有所记载,《道藏》收有《道门定制》、《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等道书,对道教文体的写作情况有详细记载。如《道门定制》卷一如此规定“章”的书写:“凡书章北向施案,笔砚悉异,不可使杂用者。闭气书写,不得与人言,字未竟不得放笔。黄素勿令破损、飞落床席地土上。剪裁令幅广一尺二寸,行阔一寸二分,行列一十七字,上空八分,下不通走蚁。”此等规矩之严,令人叹为观止。
上 梁 文
古时工匠建屋上梁时,为求吉利,需要表达一些美好的愿望,他们诵读的祝文就是上梁文。现存最早的上梁文是后魏温子升的《阊阖门上梁祝文》,为四言诗体,与后代上梁文形式不同。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上梁文。自宋以来,上梁文的写作开始增多,一些名家别集中都有上梁文,如王安石有《景灵宫修盖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欧阳修有《醴泉观本观三门上梁文》等,这些上梁文已形成其特有的文体特点。简言之,上梁文皆是首尾用四六文,中间杂以六首三句七言诗,六诗分别以东、西、南、北、上、下为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上梁文每章前冠以“儿郎伟”三字,为上梁文套语,其意思历来有不同说法。宋代楼钥《攻媿集•跋姜氏上梁文稿》认为,其意为儿郎辈,“为关中方言也”,此可备一说。以欧阳修《醴泉观本观三门上梁文》为例:
儿郎伟,我国家膺三灵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垒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内,解辫索以承风。逮先圣之抚临,跻群生于富寿。乃欲追羲轩以并轨,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举旷古难行之礼;瑞应来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云裔露之光,纷纶而杂委;朱草灵芝之秀,焜耀而丛生。爰有神泉,涌兹福地。甘如饮醴,美可蠲疴。湛灵液以渊渟,敞琳宫而崛起。岁时游豫,顺民俗之乐康;栋宇翼严,表京师之壮丽。近以有司不谨,飞焰延灾。皇上爱物推仁,因民所利。顾遗基之岿尔,回圣虑以恻然。爰饬良工,载新有作。损其土木之费,所以宽民;适其奢俭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构此修梁,盍效欢讴,形于善祝。
儿郎伟,抛梁东,危构岹峣彩露中,欲识圣君仁及物,灵源一勺本无穷。
儿郎伟,抛梁西,金碧相辉俯仰迷,万瓦寒光浮瑞露,层檐晩景挂晴蜺。
儿郎伟,抛梁南,善利深功不可谈,但喜斯民无疾疠,谁知灵液有余甘。
儿郎伟,抛梁北,观者如云来九陌,四方万国会京师,有类众星环斗极。
儿郎伟,抛梁上,栋宇规模标大壮,落成行即庆良辰,望幸何时来彩仗。
儿郎伟,抛梁下,祈福为民崇广厦,四时和气致休祥,万国多欢洽朝野。
伏愿:上梁以后,三辰顺轨,百谷丰登,卉服雕题,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为击壤之氓。皇帝万岁,皇帝万岁,皇帝万万岁。
上梁文都是这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内容以祈福,表达美好愿望为主,辞语比较华丽。虽然上梁文是工匠上梁时用来诵读的文辞,但是文人在创作上梁文时,仍然讲究文意与情趣的表达。如文天祥《山中厅屋上梁文》,用集句诗的方式表现山中厅屋之优雅;元代张养浩《绰然亭上梁文》,则流露了一种渴望归隐山林的情趣,这些上梁文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趣味。
古人建屋时所要讲究的礼仪,除上梁文外,还有宝瓶文、上牌文等。据陈绎曾《文筌》,宝瓶文是“圬者镘栋脊之辞”,其文内容、形态与上梁文基本一致,文分四段,首先是破题,其次颂德,再次谈人事,最后陈诗。徐师曾在上梁文一类中还附有上牌文,是上匾额时念的祝文,如今可见的上牌文有宋代王十朋《梅溪集》中的《渊源堂上牌文》,四六行文,以“伏以”起文,“伏愿”结束,中间没有插入诗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