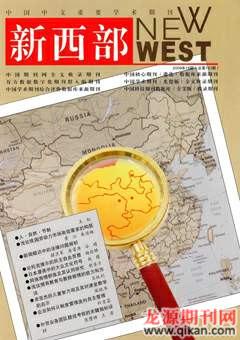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培育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探析
【摘 要】 在法制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应通过重视立法的程序公正、扩大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范围、重视执法公正以及增强法院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措施,以培育公民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法律意识。
【关键词】 法制现代化;公民法律意识;培育途径
纵观我国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历史,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最大的遗憾恐怕在于我们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过分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和法律条文的“现代化”而忽视了法制现代化的实际适用效果。这种对法制现代化的迷恋和狂热很容易让我们的思维“剑走偏锋”。从理论上来讲,任何法制的构建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我们设计现代化法制背离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现状和社会现实,它只能变成一堆废纸。在法制现代化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制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治,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培育法律意识又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培养公民法律意识,主要通过对公民自尊、自治、相互尊重和互相信任等核心要素的刺激、培育和强化,来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对法治的信仰心理,[1]并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形成守法习惯。但是,问题在于: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权就是法、诉讼可耻、重视调解、淡视权利、有罪推定、着重预防等专制传统意识的国家里,[2]在公民的意识中,恐怕最缺乏的就是对法律尊重和信仰。我们能否在人治土壤里播下对法律信仰的种子并让它茁壮成长直至开花结果甚为重要。
如果制定法律的机构不是真正通过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那它制定出来的法律就很难得到人民的尊重与认可,更重要的是,公正的法律必须得到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培育公民法律意识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同步进行。
一、重视立法的程序公正,扩大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范围
人民之所以守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民相信守法可以给他带来利益?为什么相信守法会带来利益?原因在于法就是他自己或委托的、能够代表他利益的人制定的。如果不是这样,有什么让他相信法律是维护他利益的?既然不相信守法能带来“好处”,他会自觉守法吗?当然,我们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他就范。但是,我们都明白,对于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事情,我们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只有当人们对法律产生一种“主人翁”意识,才会真正珍惜并尊重法律。
公正的立法程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威力。一旦法律具有了强大的民意和社会舆论作支持,其本身具有的道德正当性就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一些不愿意遵守的人也会慑于社会道德的压力而不得不服从,这是法庭、监狱和警察等任何国家强制力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对于这样的法律,公然违抗它不仅仅意味着违法者社会诚信形象的丧失,更意味着被社会所抛弃。正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国家就有能力迅速、及时、干净、彻底地粉碎诸如新疆7•5打砸抢严重群体性暴力犯罪事件,将一些顽固到底、与人民为敌的人绳之以法。
目前,重视立法的程序公正,扩大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范围并不是要求人人直接参与立法,而是要求立法机关需要做到如下三点:
1、立法机关要树立立法权有限理念
法治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人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将最大化个人利益作为行为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人民才需要政府。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于人民的需要和政府为人民权利的实现而服务。然而,政府权力不可避免地被少数人掌握,这些人可能以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们造福,也有可能利用人们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公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定义人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以防公权力被滥用而违背人民建立政府的初衷。于是现代国家管理中分权与制衡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在分权与制衡政治思想指引下,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运作模式是:由全体人民或全体人民推选出代表来制定法律;经过民主选举建立起行政机构来执行法律;设立司法机构通过行政诉讼来监督行政机构,以保证行政机构能够严格执行法律。
2、立法机关应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西方国家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先后建立起分权与制衡的国家管理模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虽然不赞成三权分立,但是我们并不否认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于人民的需要和政府为人民权利的实现而服务。政府本身是不能具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更是我们党执政的首要宗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理念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我们认为权力机关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因而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法律和司法机关严格适用法律就是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立法机关是不受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制约的,相反,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受立法机关的监督,向立法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立法机关除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对人民负责之外,无需对任何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负责。因此与议会制至上制度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更强调“人民至上”。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立法机关,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担负更多的责任,更应该自觉主动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人民与自己的关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3、立法机关应充分尊重民意
目前,各级立法机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立法不作为。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空前高涨。从1986年起,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人们的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法律意识也越来越高,权利观念越来越强。立法机关应该充分尊重民意,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给人民一个交代,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央立法机关还是地方立法机关,至目前为止,仍然以沉默的态度对待人民。
二、重视执法公正,确保公民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目前,我国80%的法律要靠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是执法者,如果执法者的社会公信力低,公民法律意识自然不会高。理由很简单:经过民主政治程序制定的法律是反映国家中多数民众意愿、形成国家意志、保护公民权益、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引导社会科学发展的特殊载体,同时更是判断人们行为是与非的重要标准。然而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法律本身并不能产生上述社会效果。法律必须实施才能实现立法目的。而法律的实施不仅要求广大民众守法,更需要执法者本身守法。
1、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严格守法
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代表国家公权力,对外产生的是政府行政公信力。然而,目前个别地方的基层政府行政时,出于种种原因,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压价征用、变相剥夺农民土地而当地党政领导责令当地人民法院采取不予立案、强迫原告撤诉等措施来配合当地搞土地开发、强制拆迁。[3]有的基层政府甚至打出这样的一条招商标语:“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4]“政府在任何地方都是我们最有说服力的教员,不论是好是坏,他的榜样教育着全体人民,如果政府本身成为犯法者,那么它就孕育着对法律的蔑视;它鼓励所有的人各自为法从而助长混乱。”[5]普通公民违法,污染的只是法治的水流,而执法者和司法者犯法,污染的则是法治的水源。
2、提倡行政决策民主
上述行政不法行为,往往源于行政决策的非民主化。而基层政府往往远离中央,甚至远离省政府、市或县政府,上层对其监管力度小,这些基层政府行政官员地方主义思想严重,法律意识不强,为民服务观念淡薄,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不高。加上某些基层政府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纵横交错,容易产生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违法现象,直接损害了基层群众的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人民群众能及时发现但无法控制行政执法违法现象,上层政府想控制,但由于信息和资源有限等原因,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提倡决策民主,扩大人民群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方式:比如,听证会、座谈会等法制化、制度化,不失为一种有效地尝试。
三、增强法院裁判文书说理性,教育和引导公民增强法律意识
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法院则是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同时又应该是最讲道理的地方,法院的判决如果能向当事人讲清道理,就能赢得人民的尊重,消解人民的积怨,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问题。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有力的保障手段,是社会公正的底线。法院公正的司法裁判会使公众信赖和尊崇法律。法院裁判不公正,不仅会毁掉人民对法律的信赖和崇敬,而且会毁掉政府的公信力。司法不公正,人民无法从国家合法权力框架内寻求应有的公平与正义,必然向国家权力以外的社会力量寻求支持或者以自己的力量来反抗社会。 树立司法权威,法院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捍卫法律的尊严。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法院是一个既不掌握利剑也不掌管钱袋的政府部门,它要想赢得人们的信赖,唯一的做法就是讲理。通过裁判文书对社会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最合理的法律阐释,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像“邓玉娇案”中邓玉娇刀刺官员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抑或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对于习水官员的行为,为何构成嫖宿幼女罪而不应该是强奸罪?要依法保障罗彩霞的受教育权,目前究竟存在哪些障碍?“金首饰案”为何不能被称为第二个“许霆案”?“杭州飙车案”中胡斌的行为为何不是涉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法院对这些公民关注的“影响性诉讼”进行裁判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这是司法理性引导和教育民众的绝佳时机,更是树立司法权威性的难得“机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很多法院已经丧失了很多这样树立司法权威的大好机会。
【参考文献】
[1] 徐晓晴.法律意识的实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序言P1-2.
[2]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3.
[3] 陶丰,谢春雷.“浙江法院‘拆迁变法”.载.南方周末,2003-10-9.
[4] 参见中国最牛的标语口号:http://user.qzone.qq.com/229552955/blog/88.2007-8-1日访问.
[5]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1.
【作者简介】
田宏伟(1966-)女,河南方城人,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法学及法学理论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