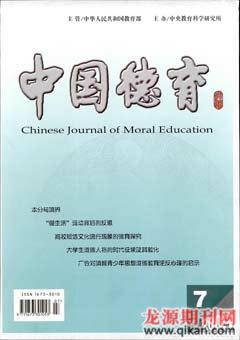论杜威的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
王洪明
从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开始,约翰•杜威的文章和著作中就隐含了他对学校道德教育目的的阐述,如1908年出版的《伦理学》,1909年出版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全面阐释了他的教育理论,许多章节论述了他独具特色的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另外,他在《道德中的三个独立要素》《人性会改变吗》《创造性的民主——我们面临的任务》《关于价值的几个问题》等文献中也对自己的道德教育目的观进行了补充说明。
一、杜威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的理论基础
杜威的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是建立在对过去教育理论的批判、道德教育的心理学和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基础之上的,体现出他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理想、基于经验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和生活道德教育观的特点。“民主”“经验”“生活”是其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的三个核心概念。
杜威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民主共同体”社会理想形态充分体现了他的道德目标,把道德作为民主的基础是杜威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哲学并非从科学或确定的知识出发,而是从道德信念出发,以便能借助各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最佳的知识方法,来表明某种基本的意志态度或道德决断更适合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劝导人们选择这种明智的生活方式。”[1]杜威以“是否符合道德”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此来重新确立民主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评价标准。“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授受关系,总结经验等,民主主义到底还是唯一的方法,使人们能成功的进行我们全体都牵涉在内的实验,人类最伟大的实验——在这共同生活的实验中,每人的生活,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有利的,对自己有利,同时有助于他人的个性之培养。”[2]
任何社会生活方式需要有标准来测量它的价值——“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地参与的利益有多少?和其他团体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什么程度?”[3]93他还认为,以上所提出的标准的两个要素都说明民主主义。“第一要素,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的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地相互影响,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的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恰恰就是民主社会特征。”他解释说,“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3]97 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原则,不再是一种远离生活的观念,也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体的、日常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民主生活方式。
“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形式结合着。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了解经验的性质。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这个意义,用实验这个术语来表达就清楚了。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结合。”“一个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还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他遭受的疼痛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是经验。”[3]153显然,只有当经验能够促进个体的生长时,它才具有教育意义。杜威认为经验对教育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经验本来就是一种主动而又被动的事情,它本来就不是认识的事情;另一方面,估量经验的价值的标准在于能否认识经验所引起的种种关系或连续性。
在这种经验观基础上,杜威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明确区分了“道德观念”和“关于道德的观念”。他认为,凡是能够影响行为,使行为有所改进和改善的观念就是“道德观念”,凡是属于使行为变得更坏的那一类观念就是“不道德观念”;而“关于道德的观念”是直接传授的道德知识,这些观念不能自动地转变为好的品格和好的行为。在杜威看来,“道德观念”来源于经验,是在经验中得到的,而“关于道德的观念”则是一种非亲身获得的符号性信息,是一种直接知识,无法付诸行为。因此,学校道德教育的职责应该是使儿童和青年生动活泼地获得最大数量的观念,使他们成为主动的观念,指导行为的动力,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关于道德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并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学校要完成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需要有三个独立要素:现实生活、教材、方法,并使三者统一于社会生活之中,以实现道德教育社会化的目的。这三方面有着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联系,称之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三位一体”。
在杜威的道德哲学中,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具有道德因素,人们的一切行为选择也都具有道德性。学校道德与社会道德应该是统一的,“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为校内生活的,一套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4]136—158他还指出:“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3]367学校生活社会化是进行学校道德教育的最基本要素,学校应成为一种典型的环境,设置这样的环境以影响成员的智力和道德倾向。儿童在学校里对正当行为所具有的动机及其被判断的标准,应该如同成人在他的广大社会里一样。学校应特别强调让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培养他们的道德品性,如同游泳,只重理论不重实际就犹如不下水学游泳,那是不可能学好的。
“民主”“经验”和“生活”进入了杜威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论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杜威构建了自己的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论体系。
二、杜威的学校道德
教育目的观
1.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普遍目的,学校道德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生长的过程。杜威认为,教育上合乎需要的一切目的和价值,它们自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一切能发展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这种教育塑造一种性格,不但能从事社会所必需的特定的行为,而且对生长所必需的继续不断的重新适应感到兴趣。”[3]378—379他还认为,道德问题是一个生长问题,坚决反对追求任何绝对目的和最终的善,认为生长自身才是唯一的道德的“目的”。
传统道德理论有“内在之物”和“外在之物”之分,以康德为代表的“内在”论者认为道德评价与“人们所得到的行为”无关,而与“人们看不到的行为内在准则有关”;以缪勒为代表“外在”论者提出“最大幸福原则”,人们应当采取能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于是道德评价的对象被放入到“外在”的经验世界之中。杜威认为“内在准则”并非独立于或先于行动,经验中的行为和习惯之间具有连续性。他反对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终极的善”的出发点,认为道德目标具有多样性、变动性,生长自身才是唯一的道德目的。
2.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好人”。“一个人光做好人还不够,他还必须做一个有用的好人。所谓做一个有用的好人,就是他能生活得像一个社会成员,在和别人的共同生活中,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好处能保持平衡。”[3]378学校要从知识、感情、能力三个方面去培养学生的公民人格。杜威认为:“教育不只是这种生活的手段,教育就是这种生活。维持这种教育的能力,就是道德的精髓。”[3]378从民主、经验和生活出发,杜威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好人”,也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好公民。他认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公民,“第一,应该是一个良好的邻居和朋友;第二,不但自己受到别人的好处,也要使别人受到自己的好处;第三,在经济方面要从事生产,要做生利的人,而不是分利的人;第四,应该做一个好的消费者,一个好的消费者能够起到监督商家的作用;第五,要做一个良好的创造者或贡献者”[5]。学校道德教育所培养的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不是道德理想之中的圣人。
3.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间接的道德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途径。杜威认为:“离开了参与社会生活,学校就既没有道德的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4]136—158学校如何才能培养起学生的“道德观念”而不仅仅是“关于道德的观念”?杜威认为,个人、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人的行为,人性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经验的积累。杜威把道德理解为风俗、传统与习惯(属于文化的范畴),都是经验的积累与自组织。风俗习惯是保存以往经验最经济的办法。道德在骨子里是经验的,而不是技术的,不是形而上的,亦不是数学的。杜威这种由人性的经验特征衍化为道德的观点,与先验的人性论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
道德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道德教育必须在生活中进行,需要把道德生活的内容从一般性的追求固定目的与遵守规则,转移到对特殊的具体的道德行为的检查、反省、评价与选择上来,把道德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与实际机缘保持有利接触。学校中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道德知识的传授并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也不能代替真正的道德教育。真正的道德教育不是孤立在课堂之中,它是一种间接的道德教育,渗透在学校的一切活动之中。
杜威的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从他的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理想和基于经验的道德教育理论出发,提出了学校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应然的目的,即培养“有用的好人”,而培养的根本途径是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间接的道德教育。这种学校道德教育目的观对目前学校过于追求道德教育的工具价值,仅仅采用直接的课程教育而忽视受教育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培养远离现实生活的“圣人”目标,是一个有力的抨击。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2.
[2] 约翰•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2—33.
[3]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5] 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M].胡适口,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9—110.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
责任编辑/杨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