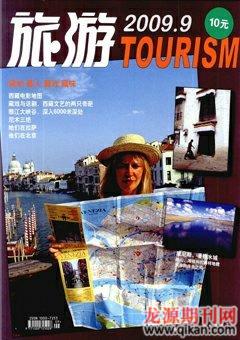鄂西火垅
陈孝荣
鄂西火垅是鄂西人的断肠娃,握在温暖的手心里呵护。一般是单独一间房,或置于偏厦,或置于私檐,或置于绕间。留一到二扇门。一扇门,通往屋外的开阔世界。一扇门,通往里屋的生活深处。置一户窗。窗户斗般大小,迎接户外光线。屋子方形,二十来个平方,够十来人围火而坐。半人以上的地方,包括楼板、楼索、窗户、火炕、炊壶、梭钩,以及墙上铁钉,都被慈祥的炊烟,抚摸得漆般黑亮,钻石般戴在人的心里。
鄂西火垅也是古井,纵深数千年。发源于祖先的篝火,一直延续到今天,古朴若禅。用于取暖、烧水、烟熏腊肉和豆腐,一如自产纯酿,芳香能牢牢抓在手里,系在心上。
它也是慈祥、善良的老人,慈眉善目,银发飘飘。人们围在他身边聚会、交谈、商讨、歌唱、游戏之地,贴心如小丫头。即使富裕人家,做了水泥楼房的,也没谁扔下这个贴心丫头。而是在水泥屋旁再做一土墙屋,置一柴火垅。倒是煤炭炉,电暖器那些洋玩意,成了弃儿。
我家的火垅一直放在绕间里。先在屋的中间挖一尺余深的土坑,再在坑的三面镶上青石。青石用龙鼓钻子打出,磨得镜般光滑。土坑里盛着细如粉末的油现灰。头上吊着祖传的铜炊壶。铜炊壶能盛一桶水。周身熏得漆黑如染。烧过百来年,依旧完好如初。吊炊壶的梭钩,为村里的铁匠打制,用于升降炊壶,自然是染一般黑。火垅框子后面则堆着土皮,那是母亲从地里背回来的。母亲勤快如水车,先是把屋四周的青草用锄头扁开,再晒上几天,晒得枯如火纸,就用背篓一背篓一背篓地背进屋,倒在火垅框子后面,堆得像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就叫柴后头。从屋外抱进来的枯柴就放在柴后头上。火垅框子上,一般放着一把或是二把火钳,火钳也是村里的铁匠专门打制,手柄处磨得像新结出的玉米一样洁白如新。灰坑里歪放着一只烤茶罐,葫芦般大小,乖猫般听话。父亲就用这只烤茶罐泡茶,自饮,或是招待客人。
往往是夕阳西下时分,金色夕阳把对面的下庄泼得红如醉汉时,一道无声的命令就下达了。我们得赶紧架火垅的火,烧水。待到水开,夕阳就石一样沉入西山,夜幕就赶紧拉起一层毡子,慢慢将村子覆盖。这时,屋外就响起了放锄头的声音,或是放背篓、篾篓的声音。不用猜,父母从地里回家了。接着,脚步声进入屋内。接着,锅碗碰撞的声响和说话的声音,就乐曲一般在屋子里响起,又水一样漫出屋外,与屋上飘飞的袅袅炊烟一起,加入村庄的大合唱。一家人的生活,又江河般涛涛向前。吃过晚饭,一家人便坐在火垅里,要么是互问情况,要么是商量事情。往往是,父亲一边烤着烤罐茶,一边细眯了眼望着我们,茶的香气如花盛开,嘭地一声,胀满屋子。或者是,母亲吧嗒几口山烟,然后就取了烟嘴,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回答。那歇在头顶的乳白色烟雾,似乎是母亲掏出的慈爱,历历眼前。一直到我们睡觉前,那话语就如山中细流,沁人心脾。亲情则如柴火烤胸,温暖于心。
倘若是到了冬天,坐在火垅的时间就更长了。往往是父亲坐在火垅一角,拿了斧头,或是篾刀,整理着木器,或是篾器,被削下来的木屑、竹屑就下雪一般,从他的腿上,一直铺到地上。地上总是积攒厚厚的一堆。待到积攒的木屑、竹屑堆到影响操作时,他就把那些木屑、或竹屑拿起来放进火里。轰地一声,火苗窜上来,刚才还温温响着的炊壶,突然间就响出大声,就像受到特别照顾,猛然间暴出的笑声。母亲则坐在火垅里,拿了针线,或是纳鞋底,或是绣鞋垫。线索抽过鞋底的声音,如细语,似叮咛,不绝于耳。我们就坐在旁边拿了一本书看。书是从他处借来,无首无尾,盐菜一般。我们却看得如醉若狂,笑哭无常。最淘气的自然是猫了,它要么是掏了木屑、竹屑,要么是牵了母亲的线索,皮球般跳来滚去,陶醉在它的游戏中。狗则站在旁边,望着跳来跳去的猫,嫉妒得眼红如血。
夏天,必得熏蚊子的。母亲先是从地里背回庄稼的桔梗,柴禾,高高地堆在火垅上。然后采来熏蚊子的薅草,密密麻麻地铺在柴禾上。然后将我们赶到屋外,再点燃柴禾,再关严所有门窗。顷刻司,浓浓的烟雾就胀满屋子。又从各个门缝、牛子眼、窗户和瓦上,如沁水般缕缕沁出。等到将蚊子熏死,再打开所有门窗,将烟雾驱尽,屋子就洁净如空气过滤。我们一觉睡到自然醒,一颗犹如洗般的太阳就爬上了柳松坪的山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