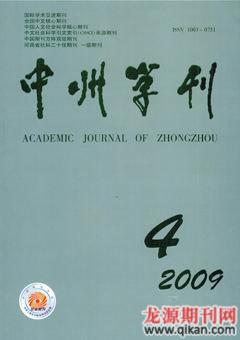为传统文化的没落唱挽歌
杨彦玲
摘 要:中国作家白先勇和美国作家福克纳都是时间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们在时间的向度上表现出极强的相似性:拥抱过去,拒绝未来。这使他们的作品有着趋同的主题指向——都在为传统文化的没落唱挽歌。对传统文化的消亡,白先勇更多的是无奈的感伤,而福克纳却在冷静的反思中,思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对两者进行深入比较,可以窥见不同文化背景和创作个性在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相似性和不同点。
关键词:白先勇;福克纳;时间意识;主题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223—05
与20世纪现代文明在世界长驱直入的发展趋势相反,20世纪世界文学中却涌动着一股回归传统文化的潮流。白先勇和福克纳便是这股回归潮流中的两位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有着趋同的主题指向——都在为传统文化的没落唱挽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被解读为对美国南方破败和衰落的历史的再现,对美国南方传统失落的一种哀悼。白先勇的小说则往往由人而到历史、文化,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中内隐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包涵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前途走向的思考。而时间,在传统文化的沦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于两位作家的时间意识,已有学者提及。对福克纳,萨特有过这样的评价:“……小说家的美学观点总是要我们追溯到他的哲学上去。批评家的任务是要在评价他的写作方法之前找出作者的哲学。而显然,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①而对白先勇,他的同时代的作家兼好友欧阳子也有过经典性的论断,她发现“《台北人》一书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保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②这个发现很准确地道出了白先勇小说的特质。和福克纳相似,白先勇的哲学也是一种时间的哲学,时间构成了他们叙述最本原的动力。
如果说白先勇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中察觉到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福克纳则是从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式微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无情。
个体悲剧中隐含中国传统文化失落
198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访问时,白先勇曾这样说:“我的《台北人》、《纽约客》的主题,都是在写历史的转折,确实在写中国传统的崩溃,确实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哀悼。”③的确,他的悲剧观主要建立在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基础上,但历史文化对一个作家而言不仅是抽象的知识传统,更是附着于活生生的个人命运之中,而时间流逝、社会变迁,又正是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梁父吟》里,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作者对传统精神价值的礼赞以及对于它们逝去的哀叹。主人公朴公曾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在文中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翁了。朴公出场时,“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着一顶紫貂方帽”④,俨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老人形象。他不仅衣着打扮传统,室内装饰也昭显着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书房里摆放着紫檀木太师椅,墙上挂着文征明的山水画和郑板桥的真迹,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和线装的《资治通鉴》。朴公的衣着、家居都有着浓浓的中国传统的味道,这些看得见的传统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心灵的折射,反映了以朴公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传统、对过去的深深眷恋。因为这种眷恋,他看不惯好友王孟养的儿子对待父亲丧事的态度,批评他在外国呆久了不懂中国的人情礼俗;因为这种眷恋,他给孙子起名叫效先,教他背诵唐诗。虽然朴公全力攀住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精神,可是,时间的流逝不是他可以阻挡的。朴公已经年近七十,任凭他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肉体生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一旦朴公去世,效先也会被父母接回美國去,变成一个“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养的命运相差不多,他们都面临着传统精神无人承继的窘境。
把文化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紧密相联最典型的,莫过于《游园惊梦》。女主人公蓝田玉年轻时是南京昆曲名角,因一曲《游园惊梦》成为将军夫人,享尽荣华富贵,后来又因丈夫死去冷冷清清地独居台南。在这篇小说中,钱夫人的命运形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失落”。随着岁月流转,她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美貌,失去了荣华富贵,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情人――最后,连嗓子也哑了,以至于无法完成一曲《惊梦》。《游园惊梦》这出戏,是昆曲的代表。而昆曲是中国戏曲的精华,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对昆曲,白先勇情有独钟。他曾说过:“昆曲是我们表演艺术最高贵、最精致的一种形式,它词藻的美、音乐的美、身段的美,可以说别的戏剧形式都比不上,我看了之后叹为观止。那么精美的艺术形式,而今天已经式微了,从这里头我兴起一种追悼的感觉――美的事物竟都是不长久。”⑤白先勇已经深深体会到,昆曲这种中国最古雅的戏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到了尾声。当对昆曲兴衰史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对这篇小说的内涵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钱夫人终于哑掉,不能把此戏唱完,暗示着中国的古典文化到今日而戛然中断。白先勇虽然在表面上仅仅描写了钱夫人的失落心理,实际上却把她个人韶华易逝的感慨怅惘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作为昆曲名伶,钱夫人个人的身世沉浮以及艺术生命的枯萎,自然而然象征了中华民族超卓无比的昆曲艺术的衰微。如此,小说主题从表现钱夫人个人身世的沧桑史,扩大成为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沧桑史。这样,白先勇笔下的历史沧桑感,就突破单独个体的心灵层面而进入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层面。
是什么导致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衰落?小说结尾隐含了答案:
窦夫人问钱夫人:“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
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变多喽。”
走到房子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的加了一句:“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的高楼大厦。”⑥
一个“变”字,就点明了这篇小说的中心主题。“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暗示了社会的变迁,即农业社会的没落和工业社会的兴起。
当然,新的工商业文明兴起,旧的传统农业文明在无可奈何中走向败落,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这一概念本身蕴含了“时间”,在提及“历史”这一名称的同时实际也就提及了“时间”。正因为时间永远向前,历史的发展无法阻挡,传统文化的沦落才被表现为无可挽回的悲剧。就这样,白先勇在历史的变迁中,在时间的流转中,在个体悲剧命运中,对传统文化的失落发出了一声叹息。
家族命运中昭显美国南方文化衰微
与白先勇一样,福克纳也痛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衰微。20世纪初,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南方,工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南方社会从农业文明步入了现代工商业文明。表现南方旧秩序在社会变革中的解体是福克纳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他把这种南方文化的衰微寄寓于南方贵族世家的衰败命运的描述之中。
福克纳在他的十几部小说中,创造了密西西比州境内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并在这个想象的南方社会中,跟踪几大家族的起起落落和众多成员的坎坷的人生轨迹,对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段历史进行多侧面的反映,对南方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和心理冲击做了切片分析。他的诸多作品形象地描述了南北战争后南方庄园主的衰败状况。在这些作品中,《喧哗与骚动》无可争议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福克纳借助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史对“时间”这个物质世界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福克纳认为,人的悲哀在于他难以摆脱时间的桎梏。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一个人是他不幸的总和。有一天你会觉得不幸是会厌倦的,然而时间是你的不幸……”⑦萨特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认为:“这是《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⑧确实,福克纳在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时间意识也正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他对人与时间的关系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在昆丁叙述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昆丁部分开头一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记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⑨
在这里,福克纳还特意说明那块表是“爷爷留下的”,又由父亲传给昆丁,这无疑暗示这块表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象征传统,正是昆丁的祖辈、父辈把南方的传统传给了昆丁,从而使昆丁受困于传统的枷锁而无法面对新生活;另一方面,钟表滴滴答答走个不停又象征着前进与变革。这样,昆丁在自杀那天的早晨躺在床上“听表”也就有了更深的含义。他不仅在倾听那毁灭一切的时间的“进军号”,也在听命于传统。正因为这块表既象征时间(变化)又象征传统(过去),通过这个象征意象,我们可以看到,昆丁处于传统与变革的夹击中,毫无逃脱的希望,最后只好跳河自杀。这实际上也是康普生家庭乃至整个旧南方不可挽回的命运。处于时间与传统的碰撞中不能自救不仅是昆丁部分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本主题。
小说中凯蒂的堕落,杰生的变异,作为没落地主阶级最后一名代表昆丁的自杀,都暗示南方传统道德文化的彻底崩溃。康普生家族彻底衰落了,它所代表的旧制度、旧传统死亡了。由此作品又引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主题,那就是时间的毁灭性。对于想永远生活在过去的康普生家族的人们来说,是时间毁了他们的家族,毁了他们美好的过去,毁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于是,他们非常恐惧和憎恨时间。康普生先生就认为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而是被那毁灭一切的时间折磨死的;昆丁对一分一秒地无情推进的时间如此恐惧,以致妄图用毁坏手表、扯掉指针、践踏地上的影子来阻止时间前进。但是,在人类和时间的抗争中,人类永远是失败者。无论昆丁如何去挽留,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南方旧传统在时间的流逝中永远留在了过去。可以说,康普生家的悲剧,是南方乡绅社会走向解体的缩影。他们的故事是崩解的南方社会无数碎块中的一片。
福克纳始终自称“乡下人”⑩。“乡下人”就字面意义来看,包含了一种与现代文明对立的意味。现代商业文明是建立在以利益、功利为原则的组织结构中,它追逐物质利益与现代生活的舒适与奢华,但也因此把现代人引向对物欲的单向度的追求中而导致精神蜕化、道德滑坡。福克纳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来审视现代文明,这种审视使他与现代文明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对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时代主流文化保持一种本能的疏离。对工商资本主义对南方的入侵,福克纳怀着一种排斥、批判的态度。在后期创作的三部小说《村子》、《小镇》和《大宅》中,他对工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和冷酷无情做了充分地揭露、讽刺、嘲弄和批判,同时对它蚕食、腐败、瓦解和征服南方社会、破坏南方传统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的状况表现了深切的忧虑和不安。
在短篇小说《熊》的结尾,在大熊老班被杀两年后,艾萨克独自一人来到森林。他痛心地看到火车开进了大森林,他所珍惜的一切都在不可挽回地成为过去。同神灵般的老班形成对照的是一只可怜的小熊,它被轰鸣的火车吓得爬上一棵小树不敢下来。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萨克看到此时的布恩,这个具有非凡勇气、曾在与老班的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把刀插进它的心脏的猎人,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橡树下,因为无法把拆开的枪装上,正在歇斯底里地用枪筒敲击枪把。他竭力想把枪修好来射击被困在树上的几十只松鼠。一个昔日的英雄已变成了一个无能、自私的小丑。福克纳在谈到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时说,他是用一个曾经同狮子一道英勇杀死老班的人的“小小喜剧来增强熊和狗的悲剧”,并使之“更为辛辣”。(11)
这一场面无疑是对现代南方人精神蜕变的一种讽谕性映射,它提示了随着现代工商业文明对传统精神品格的侵袭,现代人已丧失其英雄品格,日益变得自私渺小。正因为此,福克纳从时间的此时之在走向了它的彼时之在,即传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福克纳触摸到了一种高贵、辉煌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消逝才被表现为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
无奈的感伤与深沉的反思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成熟的台湾作家,福克纳是20世纪20年代走上文坛的美国作家,虽然有着三四十年的时间的距离,但是考察60年代的台湾和20年代美国南方,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时期惊人的相似:都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时代。这一历史变迁对福克纳和白先勇两位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震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看着一个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他们几乎是本能地想要留住时间将带走的一切,向后看的时间意识由此而生。作家把这种情绪融入在各自的作品中,我们读作品时能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作者的态度,是思旧,而非迎新;是回顾,而非前瞻;是悲悼,而非庆贺。换句话说,作者要呈现的,是旧的结束,不是新的开始。
对南方传统,福克纳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南方庄园主的后代,一个长期受旧传统习俗熏陶的世家子弟,他的感情注定了在要灭亡的那个阶级一边。但是,他对传统世界的负面阴影有着深刻而清醒的洞察。他无法容忍奴隶制对人性的践踏,他所描写的这些家庭最后都无可挽回地解体和败落了。它们的解体全部是由于内部腐败、非人性和道德堕落,标志着一个残忍的社会制度的失败和旧时代的结束。应该说,福克纳对旧传统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只不过,他不是站在工商主义的新阵营里来批评旧传统,恰恰相反,他揭露和批评南方社会及南方传统中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重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便能够抵制工商主义的侵蚀。由于他必须两面作战,所以他几乎总是处于深刻的矛盾和极度的痛苦之中。《押沙龙,押沙龙!》里折磨着昆丁•康普生的那种对南方爱恨交织的心情,正是福克纳身上矛盾和痛苦的艺术体现。
和福克纳对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留恋相似,白先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极其深厚。他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蕴积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心理形态、艺术精神等元素,都已深深地融入了白先勇的血液里。他曾说过:“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12)古典文学深厚的历史感促成白先勇的历史观中含有浓重的今昔意识。世事变迁,今非昔比,时间无情流逝,往事一去不返。无论是书写青春易逝的伤感,还是书写美人迟暮的哀愁,我们都能感受到白先勇受传统文化浸染非常之深。
正因为如此,对传统文化的消亡,白先勇沉浸于无限的感伤中,而福克纳在对传统与现代的冷静洞察中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只有过去时代的人们身上的那些古老的美德,即“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才能帮助现代人克服自身和社会的问题,阻止道德的沦丧,帮助他们在荒原般的现代社会中像人一样的生活,或者用他的话说,只有这些“昔日的荣耀”才能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13)
结语
白先勇曾经这样说过:“对于西方的伟大作家如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等人来说,探索自我即是要透过比喻来表现普遍的人生问题;但台湾新一代的作者却把个人的遭遇,比喻国家整体的命运。由此看来,他们那种‘忧时伤怀的精神,确是继承了‘五四时代作家的传统。”(14)这句话放在白先勇和福克纳身上同样适用。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白先勇的时间表述中渗进了沉重的国家民族论述,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将个体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也是白先勇能够不囿于西方现代派、建构中国现代派的重要原因。而与西方文学传统相一致,福克纳的时间表述中则有更多象征的意义,超越了美国南方的特定地域,而指涉人类的生存状况。
注释
①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见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②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见《白先勇文集》卷二《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95、196页。
③白先勇:《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答问—白先勇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5期。
④白先勇:《梁父吟》,见《白先勇文集》卷二《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⑤白先勇:《为逝去的美造像-谈〈游园惊梦〉的小说与演出》,见《白先勇文集》卷五《游园惊梦》,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⑥白先勇:《游园惊梦》,见《白先勇文集》卷二《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⑦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见《福克纳文集》,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⑧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见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见《福克纳文集》,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⑩福克纳曾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农民,甚至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他还告诉人们,他是一个农民,从未穿过西服那样的“猴子服装”。见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1)转引自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
(12)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见《白先勇文集》卷四《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254、255页。
(13)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张子清译,见李文俊编《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255页。
(14)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见《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责任编辑:凯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