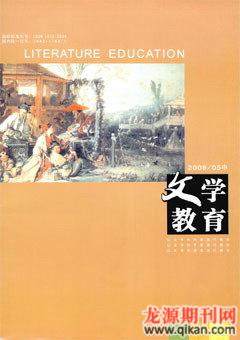从生命的多重性谈文艺无达诂
刘 菊
“诗无达诂”之说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清人沈德潜这样解释“诗无达诂”:“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深浅高下,各有会心。”赋诗、鉴诗没有固定的方法,以读者对诗的接受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接受主体的能动性。文艺无达诂从“诗无达诂”衍生而来,意为文艺鉴赏无定法,不同的鉴赏者有不同的审美角度,不同的鉴赏者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审美场不同,同一鉴赏者对同一文本也会形成不同的审美效应。
我国古代文论认为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形成隐藏作者丰富情感和意志的文本,文艺作品的价值最终得通过读者的鉴赏接受才能实现。这样,鉴赏就得“披文入情”,由显而索隐,从外而入内,经言辞以探情志,从深入分析作品的表征(文字、修辞、风格等)入手来把握其内容。可见:我国古文论已经认为创作论和鉴赏论是互通互见。创作是作者生命欲望的体现和满足。封孝伦教授曾提出人的生命具有三重性,包括生物性、精神性、社会性。三重生命的愿望,形成创作的三个向度:有的侧重于面向生物生命,注重感官刺激;有的侧重面向精神生命,注重想象世界的奇特与丰富;有的侧重面向社会生命,注重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效应。创作的对象即为文艺鉴赏的对象,这就形成了鉴赏者指向审美对象的多个向度。鉴赏是鉴赏者带着生命愿望以精神活动的方式从对象获得生命欲望的体现和满足。
文艺作品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生命需求与表达的多样性决定了文艺无达诂。
有的文艺作品通过模仿生活来构筑再现型作品以修补现实,有的作品通过想象构筑表现型作品来创造理想。现实主义作品就得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观照,浪漫主义作品就得用浪漫主义手法去解读。现代主义作品若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解读势必会百思不得其解。尽管艺术种类之间有一定的借鉴,但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的符码。在鉴赏实践中就得遵循不同艺术的符码规则和建构方式。例如,我们不能用鉴赏小说的方法去欣赏一首诗歌,小说重叙述,诗歌重抒情。我们也不能用鉴赏诗歌的方法去欣赏戏剧,因为戏剧重视的是矛盾冲突。
接受理论指出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任何文艺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而变动游移,很难停留在创作者给定的意愿或者既定的文本上。鉴赏者在欣赏作品时,得根据上下文的揭示和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鉴赏者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对作品的解释,以自己的生命愿望去重构文本。一般来说越是抽象的作品被解释、被重构的空间就越大。对反理性作品,例如现代派画,意识流画,后现在派的原小说,鉴赏者可以天马行空去想象、填补、重构。
鉴赏是“二度创造”的精神活动。鉴赏者的生命历程与生命愿望的差异必然形成审美差异。例如,郁达夫认为朱自清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而台湾散文作家余光中认为郁达夫所评朱自清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的话,还不如“加在徐志摩的身上比较恰当”,认为朱自清的情感心态“停留在家业时代,太软太旧”,认为他的散文是“清汤挂面式”。可见,鉴赏者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色彩去鉴赏,或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有的爱小说,有的爱影视,有的爱书法,有的爱音乐,有的喜欢现实的真实性,有的偏爱理想的浪漫,有的喜好现代的迷离。言情题材,武侠题材,侦探题材,生活题材,革命题材,改革题材,各取所好;或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旨归:追求感观的刺激,追求性情的陶冶,追求精神的陶醉,追求理性思辨境界,各取所需;或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有的处于情绪感动状态,有的进入精神的享受状态,而有的则达到哲理的思辨状态。
鉴赏者的生命历程是流动的,生命的愿望与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不同时代对同一作品,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的鉴赏都会形成不同的鉴赏效果。从传世之作《红楼梦》到《阿Q正传》,从五十年前的《四世同堂》,到新时期《爱是不能忘记的》,对这些作品从未有过一致的、永恒不变的解释;70年代人听《东方红》与现在人听《东方红》感受不同:小时候看《地道战》与成年后看《地道战》理解各异。不同生命历程的鉴赏者赋予作品不同的生命力。
生命的多重形式、多重需求决定文艺鉴赏多重角度:再现的角度,表现的角度,技法的角度,社会需要的角度,艺术研究的角度,艺术发展的角度。统治者的角度,民间的角度,性别的角度等等。不同的鉴赏角度强调文本的不同方面,只选择单一的角度必然武断地缩小各种可能性。每一种批评理论不可能穷尽文本的潜在意义,而是将意义中在某些时代对某些读者具有价值和可理解的某些东西分离出来。
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决定了创作和鉴赏的三重层递性。鉴赏过程是鉴赏者与创作者的生命欲望互动融会获得满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鉴赏者的生命欲望与创作者生命欲望的融合程度有一定的深浅差别,很少有人能同时获得这三重生命欲望的满足。鉴赏者从感动的生物本能层面到赏心悦目的精神层面,再达到专业批评的社会层面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审美实践中,有的接受者无法欣赏肖邦的曲子:不是所有的接受者都能欣赏梵高的画;而马原的小说也只是专业人士叫好;通俗歌曲却被普通大众唱红了天。
——河北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