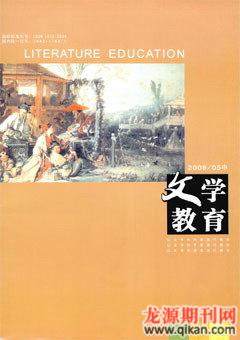文学是表达内心的方式
一、“现代主义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从先锋时期到现在,我一直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你很注意变化。而且,你在先锋作家中显得很有才气。
北村(以下简称北):你过奖了。
姜:先锋文学有着某种经典性的意义。客观上说,倒是那个时期的先锋文学评论显得不成熟。西方的术语啊概念啊什么的,全是他们搞出来的。评论界现在才觉得当时的探索是成熟而冷静的。
北:先锋这一称谓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那时候我写的东西有某些代表性。这一点我不想否认。
姜:先锋文学的很多作品现在读起来都有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力量。
北:是啊,其实这帮人当初对人物心理的入微的展示还是非常成功的。在还原生活上也做得非常到位。不仅仅是那么点前卫精神。更不是只有那么点叙事圈套。
姜:不错。不像一些评论家说的只注重于文本实验和写作路数的权威性建构。有些评论家还认为先锋作家的才力难以为继,丧失了持续解难题的能力。
北:我不这样认为,先锋作家们有这种才气。只不过,现在不能再用那种路子来写作了,这一切是会变化的。
姜:先锋文学培养了中国一批很好的文学读者。
北:可惜这样的群体太小。
姜:但也应该看到,读者们已经能穿透现实主义层面了。这也是作家们期待的。然而更多的先锋作家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等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我觉得你在这方面以及文本的探索方面付出了比较好的努力。
北:我觉得我还不仅仅单纯地追求这些。我大学毕业以后,精神方面的问题还一直闹心。很多很寻常的问题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解决。正好当时一些哲学思潮开始涌进国门。这些思潮帮助对我加深思考有过帮助。
姜:你的《x者说》系列,那种独特的话语景观显示了这个世界的模糊与不确定。
北:可以这样说吧。《聒噪者说》比较典型,其实我是表达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和一种语言的痛苦。
姜:语言的痛苦,厨川白村的话。
北:我想用语言本身来说明一个事情。但我又觉得一个真相在我叙说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叙说本身消解。我在揭示真相的同时,可能也把它消解掉了。这是一种语言的痛苦,我想要表达我的这么个看法。读者在阅读的感觉上可能就有矛盾性,觉得叙述本身不可靠。这是我预设的阅读效果。
姜:照这么说,你是在为难读者,或者真的是在和读者玩着叙事圈套,认定还原的不可能。
北:大家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作家只关心有价值的评论家的话,我从来不是为了评论写作的。
姜:说到这里这想到《聒噪者说》里那个叫朱茂新的教授为林展新的聋哑学校的写了一个“我要说话”的条幅。这有点意思。
北:是是是,我要说话。与评论家无关。
姜:“我要说话”其实也是一种《圣经》语体。质朴而又顽强。
北:你的语言感悟确实很有独到之处。看来你是一个很能理解作家的人。但《圣经》是《圣经》,人是人。
姜:先锋作家一般都根注重对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沿袭或者模仿,我很想知道你受谁的影响较大。
北:过去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很多大师影响过我。但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有些区别。
姜:一度时间,我觉得你的身后应该是博尔赫斯。特别是你先锋时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交叉花园小径的意味,迷幻不定。这种判断对吗?
北:对博尔赫斯来说,我是比较多地把他当做研究与观察的对象。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我晟喜欢的还是卡夫卡的作品。
姜:你对卡夫卡的文学精神更注重于哪一点?是不是人的生存现状?
北:这一点有,卡夫卡真实地揭示了我们整个人类生存的基本的现象。非常真实,非常直接,非常准确,体验深刻。我们这个时代那种精神上的困境,卡夫卡的作品是最早体现的,譬如囚禁感什么的。我更能体察的是他那种因无法命名而带来的莫可名状的痛苦。他的《地洞》我觉得比《变形记》还深刻。《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等等,我觉得我们无法逾越他,无法超越。
姜:你如何看一些作家寻找某个西方现代作家作为自己的文学楷模这样的现象呢?你觉得这与民族性有什么关系?
北:我觉得不要刻意区分这是一个什么民族的作家,虽然作家肯定有其民族性。我发现自己更认同西方某个作家。这是没办法的事。人类的精神有着共同点。这里面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障碍。
姜:文学说到底应该没有国界。
北:是这样的。譬如说,我也很喜欢鲁迅,但我觉得他的后期灰暗了点。
姜:为什么这样看呢?
北:他以他的眼睛清楚地洞悉了真相,但是,他的内心缺少安慰。我们反抗、反对或者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一个清晰的价值立场上和位置上。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被安慰者笼罩从而得到安慰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会平静,一种披安慰后的平静,这是一种欢乐。鲁迅的内心并没有欢乐。鲁迅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恨。恨是他的语言方式。
姜:这就是你刚才讲的“灰暗了点”的意思?
北:这个时候鲁迅的内心堕入了一种极度的痛苦中。这个时候,他的随笔犀利而深刻。但我觉得他的光彩不像我们在读西方大师时那么真切了。
姜:后期他没有小说作品了,所以在人的形象方面,他似乎远离了,走得远了。
北:实际上,人类一些共通的特征,我觉得无论属哪一种民族哪一种文化的作家,都是必须给予关注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写出很深切的存在的感受,只对生活的艺术有一点肤浅感受,我觉得我是不会认同的,因为它没有从最深处感动我。
姜:你对先锋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是怎么看?
北:你所说的传统文学是指什么文学?
姜:应该是风骚并存的东西,但更应该偏于现实主义文学吧。
北:我觉得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词汇,表达得很好。但我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个词?
姜:为什么?
北:现实主义让我想到我们所面临的某种当代性的问题,以及我们所接触到的某种现状。但我们肯定是历史地存在着。
姜:历史地存在着?
北:对。它集中表现在当下的我们的境遇。这不仅是事实层面的,也有当下存在的精神性的迷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当好严格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这种写作是最艰难的。因为人可以在写作中找到最轻松的逃路,然后沿着这条路逃逸。但人家还把它称之为文学、优秀的文学。然而是不是呢?这基于作者对于艺术的态度是什么,他觉得文学是那样的他就写成那样的。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我认为就在这儿。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姜:其实,《公民凯恩》这样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或
者说,你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看作现实主义。
北:我的作品内在的东西都是一致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己。写《公民凯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北村,你为什么不写一下现实主义作品?我反问他,你说我在写什么作品?我不知道他指什么。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他是指现实生活题材。我觉得这其实是选择载体的需要。但我觉得我也有必要选择当下的生活现象作为载体。
姜:当下的生活现象不是现实主义吗?或者说,现实主义不包容这一点吗?
北:这个不重要,绝对不是写了当下的生活现象就是现实主义,或者说作品有当代性就是现实主义。
姜:《公民凯恩》其实与你的很多作品一样,都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我说过,在先锋作家当中,在这方面,你还是独树一帜的。这是你的可贵之处。
北:不是因为你写了酒吧,写了城市景象、城市人群,然后你就可以说你写出了当代城市的真实体验,并不是这样的。你要永远围绕人的状况、人的精神状况,写出你在当下现实里面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经验。《公民凯恩》只是题材上有区别。后来我写到他出走。如果按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写到出走之前就行了。
姜:你想解决问题了。但我觉得后面是作者与作品在抢了。
北:这怎么理解?
姜:到了后面作者站出来了。陈凯恩是想从同学那里得到什么的。可同学让他很失望。我读到最后也很失望。对那个气象站的同学失望。这好像是你的一种故意。
北: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有这么点意思,我是在故意表达我的思考。不过。后面有一首诗你还记得吗?
姜:记得,你说是那个叫释弘悯的和尚的诗。
北:当时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很震动,我觉得那个人是多么痛苦。他说,我像个抹布一样,还没有把别人擦干净我自己就先浑浊了。这就是一个人在追求理想境界时遇到巨大障碍时的痛苦。这种痛苦与一般人的痛苦不同,有很内在的内容。
姜:这又回到我们原初的话题中心了,这个人内心没有安慰。他的手淫很恶心,但很无望。
北:巨大的绝望也能带来一种奇怪的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有快乐,它以虚空为特征。有些人因此就遁入玄学。有的人则在物质世界里面的肉体狂欢中找到瞬间的快乐。真正的真实的永恒的快乐,值得我们去探求。我们的作品得把这些重要的问题表达出来。
姜:我明白了,这里面有着你的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区别。现代主义重于挖掘并努力解决,而现实主义则重于展示,它提出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
北:现代主义作品也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
二、“我基本背对着文坛写作”
姜:你的语言与余华的比较接近。有一种质朴的美。但我又觉得,你与余华、苏童相比,好像还有另一种东西。
北:也不能这么说,方式可能有不同。至于其他,我说不好。
姜:苏童更重于诗意的描绘,情调的拓展。前期的余华有一种迷幻的感觉。他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倒与你的《老木的琴》有着某种相似。
北:我到现在都不能完全明白,当初为什么把这批人归入先锋。我觉得这批人总体上有一种超越精神。写作能力相当强,但差异性也是非常大的。后面的创作中就逐渐体现出来了。我觉得现在要评价为时过早,但是我敢肯定的是,现在大家都是沿着自己的方向去写的。
姜:余华在这批人当中是不错的。而你现在的写作,好像量不是太大。
北:我总是这样,写写停停,想停就停,不急于拿出东西,我基本上背对文坛写作。
姜: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北:我最近接触影视方面的东西。但我差不多要重新写小说了,是内心的催促,而不是为了应对一些人的说法,有些人说北村是不是被影视拐走了?
姜:《周渔的火车》媒体现在是炒得蛮热的。
北:千万不要担心我被影视拐跑了。要拐十年前就拐走了,我只是换了一种职业,从编辑换成编剧。
姜:写本子其实也是比较苦的。
北:我有时一两年没有写东西,甚至两三年没有写东西。但其实。我的写作总是这样,有时候两三年没有东西,有时候两三年不断地有东西。不管我从事什么工作,我觉得创作纯粹是个体性的东西,想要表达时他总会表达的。我不是为自己最近没有写东西辩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很奇怪的。我的矛盾倒不在于写小说和或者写电影,是写作或者不写作。
姜:你现在主要搞影视吗?
北:我现在是自由人。有的人可以把写小说当成一种职业来生存养生,我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很坚强的意志来抵抗市场。所以我宁愿让写小说这个途径纯粹些,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挣钱。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方式。我是写小说的,但我可能还会编剧,我想这可能没有什么错误吧?我原先的职业是编辑,可我不太喜欢这种职业。辞去了这份职业后,我就没有别的职业了。这不行。我得用某种方式养生。
姜:你原来在《福建文学》的。
北:对,后来出来了。
姜:我可以理解得纯粹或高尚一点,就是——你是用你的影视来养你的小说。
北:对,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不对。我把编剧这种角色当好,就行了。我把他当作我的职业,把小说当作我思索的管道。但做编剧的收入要比做小说高一些,这就有了点危险性。如果被迷住了,那就丧失其意义和初衷了。用文学养生不是不可以,我不会指责别人这样做,有的人书卖得不错,够生活了,但他必须具备抵抗市场影响到小说创作的能力。但我比较脆弱,不够强大。我还担心自己堕落。那就远离文学的基本目的了。有些炒作的事我觉得我不能做,我做不到。我适当写些剧本,以保证写小说的平稳。
姜:这也无可厚非,这是基本的生存之道。福克纳也写过电影剧本。
北:影视毕竟是一种商品性的生产行为,它也有危险,但我们可以对自己那部分的工作负责,过了就会迷乱。
姜:我觉得电影《周渔的火车》与小说《周渔的喊叫》已经相距很远了。
北:好像没有吧,不会太远。我理解你可能会有这点想法。但就改编的情形看,根本没有离开小说内在的东西。小说已经比较深了,情节载体为了电影的需要可能有些改变,但内在的东西会非常一致。
姜:你如何看待电影改编的问题?
北:相对小说而言,电影是一种合作的东西,大家都可能要作一定程度的妥协。艺术形式之间的区别导致一些相互融合,这是需要的。妥协的限度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否则也没法合作。
姜:这是否可以理解文学与传媒的同谋或媾合?
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有些看法,但我觉得从严肃的意义上看,很多电影超过小说,很多优秀导演就是思想家。我觉得导演的电影精神如果与原作的精神相似,就可以改编了。电影其实是以导演为表达主体的,我们必须尊重他(导演)。我不能以我的小
说的表达方式来要求他。
姜:问一点题外话。你怎样看作家写电影剧本的事?
北:电影里有文学的部分,就像它有音乐和美术一样正常。作家写剧本我觉得要严肃地做好。关键是态度,要站好编剧的位置。不要选择一些恶俗的东西。
姜:这里面是不是有文学向电影妥协的意思。
北:不能说电影就比文学低下。妥协不妥协其实还是内在的态度问题。如果写小说只想着挣钱与改编,哪怕他没有写过一个本子,他的小说也肯定是有问题的。
姜:与之相关的是,你觉得商业主义、时尚体验、消费社会与文学精神是否是绝对对立的?多元化的拜物的社会与文学精神是否相悖?
北:对立是存在的,而且有点激化。人往往会给自己找台阶,我们似乎都已经学会了妥协。但我们不能错误到价值观都颠倒了。宽容与妥协还是不同的。
姜:文学要迁就市场吗?
北:我觉得文学也是一种商品。它是通过销售渠道与读者接触的。但是,它的交流方式是真诚的,是精神的,是心灵的。
姜:有人愿意用钱去换取这一份真诚。
北:它不是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那种商品。这两者区别是很明显的。
三、“哲学没能解决我的根本问题”
姜:读《玛卓的爱情》,我总想问:当时你不到30岁,可为什么能将生活展示得那么凝重?
北: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读者也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里面的生活是凝重了些。那时候我的小说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姜:这篇小说里现代主义的特征我觉得倒不是太明显,倒是能看见现实主义的影子。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爱情。
北:那时我的年纪确实不是很大。我没有有意扩大生活的沉重。我在大学时比较喜欢思想性的东西。有些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东西,但作为精神的形式存在时,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时候的问题这类也好像特别多。
姜:都是些什么问题?
北: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到哲学里去寻求答案。于是我去大学哲学系里听课,试图找到一些答案。
姜:那个时候很多人喜欢西方的哲学。
北: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比较真实的。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一定是亲身经历的事实。但问题存在着是一种事实。
姜:那是那是。哲学帮你解决了问题了吗?
北:哲学没能解决我的根本问题。哲学课堂没有,但哲学书帮助了我。我后来进图书馆,看了大量的书。我于是认识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他们让我着迷。
姜:从你的作品里看得出你哲学上的修养。
北:我对哲学和哲学家的兴趣可能超过了文学。阅读量至少与文学差不多。
姜:你那时候读文学吗?
北:读。读西方经典文学。那是一二年级的事。后来接触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
姜:这种情形我亲身经历了,我那时也在读大学。
北:八十年代的思潮让人有点兴奋。
姜:那时你已经发表作品了吗?
北:开始了。但很幼稚。早期作品我都没有将它们归入我的创作上去。
姜:早期作品不成熟这也很正常。
北:形态幼稚了点,但精神、思想的动机很真诚。它们一直陪伴着我。因而当时的一些问题也一直陪伴着我。只不过现在的表现形式与过去不一样了。
姜:作家的生活阅历不重要吗?
北:思想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阅历。大学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八五年到九〇年这一段时间,我还一直在精神方面的问题上兜着圈子。那时还有几个人,和我比较要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一起讨论。其中有两个人可能你也知道的。
姜:他们是谁?
北:朱大可,还有宋琳。我们经常到福州讨论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姜:朱大可的评论很有特点。
北:他是我最赞赏的批评家之一。当然我是用小说表达的。不是我要把生活变得这么沉重,我所经历的状况与过程,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思想,它让我体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
姜:从思想到小说,你觉得是不是很遥远?
北:我觉得我只要是以真诚来面对我的思想,那么寻找答案的过程便会非常真实。
姜:我最近重读你的作品,是从《玛卓的爱情》这一本书开始的。后来,我发现,你的爱情小说竟然有很多。我从这里切入问题,我觉得爱情小说可能会引起我们对话的兴奋。
北:对对对,我写过比较多的所谓爱情小说。
姜:但读你的爱情小说一点儿也没有诗情画意,一点儿不罗曼蒂克。
北:是这样的吗?
姜:我尝试着将你的爱情小说作了些提炼。我觉得《伤逝》写了爱情的错乱,《张生的婚姻》写了爱情的绝望,《玛卓的爱情》展示人们在追求理想的爱情时不会生活。《周渔的喊叫》则是展示人们在生活中不会爱情。《水土不服》写的是爱情的理想,《苏雅的忧愁》写了理想的爱情,《强暴》写了爱情的脆弱,《长征》写了爱情的力量。不知这样的提炼对不对?
北:我觉得你看得还是非常准确的。
姜:可我又担心这种提炼破坏了你所营造的那种深刻与情感。对了,还有,我觉得《强暴》其实不是对女性的强暴而是对爱情的强暴。
北:对对对,这句话说得相当好。
姜:这篇小说看完后,我觉得心情特别沉重。
北:为什么?
姜:我觉得你这一篇里写的爱情给人一种无望的感觉。
北:怎么说呢?我觉得爱情的现状就是这样的。小说写作首先是个人化的。它必须顾及我的真实感受才成。
姜:与现在所谓的私人化写作是一个意思吗?
北:不,不不,有所不同。艺术家很强调个人体验,因而他的写作必然就是个人化的。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又生活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时代,那么这种个人化里面,你的所思所想、所感受所表达的,就还得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某些重要的特征。这些要在你的作品里体现出来。不是窃窃私语。
姜:这是否影响了你对爱情的认识与思考呢?
北:我经常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对爱情持什么态度,爱情在现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种东西肯定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姜:你为什么这样表现爱情呢?
北:我个人对爱情存在着一种非常完美的理想,但我们的经验却遇到一些难度,这种难度有时指向世俗层面,有些指向精神层面。
姜:如何理解你这些爱情小说中的矛盾。《周渔的喊叫》式的爱情,看起来非常伟大的爱情却经不起轻轻一碰的。我觉得这与《长征》里那种爱情的力量相比有着天渊之别。
北:我是很矛盾的。我内心的矛盾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我个人的经历可能是一个原因。我的经历有点波折。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清醒地知道这一点。
姜:造成你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北:爱情、信任、信仰等等,在现世的生活中,怎样突破它们的难度,
我一直处于矛盾和困难当中,我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相信有终极也有完美。如果没有这样的终极与完美,人类存留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那么人类与动物又如何区别?人类的理性、情感需要、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很难解释了。然而从信仰的角度却是可以解释的。
姜:说及信仰就会想到人是有原罪的。
北:在经验的过程中,那种内在的风景是什么样的,我就在作品里表达出来。实际上《周渔的喊叫》表现的是困难和失败。
姜:这里有一种爱情的混乱与无望。
北:《长征》则写了一种成功。《长征》写在《周渔的喊叫》后面。
姜:《长征》给人以信心。
北:《长征》告诉我们,信心是真实的东西。
姜:爱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情绪。
北:情感是除了信仰之外最接近宗教的东西。
姜:人如果没有宗教的话,至少爱情是可以作为宗教的。
北:是的是的。有些人以爱情为宗教,有些人以艺术为宗教。
姜:那么你认为爱情、文学(或者艺术)、宗教这三者关系如何昵?
北:爱情、艺术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们能很真实地深入某种真相,关键是没有力量。它们应该有一种坚强的价值背景支撑扶持着才成。
姜:看来,爱情小说只是你的一种载体。
北:我选择情感题材,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写爱情小说。
姜:看来这是你的情不自禁。
北:人类情感尤其是爱情中的事实如果作为一种载体的话,它特别易于从人性上表达我想要表达的问题。
姜:看来写作确实是在解决问题。为了解决某种问题,我们不得不写作。
北:是啊,爱情具有某种终极性。
姜:对对对。
北:爱情上的信心与失落、信任、爱、恨、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真实而直接。
姜:对,这些都是终极状态下的表现。
北:所以,我就非常自然地选取了情感作为题材。这样就可能比较单纯一点去思考,倒不是我专门想写爱情。譬如《周渔的喊叫》,写的是情感,但实质上是写我们目前所处的境遇中人的信心问题。人的信心在现在已经非常脆弱了。
姜:《长征》看来是表达了爱情的信心。也就是我上面说到的爱情的力量。
北:对,应该这么理解。从其中一方面看应该这么说。
姜:但是你将这种爱情的力量放到了那样的背景下是什么意思?
北:你是指题材还是指战争状态?
姜:是那种特定的长征背景。
北:这里倒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意思。
姜:这我知道。
北:主要是时空上的需要。还有哩,我在《长征》这篇东西里还想表达另一个主题,爱情这种情感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它与很多东西混淆起来了。
姜:这很有意思,确实很少有人这样考虑爱情与爱。
北:爱情里有妒嫉。《圣经》里就说过人几乎是没有真正的纯粹的爱的。在我们人,很不容易真正把握爱情的本质,其本质是舍已,离开了这个,别的东西就混杂起来了。我觉得爱情的本质完全可以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障碍。爱应该具有永恒和无限的品质。譬如说《长征》里陶红的爱,其实已经完全不是爱了。真正的爱与妒忌在生活中其实有时是很相像的,很难识别的。在我们的经验中很难分辨。
姜:这篇小说是在写爱与妒忌的区别吗?我觉得吴清风是一种真爱。真爱的情感近乎神。“长征”——我的理解是吴清风的爱情长征。
北:对对对。撇开具体人物而言,从整篇小说看,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超越世俗,超越人的身体,甚至超越时空。永恒的极其纯粹的爱,我认为是可信的。我于是就借吴清风这一形象表现了。
姜:这篇小说让我震惊的。我觉得还有一种超越身体与情感的情爱,两个人被绑在一起的羞耻之心,在吴清德的心里就一点没有。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这里你又把终极性的考虑推到了另一个终极点。
北:爱超越时空,应该是永恒的。时空变化应该影响不了爱。但要克服难度。
姜:是这样的!
四、“文学是表达内的方式”
北:我这个人并不特别智慧,我觉得人类所有的行为,从生活行为到艺术行为再到思想,人都有某种想法,人的思想是一条河,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又会在情感方式中体现出来。一个人必须要有所思想。特别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如果没有重要的想法的话,我就非常怀疑他行为的价值。
姜:小说也是为了解决自己认为很重要但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
北: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现这种想法。可以用理论这种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诗歌方式。小说方式,电影方式等等。但要注意其文体边界。
姜:这是一个边缘问题。这里面有小说的可能性的问题。方式其实不重要。
北: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式吧,每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思想者。否则感觉就会泛滥。必须有一个原则来约束感觉,才能将其引导,才成为美。这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是一个所从何来的问题。这很重要。
姜:王蒙说过,作家是用笔进行思想的。
北:是啊,必须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人生就不真实了。没有思想的艺术只能成为一种单调的艺术态度,而并非艺术。
姜:《水土不服》中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信的?这一问题比较强硬,让人无法回避。我看这篇小说的时候陷进去了。我刚才说的爱情是一种宗教情绪的感觉其实就是在读这篇小说时产生的。但我对康生与张敏的爱情又产生了怀疑。
北:这里我可能强化了一些内部的真相,将它们放大了。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一种清醒的价值观,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被忽略了。这种价值被忽略以后,所有的尺度都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信心的失落,要命的是,现在很多人却以多元化来解释这个严重问题。
姜:你是否在说人性的崩溃呢?
北:是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时代,过去看来是一件很羞耻的事现在看来都非常正常了。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真理的大多数变成了少数,强势变成了弱势。其实,真理就是真理。我们所见到的未必就是最真实的,内心最深处所能领悟的那种真正价值本身,现在需要一种启示来照亮答案了。这个答案是最真实的,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
姜:很多人用多元化来解释这一现象,你用小说来解释。
北:我选择了康生这么个人来传达我的信心,但他是很痛苦的。我想要演绎一下这个人在现实中的状况。对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部写傻子的短篇小说,很有名的。
姜:你是说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
北:对,《傻瓜吉姆佩尔》。这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它很短,但它表达了时代的内在的变化。只不过这里
面有着某种平衡。电影《阿甘正传》也是这样的。大家现在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你要是不成为这样的人,你就很难活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姜:但我觉得阿甘那样的人没有碰到什么问题。而《水土不服》里,我们又发现社会背景没有帮助康生解决问题。
北:这篇小说写得较早也较粗,但问题很重要。现在也可以探讨。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想真实地实现他的意义,除了他有坚强的信仰保护,否则,真理的极少数将会非常痛苦。除了变成傻瓜(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傻瓜)。
姜:这里面还有一种民间立场的东西,一种叛逆。
北:从精神层面上讲,人需要一种出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找到坚实的信仰背景保护,这样就进入到一种非常寂寞孤独的空间,没有安慰。真正的信仰应该有一个安慰者。思想只是人的延伸,没有找到源头,就会以虚无为特征,在虚无中舞蹈是很怪异的。它与以爱为特征的信仰的力量的安慰是不一样的,爱是相对心灵而言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活得很自在,如余秋雨和陈逸飞。
姜:人说到底必须要有精神的支撑。
北:有些人干脆放弃,有些人借助创造者的造物制造新的崇拜。
姜: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将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作康生?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北: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可能我在作品中投射得比较明显些。
姜:因为有一个叫康洪的同志,让人觉出投射的感觉了。
北:比较浓厚。尤其是这一篇,情感浓烈。
姜:看来康生的问题全是你的问题,北村的问题。
北:本质上也许是可以这样看的吧。
姜:我在看你的作品时竟然非常担心,北村现在怎么样了?让人想到这一点,说明这篇小说比较成功。思想感情上的成功。作家说穿了是一种思想的动物,感情的动物。这篇小说很能牵动人。
北:这一篇小说主观性强了点,我开始想用第一人称写,但我觉得不太真实,就换了个名字,其实还等于是第一人称。跟我内心的东西比较相似。将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有时也是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
姜:我觉得你写小说很用力。《孔成的生活》、《孙权的故事》啊什么的,都让人觉得你的力量与场。我们很多人也写小说,但没写成气候,可能就是不用力气。
北:其实太用力了容易过,会把它写破掉;不用力可能又无法准确地表达。两者能调和好当然是非常好了。我有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我可能还缺乏一些训练。
姜:康生死时,身上只有二毛七分钱,一个吃了一半的桔子,一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是不是有海子的影子呢?
北:有,有,那时候海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姜:海子死时,状况与这个差不多。海子是一个诗人,康生也是一个诗人。严格的说,北村也是一个诗人。
北:海子的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他的死对我的震动比较大。但我觉得我的张力没能达到海子那种程度。
姜:“真美,美到几乎叫人离开善了。”这是你在《水土不服》里的话,康生经常说。你让他说了好几次。我为这句话感动而思索。北村,你认为美和善是对立的吗?你为什么总要说这句话?
北:美和善从终极意义上讲是不可能对立的。我认为这世界有一个创造者,里面有一个基本法则。人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法则里面,无论你承不承认,这个基本法则讲述着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美。秩序混乱以后,美也发生混乱。
姜:照你的看法,文学还是回避不了宗教。你觉得你一九九二年前后作品的变化主要表现是不是就在这里?
北: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一边打麻将一边轻松地写作。这些我做不到。你懂我的意思吗?
姜: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在说,你不可能一边写作一边做一个基督徒。
北:一边作基督徒一边写作是可以的,但需要你的内在生命能不断提升,这样就能写出有盼望的东西。我的生命还很弱小,这是我的真实情况。文学是表达内心的方式,很轻率很不真实地表达是不可能的。
姜:宗教性的情绪怎样影响着你的写作呢?我总觉得人皈依宗教是因为人看透了或者看破了。但我又觉得人一旦如此,文学性情就没有了。
北: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看,你有没有觉得《圣经》这是一部非常奇怪的书?你瞧,它不单单是写了一些高尚的事物,它还表现了很多很多罪恶。它并不是赞同这种罪恶,它给予了罪恶某种态度,还出示了解决的途径,只是这种途径要付出代价。我觉得《圣经》是晟好的文学。
姜:《圣经》很质朴。
北:它也很直接,很透明,很有力度。因为它有定见。有的作家想要达到《圣经》的高度,我觉得是一种妄想。我是一个《圣经》的阅读者。比起九二年来。我觉得我现在实在是看到了更多的人的有限性以及在突破时的信心经历。我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我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我只能尽可能地要传达我们所看见的光照亮的东西。
姜:光是上帝的语言,小说是北村的语言。
北:是啊,如果读者在我的作品里看见了某种真相,那是因为他给出了亮光。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智慧。这是真的。九二年前,我觉得我挺聪明的。但也挺笨的,因为没找到答案。现在我才知道,不是因为我的技能不行,是因为我的内在生命的程度不够。
姜:《玛卓的爱情》、《聒噪者说》里面都说到了光。我在读到这里时还在你的书上注了一句话:光是上帝的语言。光使人找到爱情,光使人看到真相。
北:人获取真相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用摸的方法,触摸物质的形态,比如床边摸到床头柜,这是一种感觉的方式;第二种是知识的方式,或者说是思想的方式,如按照常理床边该有床头柜,但这种方式有某种危险性,也就是知识的危险性,因为这里面有着有与无两种可能;第三种方式是亮光的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亮光照亮了物质,一切准确无误,很直接地达到了事物的本质。
姜:你所说的亮光还是一种比喻。
北:是的。这是一种启示的方式。
姜:宗教是否是灭人欲的?
北:我觉得不是。
姜:那怎样理解人的欲望?
北:人如果被欲望引导,就失去人作为人的本质的意义。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欲望。欲望诉诸于人的肉体。人也有三个层面:一个是肉体的层面;一个是精神的情感的需要:第三个是终极的需要。
姜:人应该弃绝肉体的需要吗?
北:人要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终极价值引导着人,欲望其实是可以被引导到美的途径上去的。
五、“我现在表达一种盼望”
北:九二年前后信仰背景的变化可能造成了我的创作的变异。九二年前后的作品与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我的作品里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宗教信仰的直接表达。
姜:是啊,《张生的婚姻》、《孙权
的故事》,以及《施洗的河》都是这样的。现在不这样了,是为什么呢?
北:对我信仰的东西,我仍然确信不疑。但这不意味着我已经没有了障碍。我的内在生命的提升过程仍然非常困难。在这种难度面前,我向前走。可能复杂的内心的体验比当初更内在。但我不会否认我见过的东西。否则我就是一个说谎者。
姜:这又回到虔诚上面了。
北:然而我会记住我在抵达的过程中那些丰富的感觉,快乐、失败等等,我觉得人有些感受是有价值的值得记录的,有些则没有价值。你要看有些眼泪是为什么流的。《周渔的喊叫》、《长征》你有没有看到与前期《玛卓的爱情》的不同?
姜:是的是的。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很长时间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施洗的河》里,刘浪抵达上帝是不是太容易太便捷了。刘浪由恶棍变成为宗教徒是不是太快了点太简单了点?
北: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宗教经验,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这样的。
姜:那条走近神的深水河实在太短了,刘浪上岸了,刘浪净化了。
北:我把这过程写进小说里了,所以引起人的议论。接近神其实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们会告诉你是这样的。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不要在文学里加以表现?没有信仰背景的人没有这种体验于是就无法理解,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其实,信仰是通过心灵的而不是通过思想。
姜:这怎么理解?
北:不是说人不要思想,而是说这种变化不是通过思想的。否则,思想家们就是当然的信徒了。我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对你说过,与朱大可他们一起时,先读哲学,然后接触了禅宗。后来读了很多宗教的书,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不满足。后来接触了《圣经》。
姜:你是说这里面有一种长期的过程。
北;这一过程未必要写进作品。但是,你知道的,像托尔斯泰,他的自传里写到他得到真正信仰前后的情况,过程就是这样的,我读了感到很真实。那时候,托尔斯泰五十多岁了。我不好与他相比,但在信仰过程上有相似性,其实所有信徒都一样。
姜:托尔斯泰寻找过,有过痛苦。在写作《复活》时,他还没有找到。他找到的是灵魂自我救赎的道德自我完善。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你觉得你现在的书写主题有没有变化?
北:有,这我敢肯定。过去我过多地表达了痛苦的主题。我已经比较厌烦了。
姜:现在你表达快乐吗?
北:我现在表达一种盼望。表达痛苦不应该是文学的最终目的。人有理由生活得非常快乐,有理由找到生命的答案,有理由这么生活。如果痛苦不可避免地存在,也没有必要过多地放大这种痛苦。看不见理想的真实性就违背了一个人活着的初衷。这也是一种当代性。
姜:对,好像也没有一种宗教剥夺人的快乐。
北:非常杰出的作家,我只把他认为是重要的,优秀的,没有把他当作伟大的。真正伟大的作家,一定有一种境界上的提升。他的作品除了表现现实状况以外,还要给人以安慰、快乐、方向、盼望。很多作家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们还很软弱,还不能给人以一种歌唱的声音。我们还很困难。
姜:《老木的琴》也是在说痛苦,虽然,它里面充满了纯粹的音乐之声。
北:我有时候感到无力。人自己的高度不够,就没有力量,不是真理程度不够,人自己达不到不意味着要把真理拉低。因为有人达到了。那些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一辈子都放不开的东西,而伟人们轻轻一丢就丢掉了。而在我们看来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似乎是没有用的东西,伟大的人们却为它奉献了一辈子。这一点就将我们凡人与他们区分开来了。
姜:你是说我们看不到什么是伟大?
北:只有有信心的眼睛才会看到人的意义和伟大的意义。所以,我总觉得,作品写到这个份上,写得好不好,真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能力问题,不是对生活能否理解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信心并依靠它越过人性的难度,而信心又必须从面对真理的忏悔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