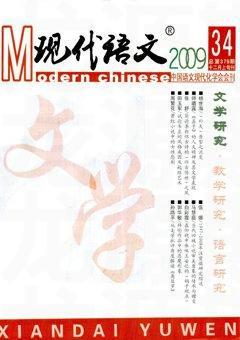当代回族小说审美意象的传承与嬗变
摘 要:当代回族作家霍达、张承志、石舒清等笔下的审美意象在衔接传承的同时,又各有侧重和嬗变,在不同语境中展现不同的审美趣味。但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信仰,使这些审美意象体现出一些共有的审美特征,一方面连接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意识,表现一种精神上的归属与期盼,同时,也预示了当代回族作家对世界的眼光和情感取向。
关键词:回族小说 审美意象 审美趣味 民族文化 归属感 情感取向
现代美学体系认为:“审美艺术学的研究(即把艺术作为一种典型的审美活动而对它进行的研究),必然指向一个中心,这就是审美意象。”[1]当代回族身份的作家成果丰硕,主要作品中反映着回族人民的生活与情感。从历史的角度看,独特的民族文化会使文学创作产生惯例性的审美意象。纵观中国当代回族小说,作家们常常借助一些既能反映回族文化特征又能表达创作主体情感意愿的意象,如月亮、水、土地等,进行象征寓意的抒写。这些反映回族人民生活与情感的小说中,特定审美意象不断传承与嬗变,对这些意象的分析,有利于深刻地把握当代回族小说的艺术特征,了解和认识回族作家的审美角度和创作心理,由此可以更进一步地解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一、清朗明月,心灵之光
随着大量优秀回族小说的不断诞生,月亮早已成为一种具有民族象征性与隐喻意义的审美意象,在回族作家笔下萦绕不去。回族作家们把咏月这一中国文化传统与特定的民族历史结合起来,月亮这个可清可晦、可圆可缺的自然物象,不仅隐喻着回族的遥远的历史,还表现着回族人民无比崇高的宗教信仰,是高洁清透的象征,是苦难的肃穆关照。
“月”,特别是新月,在回族作家笔下,是希望,是寄托,也是一种实际的生活关照。回族开斋就要以看到新月为准。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女主人公名字就是新月,写到月亮的地方比比皆是,充满着对美好的向往,一种向上的心灵之光,一种超越精神的美感。张承志笔下的“月”意象有更多的内涵。“瞬息的弦月”把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广袤荒凉烘托无余;“一弯新月”就像黑暗中给人们亮出的一盏指路的明灯。而作家石舒清、了一容等笔下,“月”被赋予了更多的地域内涵。
“新修成的大寺顶上的铜月亮,那青铜的半片月牙熠熠地亮着,使人心里充满欢欣和安慰。”“那三间破屋顶上也插着一柄铁铸地弯月亮”,“记得那天透过坍沓的顶棚,他看见了那个锈斑累累,残了一块的镰月。那牙铁月亮漆黑地立在上面,沉重而神圣。”[2]张承志通过一弯铜月亮,三间土坯屋顶上的深沉肃穆凄美温馨的“残月”,指出坚守一种信仰的艰难与希望。如果说“残月”和“弦月”是对历史的沉重回忆,那么对张承志而言,“十五的满月”就是“圣光的照耀”,是所有穆斯林的心灵灯光。《心灵史》中的一首诗说:“圆月啊,你照耀吧,唯你有着皎洁的本质。”“今夜,淫雨之后的天空上/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我的心也清纯/它朴素得像沙沟四下得荒山/然后,我任心灵轻飘/升上那清风和银晖/追寻着你 依恋着你 祈求着你 怀念着你。”[3]在这样的审美观照下,月亮不仅饱含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结,把这个蒙受苦难的民族指引到一个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展现了作家对庄严、崇高、博大、深沉的美学风格的崇尚,对诗化、象征化的艺术手法的独特追求。
回族作家石舒清、了一容对西海固的月也是经常描述。“月亮早就在天上了,只是随着夜的加深才正亮起来。”“月光下,一些沟谷和凹处更显得幽奥难测。”“我们就静静地立于月光下不知往哪里去。”石舒清大量用“月亮”、“月光”等意象衬托当时当地的人和事,表现对一些哲理性问题的思索,“月亮在天上显得安静,甚或是有些慈祥。”“天宇浩渺而澄澈,几乎只有着一盘月亮的天宇让人心里空荡荡的,有些冰凉。”[4]用这样一些特意的描写表达作者微妙的情绪,也为作品带上较为浓烈的象征意味与神秘色彩。“一轮明月已挂在天边上,跟妈妈的脚丫子一样好看,我真想在这荒野里抱着月亮大哭一场”,“有一线月光从箍窖的哨豁眼里照射进来,映在墙上,把墙上一张‘看图课文映得分外的亮。”[5]这些描述月亮的句子着眼于小说设置的场景,大多时候是为了故事情境的营造,没有特别确定的指向,但从文本整体看来,特定环境中特定审美意象的创造,是作家潜意识中“移情”活动的过程,在不自觉地对审美客体(月亮)进行想象、联想的同时,审美形象得到了积极的再创造,把心灵底处对人生的迷惘、对清洁精神的深沉追求,对外在的认识和内在的理解,很自然地表露了出来。
二、至清之水,希望之光
“水”也是中国文学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回族作家都对“水”这一意象赋予了另外一种内涵。在回族眼中,水首先是最圣洁的事物之一,因为回族是讲究清洁、洁净的一个民族,经常清洗身体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同时,由于回族生活的地方相对比较干旱,水显得异常珍贵。所以,水不仅是生命的甘露,也是生命永久的期盼,还是保持纯净信仰的佑护。
张承志《心灵史》里反复提到“水”对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水,是伊斯兰教净身进入圣域时的精神中介。水又是净身时洗在肉体上不可或缺的物质。”[6]在他看来,“水”是穆斯林通往“清冽的幸福泉”的中介。他说:“无水无村窖雪度夏,而坚持宗教沐浴的回民却家家以水的清洁为首要大事;那些盛一瓢泥汤脏水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留着那么干净的水洗澡。”[7]因为水最清洁、最珍贵,用最珍贵、最清洁的事物洗去的是纤尘世俗,换来的是心灵的纯净和精神的高贵,这是最有意义的。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月落》一章,描写新月接受最后的洗礼,“清水静静地洗遍新月的全身,又从她的脚边流下‘旱托,竟然没有一丝污垢,她那冰清玉洁的身体一尘不染!”[8]不仅充分表现着女主人公善良、美好、智慧的形象,也更加凸显了这个民族对水的“洁净”至高无上的崇拜。
石舒清的小说本就像一汪清水汩汩流淌,有温情,有喘息,有激流,更多的是平静地诉说,终究归入精神探求的大海。在他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里,水是反观自我、洞察命运的一面镜子。当主人公马子善老人明白献祭的老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看到清水里的刀子后,就不再吃喝,为的是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内里,然后清清洁洁地归去。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在他内部的视野里,就有一盆清得让人像涟漪那样微微颤栗的水。在这水里,慢慢就会生出一把世所罕见的刀子,在清水的深处像一种蕴藏的秘密那样不断地向你闪耀着银光。”“又想起槽里那盆净无纤尘的清水,那水在他眼前晃悠着,似乎要把他的眼睛和心灵淘洗个清清净净。”[9]整个小说的触发点在于一盆清水。清水的出现,让老牛看到了死亡,让老人理解到老牛对死亡的坦然。由此引申开来,感悟到一个人干干净净、身无罪孽、从从容容离开人世的可贵,于是,水有了一种神性的魅力,一个民族对生命的理解也由此展现出来。作家也从对平民的观照中发掘到出人生的真谛——清水般的心灵!
青年作家了一容以多年流浪的苦难经历,在小说中见证了水的宝贵。他笔下的水往往成为救命的稻草,“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水,是水!……他趴倒‘咕咕咕贪婪狂醉地喝着柔甜的泉水”[10],有时候在苦焦的土地上水是苦涩的,“那学校沟底下的一大坝清水,竟是牲口都不愿饮的苦水。”[11]有时候是神奇美丽的,“远处,河水显得清澈、滑溜,在下午的太阳光下,像一面玻璃抑或镜子。”[12]有时是浑浊不堪、像迷途的人一样辨白不明,“水凉森森的”[13]。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一个用轮椅推着瘫痪的儿子尤素福四处求医、沿街乞讨的老人,“每当她用汤瓶里的水细细地倒出来洗着自己的时候,便希望这水能把自己的心和脑子也洗干净,好让自己远离浑浊、远离杂乱的意念,变得纯粹和清明起来。这样,她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活下来照顾尤素福了。”[14]这里的水,跟张承志、石舒清等笔下的水一样,也有了奇异的神性,是治疗尘世伤痛、寻求来世的中介。
审美意象是知、情、意的统一。通过水的描写,回族作家们对以西海固为代表的西北自然地理与人文风情,进行着主体自我剖析式的描绘。在知方面,“水”这个审美意象成了智慧的藏身地,在感情上,是与人、与现实、与来世联系的纽带,在意方面,他们把西北部的自然风物与社会风情始终是作为人的环境,它不再是人类对抗的对象,而是人的生命的对应物。
三、至亲土地,精神之根
人总会跟自己与生俱来的环境发生着关联,作家更是如此。按照丹纳“种族、环境、时代”之三要素说,“黄土高原”构成中国尤其是西北回族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回族作家的创作。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对干涩迷蒙的黄土地极尽描写,“风土是不可思议的——我只能用散文或诗对它抒发一时的联想;我洞彻不了它。”[15]“河沟的冰在远处环绕,犁沟翻起的土壤又重又厚,黑暗中的村庄还在沉沉酣睡,为明天的辛苦积攒着力气。”[16]这是一种大地给予的无比艰辛的生活情境,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回回们从不抱怨,始终用一个颗感恩甚至虔诚的心灵面对着这种艰涩,凭借一种本民族特有的精神和心灵追求——宗教信仰,默默地与自然环境斗争、相伴,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于是他们就在这种人世的绝境营造了精神的净土,并在这信任的土地上生息。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就像提炼了中国人热爱自己祖国的感情一样。”[17]张承志就是张承志,通过一种令人近乎窒息的激情的表述,把生活在那片干涸土地上的回族人民衬托得可歌可泣,引人入神。
另外,许多回族作家的创作源于大西北的广袤黄土,是在荒凉沉寂、少有人烟的环境中想象的结果。石舒清的小说集《赶山》,以及《月光下的村子》、《沉重的季节》等作品,就将历史情境放在西北一隅(主要是西海固地区),反映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回族种种现实,抒发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深深的悲凉感。小说《锄草的女人》中,对一位农村妇女锄草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女人静默地与土地面对面交流,营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美妙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类似“意识流”一样的思绪也波动不止,他深深感慨于女人与土地的相亲相依。可以说,石舒清的小说主题往往是土地,那是一种对乡土的热爱,一种泯除物我之异、消除心手距离的精神追求。李敬泽在石舒清小说集《暗处的力量》序言中说:“土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乡土,一直是石舒清的主题,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因为那里是西海固,是中国最贫瘠的地方,干旱年复一年地煎熬着人、畜和草木。”“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18]事实正是如此,石舒清对西北苍凉的大自然进行哲理地描绘,使对待土地的民族情感上升为对所有人精神世界的思索,从而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反映出了一种人类的大美,形成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每个人经历的地方不一样,眼界高低不同,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依恋和审美心理也会大相径庭。了一容同样写了很多关于“土”的文字。“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连走了四个多小时的沙石路,然后就开始爬山了。”[19]“狭窄的山路,不是晒干后变得石头一样磕磕绊绊的红胶泥块,就是一脚下去便再也看不见脚面的黄烫土。”“西海固的山大多是这个样子的,没一点办法,风一吹,黄土就刷啦啦地往下淌。”[20]在这些小说里,了一容用他个性化的语言朴实地将本土最真切的一面描述出来,显得凝重而悲壮。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些感觉是悲怆、激烈、血性,对作家而言,正是通过人物艰难的生存,表达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之深、思之切、虑之深。
除了“月亮”、“水”、“土地”这几种审美意象,当代回族小说中具民族特征的意象还有汤瓶、石头、剪纸、礼拜、清真寺、白帽子、长跑、胡子等,正是这些审美意象具有选择与组合的无限丰富性,共同组成了当代回族小说中审美意象的长廊,使回族作家的作品既可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作品,展现民族内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又可以不断地别出心裁,让小说本身就沉浸在一种独特的民俗风景中。虽然回族作家对笔下的意象运用各不相同,赋予的意义也有所差别,但总得看来,还是贯穿着一种对民族的审视和理解,这是穆斯林美好的愿望的真切体现,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也就是说,通过回族小说中审美意象的传承与嬗变,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回族文学发展的明显线索,更能看到回族人民的精神坚守和衍进的艰难历程。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回族文学的审美嬗变历程”,项目编号:2007Y006。)
注释:
[1]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2]张承志:《牧人张承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19页。
[3]张承志:《心灵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第329页。
[4]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5]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303页。
[6][7]张承志:《心灵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第8页。
[8]霍达:《穆斯林的葬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9]李敬泽:《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序言》,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
[10][11][12][13]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第298页,第32页,第88页。
[14]了一容:《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15][16][17]张承志:《心灵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第122页,第11页。
[18]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1页。
[19][20]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第289—291页。
(马慧茹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