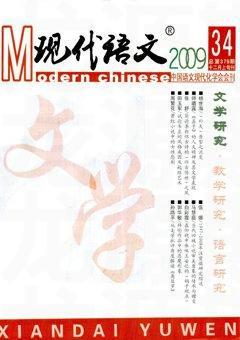捍卫尊严,让爱作主
摘 要: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书写爱情的篇章,其中春秋时期《诗经》中的《氓》与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都表现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与捍卫。本文主要从作者对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女主人公爱情变故的原因及她们对爱情作出的抗挣三个方面探讨比较两者人物形象的不同。
关键词:《氓》 《孔雀东南飞》 女主人公 比较
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中一个生生不息的主题。春秋时期《诗经》中的《氓》和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这两首叙事诗,都通过塑造美丽、温柔、勤劳能干、忠于爱情的女主人公形象,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这个主题。她们倾注了全部的真爱,却又经历了爱情的洗礼和婚姻的变故,成为被压迫、被蹂躏的弱者。为争得真爱,捍卫尊严,她们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抗争,成为文学史上具有反抗精神的熠熠闪光的女性形象。
一、不同手法塑造立体形象
两诗都塑造了美丽勤劳的女主人公形象,但所用手法不同,人物形象也有差异。《氓》主要采用女主人公自述的口吻,采用前后对照的方法来述说婚前婚后生活的变化。诗歌可能作于与丈夫决裂之后、渡过淇水的归途之中,作为弃妇的女主人公的心情悲痛而又惘然,面对着见证了她那段以欢乐始、以悲伤终的爱情生活的淇水,女主人公从以涉淇订约为中心的初恋的回顾,开始了她痛苦的歌唱。当初的她被氓的爱恋与诚意深深打动,抱着对未来爱情生活的美好憧憬,做着温馨而甜蜜的梦,以致于他连媒人都未找好,她就情意绵绵地送他过了淇水到顿丘,温柔地劝慰他不要生气,约他秋天再来结同好。初涉爱河的她像所有怀春少女一样,对自己的心上人如此依恋、痴情,“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经过焦心的盼望,终于盼来了行媒迎娶的归车,“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是涉淇订约的自然延展,是他们爱情的高潮,欢乐的顶峰,然而同时也是以后三岁为妇不幸遭遇的起点。爱情的甜蜜使她怀着“及尔偕老”的念想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家庭生活的一切辛苦与操劳,“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然而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当初面带着嗤嗤然的敦厚的笑,耍着可爱的小小花招,借“抱布贸丝”来向她求婚、商量婚姻大事的氓竟然成了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诗歌就这样在女主人公的喃喃自叙中,在订约前后的对照中,塑造了一个善良温柔、勤劳淳朴的劳动妇女形象。
《孔雀东南飞》则采用铺陈和衬托手法来塑造刘兰芝形象,且兰芝的形象比《氓》中的女主人公更丰满。对其相貌,诗歌通过“新妇起严妆”一节作了大量的铺叙:“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位美丽绝伦、气质高雅的少妇形象宛然如在眼前。而兰芝请遣一节中,她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回娘家后,阿母也如此陈述,可见,她不仅心灵手巧,擅长女工活计,而且能够读诗奏乐,知书达礼,是一个聪颖慧敏、修养高雅的女子。当然她也有勤劳淳朴的一面,与仲卿结婚后,她“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相见日稀,独守空房,不嫌寂寞,昼夜作息,“三日”就能“断五匹”。可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的她却遭到了婆婆的无礼挑剔:“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如此温顺的媳妇在自遣之前,却能想到去拜别婆婆与小姑,“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虽有满腹委曲,却不做任何辩白;她在焦家行为“无偏斜”,确实“无罪过”,却向婆婆作了谦逊的检讨,其温柔善良也自然流露出来。与《氓》中的女主人公相比,刘兰芝的形象更立体、丰满,有血有肉,除了勤劳淳朴、温柔善良的一面,她的身上还带着古代劳动妇女知书达礼、举止得体的美德。
二、不同原因导致爱情变故
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却各有各的不幸。两位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在刚刚品尝到婚姻的甜蜜不久,就与婚姻的变故不期而遇了。但导致和谐爱情变奏的原因不尽相同:前者是丈夫变心,后者为婆婆挑剔。《氓》中“氓”虽然貌似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无感情、无信义、自私自利的人。他以虚假的热情欺骗了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之后,便“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他的欲望一旦达到,便将儿时青梅竹马、言笑晏晏的欢乐场面、将昔日旦旦的誓言和白头偕老的美好祈愿弃之脑后,朝三暮四,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可以说,氓的三心二意,导致了两人的感情危机,从而将两人的美满婚姻送上了绝路。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感情甚笃、爱情甜蜜,导致生离死别、甚至双双殉情悲剧的不是男主人公,而是焦母。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焦母“久怀忿”的不是别的,而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而兰芝自己认为“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显然,“举动自专由”使婆媳产生了矛盾,且演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才华识见尤其是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格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露出来,这种行止见识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害怕和无可饶恕。《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夫妻情深,本是作母亲求之不得的高兴事,为什么焦母不但不高兴,还要想方设法拆散这对鸳鸯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而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
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而焦刘二人感情甚笃,自然引起焦母无意识的嫉妒。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又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另外曹禺话剧《原野》里写了另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我国著名作家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像从前那样爱我。”可见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是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
也许焦母正是因为有着与卡巴诺娃相同的感觉,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和媳妇感情浓厚、恩爱无比,而自己的话却正在逐渐失去威力,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惶恐,她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她从容地使出了杀手锏,动用《礼记》中的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于是,一对恩爱夫妻的命运就这样被焦母重新改写了。
第二,焦母当时正处于更年期综合症。刘兰芝之所以能嫁到焦家去,首先必须通过焦母这一关,兰芝既然已经名副其实地做了仲卿的媳妇,可见,焦母对于儿子的婚姻开始时并不是横加指责的,对儿媳妇百般挑剔是在她进入更年期后的事。据有关材料考证,焦母当时正是五十多岁的年纪,正处于女人一生中一个特殊的生理时期——更年期,这个时期的女人性情不稳,感觉敏感,紧张焦躁,易动肝火,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的焦母对儿子婚姻爱情无礼干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三,刘兰芝婚后无子。从诗中“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看出,刘兰芝和焦仲卿结婚已有几年,但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在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体系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焦母当然可以以不孝之名休掉兰芝。按照当时的制度,女性社会地位及其低下,但如果女性处于家长的地位上,便可对这个家庭的一切发号施令。而没有子女的兰芝理所当然地只能处于被欺凌、被羞辱的境地。
尽管导致二者爱情变奏的原因不同,一为丈夫变心,一为婆婆挑剔,但细究起来又如出一辙,那就是封建家长制和男权制度等传统宗法观念。这才是导致这些美好女性爱情变故、幸福迷失的罪魁祸首。
三、不同觉醒作出不同抗争
尽管两位女主人公都处于被欺凌被压迫的地位,但由于两人所处的背景不同,觉醒程度不同,因而面对强加给她们的婚姻的厄运,她们所作出的反抗也是不同的。
《氓》中女主人公曾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氓”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痛切地感到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平等,面对这种不平等,她有悲伤、有悔恨,要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当她“及尔偕老”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后,她由忍耐、不平转为内心强烈的怨愤,向广大姐妹们发出痛楚的呼喊,告诫她们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既然不能永远执子之手,那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女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多于悲伤的怨恨和清醒之后的坚强。但她的反抗仅仅是出于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本能,出于一种无奈,因为她还不明白,造成她不公命运的是当时社会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男权地位,因而她的反抗尽管可贵,但又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与《氓》中的女主人公相比,兰芝更富有一种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体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面对婚姻的变故,她更多的不是怨愤和悲伤,不是悔恨和呐喊,而是对命运不可逆转的清醒的认识。面对婆婆的挑剔,她清楚地认识到“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请求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为自己争取主动,维护尊严;面对仲卿“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的叮嘱,她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直言坦白“何言复来还”,并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不容乐观的预想,“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面对阿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质问和威胁,她知道哀求不会生效,她也不屑哀求,对前途完全绝望,不动声色地拿定了主意“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被迫再嫁时面对仲卿的“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的讥讽,她强忍内心的悲痛,发出“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的深刻感慨;婚礼那天,她选择了“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的时刻,将自己的纯洁之躯托付给一池清水,以死明志,维护坚贞的爱情;以死抗议,控诉封建伦理道德对善良人性的摧残。兰芝生活于汉末建安年间,而汉末魏晋时期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因而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追求平等自由、维护人格尊严、坚守独立个性的精神,她不只是才貌双全的劳动妇女,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是人性美的化身,她是美好理想与追求的象征,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的人性的光芒将永远引领人们对美好真爱的追求。
爱情的故事每天都有新的面孔。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今天,我们重读两位女主人公的故事,重温她们对待爱情的坚贞,遭遇婚变时坦然面对一切的刚强、冷静与果决的勇气,时隔千年,仍会感受到那种难以言表的强烈心灵震撼。一种精神在昭示后人,捍卫人格尊严,让真爱作主,追求真正幸福。
附:
《诗经·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参考文献:
[1]王爱霞.《氓》,“上以风化下”——《氓》诗与其他婚变诗的比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5).
[2]张海平.流氓之滥觞——解读《诗·卫风·氓》[J].楚雄师专学报,2000,(02).
[3]赵卫华.《诗经·卫风·氓》新读[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03).
[4]邹廷福.从《氓》诗中的婚变看社会的进步[J].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2).
[5]王伟.《诗经》“氓”字考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6]范富安.从《孔雀东南飞》的文化特征看其产生时代[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3).
[7]解国旺.《孔雀东南飞》主题新探[J].殷都学刊,1994,(01).
[8]陈恒恕.也探《孔雀东南飞》悲剧之因[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04).
[9]梁春海.《孔雀东南飞》刘兰芝人物形象的塑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2,(S2).
[10]黄硕.婆媳冲突为哪般——《孔雀东南飞》刘兰芝被休原因再探[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04).
(张萌苗 山东省临沂第三中学高中部 27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