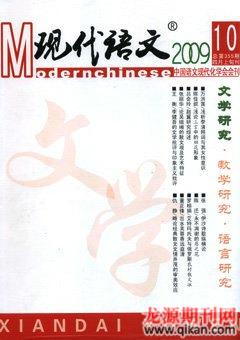论归有光散文中的悲剧因素
梁 莉
摘 要:归有光被誉为“明代第一”散文大师,在明代作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散文成就较高。归有光以其悲剧性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中的深刻悲凉,使其散文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主要体现在悲剧主题、悲剧意境和悲剧精神上。
关键词:归有光 散文 悲剧因素
被誉为“明文第一”的散文大师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他在明代的作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和诗歌,而以散文成就较高。《闻一多诗文选集》称归有光是“散文中欧公以来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归有光的散文集明代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作家之大成,上继汉代司马迁《史记》之文风,下承唐、宋韩愈和欧阳修散文之绪馀,对清代桐城派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明清之际的文坛上起了转移风气的作用。他一生家庭迭遭变故,仕途坎坷不平,直到六十岁时才中三甲进士,这种特殊的人生境遇造就了归有光精神世界的深刻悲凉,并使其散文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因此,研究其散文中的悲剧因素,对了解其作品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归有光散文的悲剧主题、悲剧意境和悲剧精神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所谓悲剧,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谈到:“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同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伟大人物的死亡。”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悲剧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之情”。惟有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时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归有光的人生遭遇可以说是达到了悲的极致。从他的家世来看,归氏在昆山是望祖,曾显赫一时,当时有“县官印不如归家信”之说。他的曾祖归凤于明代成化十年中举,曾任过城武县知县。祖父归绅、父亲归正都没有功名,布衣终生。到了归有光之时,这个大家庭已一败涂地,“源远而末分,口多而心异”;“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冥冥汶汶,将入于禽兽之归。……而归氏几于不祀矣”(归有光《家谱记》)。归有光就是在这个大家庭穷困潦倒之际踏上了人生征途。他自幼聪颖过人,在《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中他回忆道:“余始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朱熹),而能读其书。”到10岁时,他就作了《乞醯论》,洋洋千余字。14岁应童子试,20岁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正可谓少年英俊,文采斐然。然而,好的开端并不等于成功的一半。从20岁开始,归有光就踌躇满志地踏上了乡试之路,然而这条路一走便是15年,他前前后后共考了6次,至35岁才在文毅公张冶的特意选拔下中举。从36岁开始,他又投入了进士的考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前后共考了9次,来往路程共达7万里,直到60岁才考了个三甲进士,可谓苦不堪言。当归有光带着浑身的疲惫、满腹的积怨和远大的报负登上仕途,准备大有一番作为时,却因为他刚正不阿、正直清廉的性格多次得罪了权贵,不断遭到排挤和诽谤,最终病死任上。
归有光一生不仅仕途蹭蹬,而且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的家事遭遇可以说是达到了悲惨的极点:他幼年丧母,中年两度丧妻,连丧一子二女,生死离别,淹然幻化的撕心之痛伴随着他66年的坎坷生涯。
尝尽了仕途的艰辛,经历了生死的折磨,看遍了人世的黑暗,这并没有使归有光消沉,反而让他更加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发内心的悲怆之情。因此,抒写人世间的沧桑与悲凉就成了归有光散文中悲剧色彩最为浓烈的一个表现。夏咸淳《明代散文流变初探》评:“归有光是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既无王、茅的气势,又无顺之的洒脱,却有平淡朴素之美,不事雕琢,而风调悠然。他长于写人伦之间的真挚感情,尤其善于写人间的悲剧,近代古文家林纾说:‘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其《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品。《项脊轩志》是作者描写与祖居之处项脊轩有关的“多可喜、亦多可悲”的往事,抒发了他对封建大家族分崩离析、倾颓衰落的感叹,以及对祖母、母亲、爱妻的哀悼,其文感人肺腑处每每于平易中见出。比如,写项脊轩的闲静安谧,仅用了“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10个字,亲切而有韵味。而当写项脊轩的变迁,写物是人非的惨痛,作者也没有大起大落的笔墨,而是借老妪的闲谈以见之。“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将无限深情寄寓在平淡含蓄的话语中,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效果。
《寒花葬志》中,全文仅用了112个字,即使婢女寒花的形象呼之欲出,其对人生的感慨亦感人至深。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火煮荸荠,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余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这篇文章选取了婢女寒花的三件小事,初来时垂鬟着绿衣裳,不让归有光吃她削的荸荠,吃饭时目眶冉冉而动,生动再现了一个天真、活波的婢女形象,然而她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生命如此脆弱,人生飘忽无常,短短的一篇散文给人的启示却是如此的深邃,怎能不让览者为之愀然动容!在《先妣事略》中,作者从一个过早失去母爱的孝子身份,追忆8岁时曾天真地把母亲的长眠当作酣睡,“见家人泣,而随之泣”的情景,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嘉靖二十七年,43岁的归有光遭受了中年丧子的沉重打击,悲痛至极,在《思子亭记》中写到:
盖吾儿居引七阅寒暑,山池草木,门阶户席之间,无处不见吾儿也。葬在县之东南门,守冢人俞老,薄暮见儿衣绿衣,在享堂中,吾儿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亭。徘徊四望,长天寥廓,极目于云烟杳霭之间,当必有一日见吾儿翩然来归者。
作者曾携子卜居安亭江上,前后七年。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与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现在人亡物在,睹物思儿,其伤心痛楚之情,难以言喻。痛定思痛,就产生了“无处不见吾儿”的幻觉。同时,又借守冢老人的见闻,以“吾儿其不死耶”的幻想,聊以自慰,期盼亡儿复生,抒发了作者对亡儿极度的思念之情。
正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艰辛,尝尽了其中的辛酸苦辣,归有光的散文中才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悲惨凄凉的文学意境。《项脊轩志》末后两节极具情韵,特别是结尾“庭前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平淡的描述中并没有透露出对亡妻的哀悼之情,然而作者实际上句句都在抒情,字字饱含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其中的滋味恐怕是说也说不尽的!比如《女如兰圹志》是为爱女写的一篇墓穴文:
须浦先茔之北,累累者,故诸殇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兰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逾周,能呼余矣。呜呼!母微,而生之又艰。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抚,临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为也?
长期经受生死离别的折磨,让作者由悲生愤,不由发出了对上天的质问“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为也?”其悲痛之情感人至深。再如《见村楼记》中写到:
余间过之,延实为具饭,念昔与中丞游,时时至其故宅所谓南楼者,相与饮酒论文,忽忽二纪,不意遂已隔世,今独与其幼子饭,悲怅者久之。城外有桥,余常与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时其不在,相与凭槛,常至暮,怅然而返。今两人皆亡,而延实之楼,即方氏之故庐,余能工巧匠无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来省墓及岁时出郊嬉游,经行术径,皆可指出。孔子少不知父葬处,有挽父之母乎?
作者通过眼前实景,回想起二十多年和延实父子交往的情景,将浓烈的友朋存亡之感寄托于简洁而富于变化的记述中,正因为他是发自肺腑,得自心源,才尤为感人,让人回味无穷。王锡爵《归公墓志铭》中曾评归氏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
归有光作为一个有远大报负和极具才华的知识分子,身处逆境却没有在逆境中沉沦。在他的散文中,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悲剧精神的体现。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体(人)与否定生命的一切因素顽强对抗、坚定地创造和捍卫生命尊严与意义的一种态度,一种愿望,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种百折不挠的内在意志激情的体现。归有光少时起就怀有济世之志,他曾说过:“余少时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说过:“余少时有志于豪杰之士,常欲黾勉以立一世之功”(《碧岩戴翁七十寿序》),还说过:“余少时有狂简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梦鼎堂记》)然而造化弄人,命运给予他的远远不是他想要的,黑暗的社会阴影时刻笼罩在他的心头,八股科举取士带来的切肤之痛让他终生难忘,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临着外界的种种压力,归有光凭借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与之顽强抗争。正如他在《曹按察简》中所言:“鄙人向年为吏吴兴,虽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与俗人好恶乖方。迁去后,极意倾陷。今幸公道昭明,诸老见察;第越中昔时和声而欢者,犹似有一重障翳。仆随缘到此,宦情甚薄,然大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污蔑。”在他的一些政论文中,常常涉及到民间疾苦和军国大事,写得义愤填膺、慷慨动人,其感情之深、之切,并不在于那些表露家人父子之情的文字之下。例如《送县大夫杨侯序》中说:
东南之民,何其惫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宜有以优恤而宽假之,使展其力,而后无穷之求或可继也。……今民水旱一仰于天,譬之植果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后从而收其实。今则置之硗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其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废,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
作品不仅反映民间疾苦,而且指责了朝廷的靡费,民生疲惫已甚,而天子“兴致太平”,这正是作者所愤慨不平的。又比如在《遗王都御史书》中,作者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严词指责了当时的漕政,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八股取士的受害者,归有光针对当时八股取士制度之流弊,在《与潘子实书》中愤然指控:
科学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之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脱解,以至老死而不悟。
这虽是作者屡试不第心态的真实写照,但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总之,悲惨的人生遭遇是造成归有光一生坎坷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才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成为明代散文中的压卷之作。
参考文献:
[1]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张啸虎.归有光政论散文探[M].江汉论坛,1984.
(梁莉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 21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