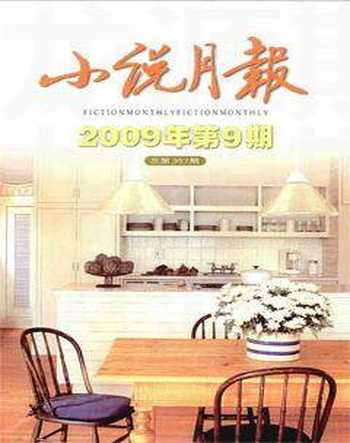好人难寻
红 柯
1
马奋祺年前调到县文化馆,周末回家,老婆娃还在村子里,娃念书老婆种地。看了老婆娃,马奋祺还要去看看王医生和店老板老赵。两个老朋友就笑:“到了县上就没交下新朋友?”马奋祺就说:“我这年纪还交啥新朋友?县城那地方想交也交不下新朋友。”王医生说:“县城还算个城?西安宝鸡还马马虎虎,县城顶多就是个大村庄。”马奋祺跟王医生碰了一杯,“对着哩,对着哩,县城算个屁,就是个大村庄,没啥了不起,又不是北京上海。”王医生的娃在上海念大学,王医生有条件说这话。
马奋祺调到县文化馆,就没开心过,同事们全是城里人,马奋祺一只脚在城里一只脚还在泥坑里,这是同事私下谈闲话说出来的。马奋祺老婆娃在农村,马奋祺想把娃弄到城里念书,跑断了腿连门儿都摸不着,再听人家说风凉话,就气得不行。一个人喝闷酒,都是四五块钱的太白酒。让同事看见又一顿耻笑。“太白,太白是老农民喝的。”城里人喝西凤喝五粮液,牛皮一点的喝茅台。马奋祺连茅台瓶子都没见过。对马奋祺来讲,太白酒很不错了。农民过年过节过红白喜事都打散酒,瓶装太白都是看老丈人用的。狗日的城里人就这么糟践太白酒。马奋祺该捍卫太白酒,人家王医生就用太白酒招待他与老赵。
周末回家,马奋祺就带一瓶太白酒去看老朋友王医生和老赵。王医生老婆做几个菜,把酒装在锡壶里热好,这种聚会越来越让人感到欣慰。王医生说:“老马你好好弄,你看你三锤两梆子就把自己弄到了县上,再弄上几下,把老婆娃弄成城里人,你弄不动了你也不后悔。”对呀!老赵也拍大腿,跟马奋祺碰一杯。马奋祺连灌两杯,细细这么一想,这话实在,马奋祺就拍了大腿。弄!就这么弄!马奋祺就离开镇子。
马奋祺来回骑自行车。二十来里路嘛,对马奋祺来说碎碎儿的一个事情。马奋祺推上车子往出走时,一身酒气,王医生就劝他坐班车,马奋祺跨上车子原地转两圈:“要锻炼哩,再不锻炼,痔疮长成萝卜那么大,狗子受罪呀。”马奋祺和他的车子三摇两晃出了镇子。老赵说:“狗子夹得紧紧的,就像夹了个碎人妖精。”
马奋祺骑车子狗子夹得紧!从村子到镇上到县上大家都这么看。沿途的行人也这么看,马奋祺经过的地方总是一片呼声:“哈,狗子夹这么紧。”“没紧裤带。”“没骑过车子。”最后这句话有点道理,马奋祺就像刚学车子的生手,骑得万分紧张惊心动魄,不要说行人,来来往往的机动车都纷纷让路,马奋祺所到之处,草木皆兵,连路都在摇晃。
县城外边有一个村子,除了本村人以外住了许多打工的,吵吵嚷嚷跟庙会一样。小吃小摊摆在路边,打工的男男女女就在路边小摊随便吃点去干活。醪糟面皮,扯面豆腐脑儿,又添了一家烤烧饼的,芝麻烧饼馒头韭菜合子南瓜合子样样式式。马奋祺从烤馍馍的摊子前边来来往往三四回了,这个摊子刚开张不到一个月,马奋祺第一回路过的时候就想下来吃个芝麻烧饼,大老远就能闻到芝麻的香味,比韭菜、比南瓜还香。那些吃饭的人个个埋头狠吃,性子急的就掂一个热气腾腾的烧饼夹菜合子,或步行或骑车子,车子也有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车子跑得歪歪扭扭,边走边吃边跑边吃,到城里大街上才能吃完。从村子到城里路不长,可拥挤得厉害。再拥挤也得给马奋祺让路,马奋祺的样子太吓人了。奇怪的是没人骂马奋祺,大家多多少少都不大稳当,一手驾车一手掂着吃喝,但也没有马奋祺那么夸张。说到底还是打工的人厚道,没有嘲笑马奋祺的意思。进到城里,大家一边观望一边评点。有认识的还要点明:文化馆的大文人,大秀才,哈哈,把狗座都夹断了。
马奋祺必须在文化馆大门前十几步地方停下来,他不想让他的同事再议论他,他推上车子进单位。从同事的表隋上能看出来,大家啥都知道。就这么大个县城嘛,王医生说得对,跟村庄没啥区别。比村庄富,可也比村庄毛病深。啊呸!啥尿地方嘛,我爱咋骑就咋骑,我想咋骑就咋骑。这都是憋在他心里的话,他不说鬼知道。可大家还是知道了。老馆长说:“老马你想开点。”“我好好的我有啥想不开的。”老馆长说:“这就对了,你就这么想,反正是你骑车子不是车子骑你。”“你说啥?你说啥?”马奋祺急了,老馆长也吃一惊:“哎呀,你就权当耍杂技哩。”把他娘给日的!马奋祺在心里骂开了,马奋祺嘴巴抿紧紧的,马奋祺心潮起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生怕心里的万丈波澜喷涌而出,不可收拾。我总不能推着车子进城嘛,又不是进金銮殿。就在这个时候,鼻子救了他,他闻到了芝麻烧饼的香味。
第一回经过烧饼摊子前时人家卖烧饼的还朝他招呼了一下,他的车子慢下来了,卖烧饼的就掂一个热腾腾的烧饼朝他晃。他只是放慢了速度,他也确实闻到香味,可他的腿不听鼻子也不听嘴巴更不听肚子,他身体的另一半把他硬给拉走了。而且不是一次。第二次他都下定决心了,停下来,吃上一个热烧饼。卖烧饼的还是老样子,热情得不得了,不停地朝他晃那金黄金黄的烧饼。这回不是腿,是身上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他拉走了。这股邪劲儿左右了他两次。他记得清清楚楚是两次。不就一个烧饼嘛,吃就吃嘛。这一回他非吃不可。没等人家招呼他,他就从车子上跳下来了,车子差点倒了,他用力过猛,好像铁道游击队在跳敌人的火车。他的脚本能地一撑,没让车子倒下去。卖烧饼的已经招呼他了:“老板、老板,尝一哈(下),尝一哈(下)。”热烧饼在麻纸里裹着,他就尝一哈(下),丢一块钱,人家找他五毛。他的全部感觉都集中到舌头上了,烧饼又脆又酥,咬在嘴里发出咯铮铮的声音,柔和舒缓,就像灶眼儿里的麦草火,麦草火细发,烙锅盔摊煎饼要用麦草火。人饿急了,也要吃柔和细发的食物。吃酸拌汤吃发面锅盔。这都是马奋祺三十四岁以前当农民干体力活的切身体会。
马奋祺一板一眼认真细致地吃完烧饼,一抬头,正好到单位门口。
马奋祺在门口停一下,往回看一眼,半条街,以往他就那么狼狈不堪地骑着车子奔过来,远远地跳下车,再推上往单位走,那样子不但狼狈而且滑稽。
他曾经谋划过端上一个保温杯,跟个大干部一样从城外一路走来。不成,势太大,那是县长的派头,不适合一个文化馆的小小的创作员。拿上一根烟,咱也不拿“好猫”,拿“猴王”或者“白沙”,抽上一口,走他个十来步,跟蒸汽火车一样腾云驾雾穿城而过。不是县长的人也能这么弄吗。都谋划好了。都把烟打火机备齐了。还是老经验救了他,临上场前,他在房子里演示一遍,吓出一身汗,派头没了,架子没了,势没了,活脱脱一个戏子,在演戏。马奋祺骨子里还是个农民,鄙视戏子。戏子很牛皮的,不比官差多少。老观念作怪,宁可受罪也不沦为戏子之流。马奋祺技穷沉默。烧饼摊子出现了。刚出摊人家就招呼他。他不理人家,人家也不生气,一如既往地招呼他,直到放下架子,跳下车子,亲口尝了一哈(下),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二回吃烧饼马奋祺留了心。从烧饼摊子开始,他混在人群里边走边吃。那些打工的
人吃得又急又快,三口两口吃完一个,又开始吃第二个,也是三口两口吃完,再喝豆浆,豆浆很烫,时间全浪费在喝上了。喝豆浆的占少数,都是工种比较好收入比较高比较讲究生活质量的人,大多数人就是两个烧饼夹面皮,当然是擀面皮和烙面皮。吃肉夹馍的人很少。马奋祺吃得不紧不慢。马奋祺就有了心理优势,就慢下来,就很悠闲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嚼慢咽。烧饼很有嚼头,农民自己磨的面粉,不是面粉厂加了各种增白剂的那种面粉。面也醒到了揉到了。肯定是夜里和好面,发一个晚上,天亮开始做,做整整一天,现做现售。进入大街了,人群少了大半,马奋祺手里的烧饼正好下去一半,另一半可以从容不迫地吃到单位。一手推着车子一手捏着热烧饼,边吃边去上班,一看就是公家人,而且是不太讲究的大男人,不怎么爱护自己,紧紧张张地对付一下,忙啊。男人嘛,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走向单位,没人多看他一眼。马奋祺十分正常地进了单位。
马奋祺并不是每天如此,一个礼拜一次嘛。马奋祺正常了嘛。马奋祺松了口气。马奋祺就想,我干吗老吃烧饼呀,韭菜合子南瓜合子不是很好吗。马奋祺就吃了菜合子。菜合子不耐饿,得吃两个,韭菜南瓜各一个。也不再拘泥于周末返城时吃,周一至周六天天都能吃。想吃就去吃。
2
大概是某周二的中午,马奋祺误了午饭。文化馆人少、且穷,开不起灶,就跟博物馆文体局在一起开灶,灶也不错。相比之下,文化馆事少,基本上是上班到单位转一转,就待在自己屋里看书写作。马奋祺也不例外。文化馆的人错过吃饭的机会比别的单位多多了。别人经济条件马马虎虎,误了饭就上馆子。在小摊上吃没面子。马奋祺把啥都想开了。关键是那个烧饼摊子确实不错。价格又便宜,一块钱就能吃饱。某周二的中午,马奋祺写完一篇稿子,已经快下午了,他写得性起,没有午休,收笔一看表,快两点了。放松了,喝点水,肚子一下子就空了,好像久旱的土地,遇上水反而更旱,这就不是一点点水的问题了,要降雨,让老天爷说话。民以食为天,先吃饱肚子,还要吃好吃舒服。马奋祺在馆子里就没啥舒服过。除过跟王医生赵老板在一起,马奋祺就不爱跟人吃饭。不管是在镇上还是在县上,跟人吃饭顿顿都是鸿门宴,都是阴谋诡计。马奋祺也没指望能在县城吃上个舒心饭。这个烧饼摊子是个例外,例外得让人不可思议,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某周二快下午的时候,马奋祺步行到城外的烧饼摊子上,卖烧饼的早就把一个热烧饼掂到手上了。没有早晨那么多人,挤疙瘩谁也看不清,甚至看不清摊主。现在就清亮多了。摊主是个瘸子,腋窝里夹一条拐杖,身子斜着,挤在人堆里看不出来,单个站着就相当清楚了,掂着热烧饼问马奋祺:“老板,老板来一个?”
马奋祺要了韭菜合子。马奋祺不急着走,坐在小凳上慢慢吃,吃完韭菜合子,又吃了南瓜合子。菜合子就得一块钱,有菜嘛,两块钱一顿饭不算贵。马奋祺点一根烟,抽了一口。瘸子看出了他的身份:“你不是老板,你是公家人。”马奋祺笑笑。马奋祺又抽一口烟。马奋祺情愿人家叫他公家人,他就是公家人嘛,吃皇粮快十年了,叫他公家人听着踏实。叫他老板就相当滑稽了。马奋祺心情不错,马奋祺就指着铁皮炉子上的那个红油漆刷的“烧饼”二字说:“有菜合子呀,咋不写菜合子?”瘸子说:“你就没尝出来?烧饼比菜合子地道嘛。”“我还真没尝出来。”“菜合子有菜么,那种香是菜带出来了的,烧饼纯纯的粮食,做烧饼费的工夫大,烧饼实惠耐饥。”“你把我当麦客呀。”“不是不是,给你实话实说。烧饼是我的拿手好戏,是绝活。”“菜合子呢?”“捎带着做哩。”“你还是个实在人。”“凭这活人哩,不实实在在弄就日踏尿了。”
马奋祺就隔三差五到烧饼摊子上解决午饭。有时是菜合子,有时是烧饼。吃烧饼就在相邻的面皮摊子上要一份面皮,夹上吃有味道,马奋祺就夹上吃。马奋祺去之前泡上茶,回来喝茶温度刚好。热茶下去,肚子就咕噜噜响上一阵子。他拿上一份参考消息,从一版看到四版,可以休息一会儿了。上床之前,再拆开信,是某杂志社来的用稿通知,薄薄的一封信,要是退稿就是个大牛皮纸袋子,就会在同事中间传一圈,人家还一个劲儿问:发了没有?发了没有?别忘了请客。真正的用稿通知就一张纸。人家会把这种信从门底下塞进去。有好几次他都踩在脚底下,信封上的鞋印比邮戳还清晰。他开门时就小心翼翼,特务一样探头探脑观察一下,再转身进门。看完用稿通知,往枕头上一挺,眯瞪半小时或一小时。下午两点半,到办公室去闪一下面,证明他在上班。
大家又有话说了。有人问他:“老马混得不错嘛,灶上饭都咽不下去了。”“得是有人请哩?”马奋祺淡淡来一句:“反正没饿着。”
不出三天,就真相大白,就有人劝马奋祺:“小摊上不卫生,小心传染病。”马奋祺还是淡淡一句:“吃着美就成,谁还管这些。”“那都是打工的吃饭的地方。”马奋祺这下可不是淡淡的一句了,马奋祺嗓门儿高起来了,比得上帕瓦罗蒂了:“打工的咋了?咱就是打工的嘛,咱就给公家打工哩,咱以为咱是谁呀?咱以为咱这搭不是地球?”再也没人说杂点话了。马奋祺头仰得高高地去小摊吃烧饼夹面皮,吃韭菜合子南瓜合子。马奋祺回到屋子喝了热茶,先不急着休息,先到院子里转上两圈,站在盛开的月季跟前,一边赏花一边放肆地打出一串饱嗝,咯咯咯就像装了一肚子青蛙。有时候还大张着嘴巴,拿根牙签在嘴里掏啊掏啊掏出一点点东西,啊呸!吐地上。抹抹嘴问老馆长:“你看我这副球样子像不像城里人!”老馆长就笑:“你是个难日头,你是个雌牙,我认得你了。”“你这是表扬我哩,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人要难日哩,人一难日人就轻松了,人就活出个人样了。”
就在马奋祺成为难日头成为雌牙的这一天,马奋祺又逍遥自在地去摊上吃烧饼夹面皮。马奋祺意外地碰到了瘸子的疯子老婆。马奋祺听相邻的卖面皮的女人说过,瘸子的老婆是个疯子,只知道吃只知道屙只知道生娃娃,除此之外啥都不知。马奋祺就说:“那不是个累赘嘛,正正经经娶个老婆嘛。”“好端端个女人谁愿意嫁个残废?”“人家有手艺,能挣钱。”“摆小摊子又不是开大饭店开大宾馆,又不是挣金山银山,想娶个好端端的女人做梦去吧。”这话是当着瘸子面说的,瘸子也不生气:“说的是实话,说的是实话。”卖面皮的女人就笑:“他喜欢疯老婆喜欢得不得了。不信你问他。”瘸子笑眯眯的:“我不心疼我老婆我心疼你呀。”“你挨刀呀。”卖面皮女人的丈夫拉着架子车在一旁咧大嘴笑:“好你瘸子你还想心疼我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要是愿意你就让瘸子心疼心疼你。”“放你娘狗屁,你吃了屎吗你嘴这么臭。”拉架子车的丈夫伸伸胳膊展展腰:“我人不轻省我想歇上几天,谁想顶就顶上几天。”女人马上回击:“大男人这可是你亲口说下的,你可别后悔。”“我不后悔,我有啥后悔的,我歇去呀我又不吃亏。”男人
拉上车子走了。女人摆摊子男人拉车子送货。凭马奋祺的经验,这两口子都是暗藏玄机话里有话。马奋祺朝路边的小摊扫了一眼,果然发现五六米以外的那个卖鸡蛋醪糟的汉子涨红了脸,低着头浑身不自在。马奋祺就知道这是丈夫在向妻子发出警告,同时也警告了这个给人家女人打瞎主意的男人,甭胡骚情,我可不是好惹的。从女人的话里可以听出来,女人不敢胡骚情,女人用另一种貌似蛮横实则惶恐的心态向丈夫表了忠心。往后的日子就平安多了。真正要感谢的还是这个瘸子,他点到为止,夫妻两人短兵相接乒乓两下也不伤感情,那个男子也没丢面子。马奋祺不由得对瘸子刮目相看。
话题又回到瘸子身上。卖面皮的女人说:“他对老婆可真是细心到家了,跟哄娃娃一样,老婆连父母都认不出来了就认瘸子,喊一声瘸子疯老婆就出来。”卖面皮的女人喊了一声瘸子,十几米外的那排房子里就出来一个女人。打一眼看不像个疯子,而且斯斯文文像女教师,甚至有点秀气,等走到跟前才发现那双眼睛空荡荡没有一丝光彩,跟个木头人一样。马奋祺这时候也成了木头人。
3
马奋祺不知道他是如何离开那个小摊的。一连好几天马奋祺都没去小摊上吃饭,也没到单位灶上去吃。马奋祺跟死人一样躺了好几天。差不多快饿死了。大家敲门,喊他,他才应了一声。开了门,他的样子肯定很吓人,把大家吓坏了。老馆长指挥年轻人赶紧往医院里抬。都抬到院子里了,马奋祺才喊叫起来:“我没病我没病,给我吃的给我喝的。”
院子有风,风一吹把马奋祺给吹醒了,也吹出感觉了,最大的感觉就是肚子饿,肚子空了好几天了。
那是大家最热爱马奋祺的一天,马奋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关爱。马奋祺想哭。马奋祺吃着同志们的方便面。那时候方便面刚刚兴起,一般人吃不起,几个爱时髦的年轻人才有这种稀罕东西,都贡献出来了,泡在饭盒里,热气腾腾,吃得马奋祺满头大汗,眼泪汪汪。大家一边看马奋祺稀里呼噜吃方便面,一边七嘴八舌吵吵嚷嚷,马奋祺听到的大概意思是这几天大家以为马奋祺神秘失踪了,甚至有人怀疑马奋祺受到什么刺激寻了短见,城外的北干渠以及几条深沟大壑都去搜寻了。唯一漏掉的就是他的房子,黑着灯,叫半天没动静,趴窗户看,床上空荡荡、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这三四天马奋祺就坐在门后的藤椅上仰望天花板似睡非睡,中途曾经梦游般喝了茶水吃了泡涨的茶叶,后来就处于混沌状态了。同志们再次敲门喊叫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应了一声,这一声还真救了他的命。两份方便面下去,马奋祺就困了,在巨大的困倦中马奋祺朝大家鞠躬,差点摔倒被同志们扶到床上,就彻底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马奋祺没有立即下床,马奋祺睁大眼睛望着窗户外边,天空灰蒙蒙的,阳光里全是灰尘,阳光也是脏兮兮的。馆长来过一次,馆长是个书法家,懂点中医,号号脉,没啥大毛病,睡上几天就没事了。馆长说:“你好好休息,不要想啥。”“我这样子了我还能想啥。”
马奋祺一直等着馆长来询问一些情况,馆长一直没问,他彻底康复了馆长也没问。他竖起耳朵,跟雷达一样高度警觉,奇怪得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再也听不到人家议论他了。他还注意了大家的表情,都很正常很平静。这种正常这种平静让他很不踏实。他开始失眠。看不进去书,写不成东西。让电灯泡白花花地把他照着。那时候的养鸡专业户已经开始用大功率的电灯泡彻夜地照射母鸡,母鸡们让老板如愿以偿,每天下两个蛋。马奋祺听到的议论也是与他专业有关。你看人家老马,熬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熬出来的可是文章呀,那可是精神文明。马奋祺的耳朵竖得尖尖的,跟刀子一样,有时马奋祺还问人家:“你还看到啥?”“电灯泡嘛,亮一个晚上嘛。”“那你听到了啥?”“吹风哩,蛐蛐叫哩,还能有啥?”不能再问了,再问就赤裸裸了。人家来一句:“你想听到啥?”他连退路都没有了。他就不敢再问了。他心里就这么想着。他觉得大家已经知道那件事情了。人人都知道了,也就懒得背后议论了。你又没办法问。你又解释不成。
他开始吃安眠药。只安然了一礼拜。再吃就不顶用了,问医生要,医生不敢开,再开就把你吃死了。“还不如吃死算了,把人难受死了。”医生就笑:“那么容易让你死呀,好好活着吧。”
这期间他去了一次卖烧饼的小摊。他还见到了那个疯女人。疯女人还朝他笑一下。还好,这回他没有失态。他甚至伸出手去接疯女人递过来的热烧饼。卖面皮的女人说:“嘿,她能帮上手了。”瘸子也说:“我老婆有救了,能帮我做事了。”也就递给马奋祺。另来一个顾客,就不灵验了,疯女人没反应。马奋祺快撑不住了。疯女人谁也不理,蹲地上抓石子玩。
瘸子的妹妹,大家经常见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一直帮瘸子做生意。其实大多时间在照顾疯嫂子。姑嫂关系不错,小姑一招呼,疯女人就跟上走了。让马奋祺吃惊的是疯女人还有娃娃,两岁多的一个男娃娃,小姑子抱着,在十几米外的房子前边玩儿。租的房子,瘸子说他们离县城三四十里路,快到另一个县了,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马奋祺一个月去两次。第二次情况好多了,他甚至看了一会儿疯女人。疯女人这回没有笑。疯女人皱着眉头望着马奋祺,马奋祺低下头,马奋祺感觉她还在看他。瘸子递给马奋祺韭菜合子,瘸子说:“你不用怕她,她疯疯癫癫的,除过我除过我妹我儿子她谁都不认,有时候连我都认不出来。”马奋祺没吭声也没表情。马奋祺往回走的时候听见卖面皮的女人对瘸子说:“把你那疯老婆管好,痴不呆呆瞪着人家,影响生意哩。”
马奋祺发誓再不到小摊上去了。好像在挑战自己的神经,过了两周他又去了。这回疯女人没过来,疯女人在村子里乱跑,小姑子在后边追,追上了又拉不动,就死死地抱住疯女人的腿。瘸子过去,疯女人就不疯了,乖乖跟小姑子回到房子里。这回马奋祺没吃东西,就回去了。马奋祺回去就后悔了,卖面皮的女人又会抱怨影响了做生意。
有一天,县城联合进行扫黄打非,文化馆的任务是突击检查地摊上的淫秽报刊。收了一大堆,堆在文化馆的院子里,后来全都烧掉了。文化馆想当废纸卖掉,公安局不同意。必须烧掉。公安人员冷笑:“卖废品收购站,再转到造纸厂,你以为会捣成纸浆呀。”老馆长说:“对呀对呀,废物利用嘛。”公安人员就一板一眼地告诉老馆长:“有三分之一能捣成纸浆就不错了。”老馆长真是愚到家了,还追问那三分之二,把公安给气笑了:“你个蔫老汉你都蔫成茄子了,碎娃们可都是生瓜漏,专偷你这三分之二。”公安出去的时候还嘟嘟囔囔文化馆里咋都是老古董加小古董。按要求要写一份报告,对这些淫秽报刊进行归类综合。这是老馆长的强项。老馆长却把这个重任交给马奋祺,马奋祺推了又推推不掉就接下了。老馆长还说:“说不定还能给你提供写作素材呢。”
马奋祺还真找到了几个好素材。马奋祺很兴奋,话也多了,也爱跟大家交流了。大家也都关心马奋祺。
马奋祺已经成县上的名人了,作品越来越多,重要的刊物都发表他的作品了。传说有可能给老婆娃农转非。别人问马奋祺,马奋祺就神秘一笑,真假难辨。老馆长让马奋祺写材料,也有交班的意思。
马奋祺对这项任务很重视,也很扎实,用了整整一个礼拜。眨眼到了周五,可以收尾了。有个同事又转交一份材料。大框架出来了,往里边一塞就可以了。马奋祺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马奋祺抽一根烟。马奋祺快两个月没回家了。都是那个疯女人给闹的。文人脆弱呀。马奋祺好像在等一件事情。马奋祺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马奋祺确实在等一件事情。马奋祺打开新资料看了一会儿,五六份呢,都是描写妓女堕落的详细过程,几乎都有一个程序,纯洁少女被色狼欺骗失身,进入非正常生活。其中有几例,还生了孩子,孩子与未婚妈妈的悲惨遭遇。有的疯掉了。在疯掉这一段画了杠杠,用红笔画的。马奋祺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坐下。他知道此时此刻许多双眼睛从不同方向盯着呢。同志们也太小看他的心理素质了。马奋祺抽一根烟,不到半小时就把材料整理出来了。不就加两页纸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喊小戴。小戴是新来的小伙子,打杂的,他吩咐小戴找打印部打出来,明天交给老馆长。那时候还没大礼拜,周六要上班的。对马奋祺来说,已经是休息日了。马奋祺迎着众人隐秘的目光站在院子里,扩胸扭腰转体,活动筋骨。
马奋祺到商场去挑了一个电动玩具汽车。马奋祺到小摊上去吃了烧饼夹面皮。瘸子的妹妹抱着小孩过来了,瘸子说:“你不要来嘛,你看着你嫂子。”“我嫂子睡觉哩。”马奋祺结了账,马奋祺说:“我喜欢碎娃我抱一抱碎娃。”瘸子很高兴:“你想抱就抱。”马奋祺就把娃娃抱起来,两岁的娃娃很沉的,农村人的习惯不能说娃娃沉,要说娃娃乖,最好是摸摸娃娃的小牛牛。马奋祺摸了牛牛,娃娃没哭,还咧嘴露出豁豁牙笑哩。卖面皮的女人说:“他妈是个疯子,娃乖得很,又乖又灵醒。”瘸子说:“我娃八个月就会叫妈叫爸了。”卖面皮的女人说:“叫他疯妈他疯妈答声哩?”瘸子说:“不答声,也不闹,就痴勾勾看着娃娃,没反应,有反应的话就能治好。”马奋祺说:“你这当家的不容易呀。”瘸子说:“给自己过日子哩有啥容易不容易的。”马奋祺就把电动玩具汽车掏出来让碎娃玩儿,碎娃喜欢得不得了,不跟大人玩儿了,趴地上玩儿汽车。瘸子急了,硬往马奋祺手里塞钱:“我不能收你的饭钱。”马奋祺说:“我喜欢碎娃,没别的意思,大人是大人,娃娃是娃娃。”瘸子说:“我又没给小汽车的钱嘛,你让我的面子往哪搁?”卖面皮的女人做出裁判:“老马你是公家人,你也要理解我们,你给人家娃娃送个玩具,人家请你个客在情在理,烧饼钱你得收下。”马奋祺就收下烧饼钱。瘸子就松开手。瘸子手上劲很大,抓着你你就别想动弹。
4
马奋祺彻底放松了。马奋祺老婆娃农转非也有眉目了。马奋祺两个月没回家了。马奋祺先不回村子,先到镇上见王医生赵老板。老朋友见面无话不谈。王医生说:“两个月不见个影子我就知道你弄大事去了,老婆娃的事比啥都大。”三个老朋友这回喝的是西凤酒,老赵说:“等老马一家进了城,咱到城里吃老马去。”又碰了一回酒。
马奋祺酒后吐真言,告诉两个老朋友:五六年前广播站那个疯掉的姑娘嫁了一个瘸子,在城门口卖烧饼。王医生赶紧问马奋祺:“她认出你来没有?”
“我没想到她疯成那个样子,只认识丈夫小姑子和她儿子。”“她还有儿子?”“儿子又乖又灵醒。”王医生和老赵就像听神话故事,大眼瞪小眼,让他们更惊奇的是马奋祺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痛苦。当年那个镇广播站的姑娘跟马奋祺好了一场,怀了娃娃,在王医生的私人诊所刮宫后疯了,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三年四年五年,写快板编故事的马奋祺几经磨难,影响越来越大,离开镇文化站调到县文化馆当创作员。真是山不转水转,在县城跟疯女人碰上了。
马奋祺很沉痛地告诉王医生和老赵:“我最操心的是她嫁了啥男人。嘿,是个瘸子,身残心不残,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女子嫁了一个好人,你说,你说,嗨,还有啥说的!”马奋祺脑袋往后一仰,半躺在凉椅上,又是伸腿又是展腰又是舞胳膊:“我最担心的是怕她堕落。前一响配合公安局扫黄打非,收缴一大堆黄色书刊,乱七八糟都是女人如何如何堕落,天天看这些东西,把人刺激的。最后还要让我写材料,把他的,我差点爆炸。女娃是个好女娃啊,她后半生出个啥事,我一辈子良心不得安生。”
王医生冷冷地问马奋祺:“你现在安生了?”
“那当然了,我隔三差五去她丈夫的小摊上吃烧饼。”
“照顾生意?”
“话咋这么说哩?我要细心地观察观察,我发现她丈夫是个好人,细发得很,比她父母都好,你说这么好的男人全世界有几个?好人难寻,好人难寻呀!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老赵说:“这挨屎的吟开了唱开了,这挨求的。”马奋祺站起来,走过来走过去:“你不要说我是挨尿的,你就说我是挨刀的,挨刀的马奋祺,我比挨上一刀还要痛快,今儿上午我给瘸子的娃娃送了个玩具汽车,我还摸了碎娃的牛牛,我一下子轻松了,展畅了。”王医生还是那么冷冷的:“有你挨尿的不轻松不展畅的时候。”
马奋祺当下就硬在那里,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话,只有出气声。中间王医生老婆进来倒一次水,气氛不对,女人没言语躲出去了。马奋祺硬了十分钟,自己把自己解开了:“老王你是咋了嘛,怪声怪气的。”王医生还是那么不阴不阳:“那是你自己怪,你就觉得我怪,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怪。”马奋祺声音大起来:“你明明是扫我的兴哩嘛。”王医生还是那么不阴不阳:“我咋能扫你的兴,我是给你助兴哩。”马奋祺当下就蔫了,马奋祺指着王医生的鼻子:“你你你。”王医生头都不抬,只管喝茶。
马奋祺推上车子都推出小镇两三里路了,还推着走。熟人越来越多,熟人就叫:“老马老马,你不骑车子咋叫车骑你哩?”马奋祺往手上一看,我的爷,手里有一辆车子嘛,把他娘给日的,嗨!王医生王医生,你咋是这么一个狗东西!这么一骂,马奋祺就上了车子。
很快到了家,见到了老婆娃。都怪王医生扫了他的兴,他整个人都蔫了。老婆以为他病了。他说没病。老婆吓得不敢出声,儿子上中学了,儿子也怯生生地看黑脸父亲。马奋祺就难受了,我这是干啥哩嘛,把老婆娃吓成这样子。马奋祺就大模大样咳嗽一声,摸一下下巴,跟个大领导一样,沉着脸告诉老婆娃:再等上一两个月,你俩的户口就迁到县上了,把屋里收拾收拾,该带的带,该放的放,该送人的送人。老婆还愣着,儿子叫起来,“妈哎,咱吃上商品粮啦,咱成城里人啦。”老婆就笑了:“这么大个喜事还沉个脸,我以为把祸惹下啦。”屋里当下就热火了。
老婆眨眼做好了饭,油饼鸡蛋酸拌汤,不是一个人吃的,是十来口人吃的。老婆把村里
有声望的人都叫来了,满满坐了一炕。老婆把平时攒下的烟酒都拿出来了。全村人都知道马奋祺全家要进城了。大家高兴。村里出个文曲星。老婆心细,老婆发现丈夫心里不展畅。村里人可不这么看。这么大个喜事你看人家马奋祺,不惊不乍,脸沉得平平的,干大事的人都这样。大家都觉得马奋祺了不起。
马奋祺回到单位,还是蔫蔫的。他没心思去小摊上吃饭。他返回城里过烧饼摊子时混在人群里混过去了,好像那是个关卡。有好几次他误了午饭,就鼓起劲去吃烧饼夹面皮。都走到大街上了,都看见烧饼摊子了,腿脚不听使唤了,他心里大骂王医生。王医生,狗日的王医生你啥意思吗?你阴阳怪气的你到底啥意思吗?马奋祺等不及了,这个周末就去问王医生,到底是啥意思。
还没到周末,城外出了车祸,女疯子被拉煤的大卡车轧死了,后轮轧的,不怪司机,司机没责任。瘸子丈夫也说司机没责任。疯子嘛,胡跑乱跑,谁也没想到她在路边好好待着,听见喇叭响,不是鸣笛的喇叭,是那种新式大卡车的收音机放出好听的音乐还有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声音。
女疯子就奔过去了,就让汽车后轮轧到了。据说女疯子曾当过播音员,乡镇广播站的那种广播员。听到这个消息马奋祺不假思索地纠正了大家的议论:“不是据说,是真的,她真的当过广播员。”
5
瘸子忙了半年,料理老婆的后事。半年后,瘸子还在老地方卖烧饼。马奋祺到瘸子住的地方,给瘸子的老婆上了香。房东跟瘸子吵过,不让瘸子在房子里放香炉设灵牌,“到你屋里弄去,这搭又不是你屋。”瘸子就求人家,就加房租,总算对付下来了。马奋祺上香时房东的女人往里看了看。马奋祺已经把老婆娃弄到城里了,马奋祺再也不像老农民了,举止间有了些威严,房东女人没吭声走了。瘸子的妹妹大声对房东女人说:看啥看哩,是娃他舅,你把眼窝睁大是娃他舅。马奋祺心里一惊,这个碎女子跟妖精似的,说出这么厉害的话,把房东吓住了,把马奋祺也吓住了。马奋祺把瘸子的儿子,也就是女疯子的儿子抱在怀里,摸摸后脑勺又给娃擦擦鼻涕,“娃乖得很,越长越乖。”瘸子的妹子让小侄儿把马奋祺叫舅,那娃乖得很,连叫三声舅舅,童子声,又脆又响,底气很足,马奋祺就应了一声。瘸子的妹妹说:“娃把你叫舅,你要经常来哩。”
马奋祺就隔三差五去烧饼摊子。节假日就到瘸子住处吃上一顿饭,去时带些礼物。有一次瘸子喝酒喝多了,就哭了,哭他可怜的女人,连哭带说,听得马奋祺头皮发麻。瘸子的疯老婆犯病的时候就脱光衣服。那些流氓混混就趁机糟蹋可怜的女人。女人的肚子莫名其妙大起来过三次,瘸子都打算要这些来路不明的生命了。医生坚决反对,那都是有先天疾病的胎儿。医生明确地告诉瘸子:这些流氓都有性病,个个都是污染源。可怜的女人受多大的罪。瘸子这样结束他的谈话:“车祸把她解脱了,她再也不受这个罪了。……她死得很安静,跟睡着了一样。”
马奋祺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他跟瘸子交往以来唯一的一次长谈。从那以后瘸子就沉默了。一心一意地卖烧饼,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
马奋祺还记得瘸子把疯老婆的死当成一种解脱,他就问人家瘸子:“你是不是想让她死。”瘸子就对马奋祺望了好半天,瘸子说:“我想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打从我老婆第一次被人糟蹋我就想这个问题。”马奋祺永远也不会告诉别人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他第一次在县城外见到疯女人时,他就有这个想法。他甚至想到了汽车。还真是汽车。后来他跟王医生和好了。好几次他等着王医生问他:你心里一定想过疯女人早早死掉,她的存在会让你难堪。这些都埋在王医生的眼睛里,王医生就是不说。王医生不说谁也没办法让狗日的王医生说出来。王医生竟然在马奋祺毫无防备的时候来了一句:“瘸子是个好人,好人难寻,好人难寻呀!”狗日的王医生,你啥意思吗?你说这话你啥意思吗?马奋祺心里胡乱喊叫,就像一条疯狗没完没了地叫。
[作者简介]红柯,本名杨宏科,陕西岐山人,1962年生,毕业于陕西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1986年远走新疆,在奎屯生活十年。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跃马天山》、《太阳发芽》等8部,学术随笔集2部共约五百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及多种刊物奖。现在陕西师大文学院任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