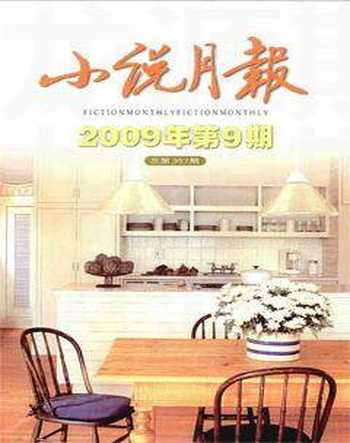分娩
秦 岭
窗外,春夏之交的日头软耷耷的,像只挂在树梢上过了霜的软柿子,悬得邪乎,说不定啥时候会掉下来,泥巴一样铺开。火车偶尔才颠簸一下,总体上比较平稳,这有点像甄满满的大肚子,好久才隐隐感觉到胎动。每次胎动,能感觉到滚圆的肚子有一种荡漾的感觉,像这软耷耷的日头。甄满满巴不得火车像颠簸在崎岖石子道上的拖拉机一样抽搐起来,兴许就能把肚子里的冤家抖弄出来。真的能在火车上或者铁路沿线的某个医院分娩,那就是胜利。但是,我的天!假如蹭到终点站,橡胶气球一样的肚子迟迟破不了口,咋办?
在哪儿破肚,哪儿就是她此行的终点站。
心是铁了的,非得把娃儿生在途中不可,当然最好是在大城市分娩,大城市是庄稼人都向往的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关心她、心疼她、呵护她。说不定,还能拦上一位大领导,顺便告黑煤窑老板孙卫星一状。问题是,分娩的时辰会那么巧吗?人算不如天算啊!甄满满呆呆地凝望着窗外高远的天。空中,大黄风像傻子一样左冲右突。一只孤单的鸟儿,吃力地扇动着求生的翅膀。
甄满满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已经心急火燎地窜了整整一夜,由西向东,毫不吝惜地甩掉了许多村庄、城镇和庄稼地。她的目光像带了钩子,死死地盯着每一个一晃而过的车站。车站就是鱼儿,肚子里的胎儿就是鱼饵。每当某个站台在眼前溜掉,被冷落的感觉像暗夜一样挤压着她,她就情不自禁地用手轻轻挤压肚子,似乎要把鱼饵直接喂到鱼儿的嘴里胃里。甄满满的心颤抖得厉害,呼唤像滚雷一样在她的心尖尖儿上碾压而过:娃儿啊我的冤家,你,你,你你你咋还不给妈出世啊我的冤家!这样的呼唤凄苦而无助,像秦腔戏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某个青衣角儿。八号车厢里很拥挤,一片嘈杂,周围都是衣衫褴褛的农民,一看就是民工的模样。电视里报纸上都说呢,这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中国首当其冲,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不得不返乡。从火车上就看出来了,返乡的比外出的要多得多。
娃他姨,你一个女人家,挺个台面一样的大肚子,咋一个人出门呢?咋就没个人陪呢?
问甄满满的是个陕西腔。
泪就汪满了,却没有溢出来。嘴一咧,就吼起了秦腔。一个清清秀秀的女人家,吼的却是大净的行当:王朝马汉一声禀……刚吼了一句,就拐到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旅客们被甄满满的怪异举止弄得有些发愣,一致的判断是:这个大肚子女人,疯得着实不轻。
有个民工忍不住发出了山西腔:大妹子,这倒春寒的天气,你这是去哪儿呢?
甄满满没有回应,颤巍巍地站起身,学着电视里小妞儿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扭起来。
疯子当然不同于常人,所有的交流就变得山阻水隔。疯子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本来就是未知的无序与混沌。面对一个怀孕的疯子,这样的未知足以让大家在欷歔中放开猜测的翅膀任意畅想,任何人在判断中都有理由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这疯女人也许是被男人抛弃了;比如,她肚子里的娃儿,说不定是遭人强暴留下的种;再比如……
甄满满理所当然成为列车员重点监护的对象。
此刻,甄满满的肚子像极了她的名字,饱满得像个盛足了麦子的麻袋,把一件男式防寒服绷得紧紧的。防寒服是村委会统一发放的,那是城里人为贫困地区农民过冬捐献的爱心。男人张平安并不平安,已瘫痪在土炕上好几个月了,每天被一床破被子夹裹着,像一堆正在腌制的腊猪肉。防寒服就让甄满满穿了,暖胎。
甄满满是偷着从村里跑出来的,她给男人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留了几个字:放心!我生完咱娃儿就回来过日子。
高中文化的甄满满很清楚,这样的纸条首先会使全村人大吃一惊。但甄满满对这样的留言很满意,至少,全村人不会担心她离家不归,更不是为了出门寻死。没人会相信她是出门寻死,四年前她在镇子里上高中时,考上的是南方一所著名大学,但由于缴不起高昂的学费,她偷偷把录取通知书塞进灶膛里烧了,在炕上半死不活地躺了十几天,最后不也挺过来了?人的命啊!不寻死就是底线,有了这个底线,村里因她的出走而引发的一切的一切,即便天塌地陷,都顾不得了。
甄满满是用站台票混上车的。火车一启动,她就唱了一句“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只一句,脸就憋得通红。上中学时是文艺骨干,如今想跑调也难。要想给人以疯子的假象,只有把歌曲和秦腔混着唱。
甄满满察觉下边没来事儿,正是布谷鸟站在麦田边的杨槐树上呼唤开镰的时候,晓得怀上了。当时坡上的山丹丹花儿绽得正旺,爬墙草在低矮的土墙上流淌着墨黑的绿,仿佛流淌着一个柔软的梦。这梦和甄满满的梦一样,充满甜蜜的憧憬。男人张平安就是那阵子出的事。男人在孙卫星的黑煤窑打工。塌方的时候,男人正好在窑口,幸亏只砸断了两条腿,而井下的十几名矿工就没有这命,通通被阎王收了。矿工事先和矿主孙卫星签了生死簿,死了的也就死了,伤了的也就伤了。事后孙卫星拿出了一些钱抚恤遇难者家属,并承诺煤窑恢复生产后,优先招收死难者的亲友下井,说这叫人道主义救助,把亲友们感动得涕泪一片晶亮,像阳光照在脸上。
孙卫星的煤窑没几天就重新开张。甄满满被照顾到矿上,给矿工们做饭。
甄满满咬牙切齿地对躺在炕上的张平安说,我要告!
张平安惊讶地问,告?告啥?
甄满满说,到处都是黑煤窑,这些年,人都死几茬儿了,咱庄户人的命难道就这么不值钱?
为这句话,张平安差点气疯了,他几乎忘记自己早已断了双腿,似乎要从炕上腾地站起来。他说,满满你简直是疯了你!没有黑煤窑,咱庄户人从哪里挣钱去?再说,煤窑都是乡政府的财政柱子,你往哪里告去?真的告垮了煤窑,你还能找到在矿上做饭的活儿吗?那不是自个儿作践自个儿吗?
明晓得这是个偏理儿,但偏理儿也是个理儿啊!甄满满就不吭声,泪哗哗哗地下来了。要说,男人比她更懂法,当年一起上高中时,男人在全乡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中,获得过第一名。
男人光手术费就花去了三万元,孙卫星那五千元的人道主义救助远远不够。不仅搭进去了所有的家底儿,还把唯一的一头猪、一头驴和过冬的小麦卖了,外边还欠了一万元的天债。日子像暴风雪后的秧苗,整个儿打蔫儿。乡政府、村委会理解她家的难处,送来了一袋面粉、一桶食油。甄满满晓得这是报纸上常说的爱心,面对摄像机镜头,甄满满扑通一声跪下了。
甄满满是在院子里给干部们下的跪,这一切,全被窗户上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捕捉到了。张平安歪歪斜斜地瘫在炕上,腰部以下打着石膏和钢钉,缠裹得像个大木桶。
等甄满满进了屋,张平安说,满满,我给你说三件事。
甄满满说,你啥也别说了,我晓得你要说啥。
张平安说,你根本就不晓得我要说啥。
甄满满清楚,张平安肯定要给她安排今后的日月。堂屋里躺着病魔缠身的公婆,娘家那边也穷得丁当作响。妹妹环环在镇子里上高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凭自己高考的经验,环环考大学至少有九成的指望。这几年的学费,都是张平安用矿上挣的钱帮小姨
子添补着,否则环环早就变成了城里人家的保姆。张平安一瘫,环环就断了钱路,今后考大学就更成了云彩,风一来,就散。甄满满说,平安你三件三十件三百件要说就说吧。
张平安平静地说,没那么多,就三件。第一件事是你还年轻,以后还要过日子。
甄满满说,你这不是白说嘛。
张平安说,我没有白说,我晓得你心好,赶你走你也不走,我的意思是,趁你还年轻,你就傍了孙卫星吧。我晓得,他心里一直没有放过你。
张平安说到这里,竟哈哈哈哈地放声大笑了。笑声很恐怖,像从枯井深处传来。甄满满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甄满满这才发现,男人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毒鼠强瓶子,瓶口像死神的嘴一样洞开。
天哪!甄满满的喉咙里滚出了一声轻吟,像豹子一样扑了上去。
甄满满硬是把药瓶子夺了过来,说,你说你的第二件。
张平安说,第二件嘛,趁早,到卫生院把娃儿做了。
甄满满的嘴唇撇了一下,说,第三件呢?
张平安说,第三件嘛,千万不能让环环走你的老路,落得像你如今这个下场,一定要让她考上大学。我敢打包票,你给孙卫星哭个穷,他保准把环环的学费全包了,那狗目的在等你低头哩……
男人说这话的时候,紫黑色的脸上竟然浮泛起一层不易察觉的潮红,干瘪的眼珠子带出了几分罕有的矜持、诡异、机敏和惊慌。只是一瞬,就勾下了脑袋。
遇到往常,男人说出这种话来,满满会啐男人一脸,甚至扇过去一个响亮的耳光,而这次,甄满满啥话都没说,洁白的牙齿咬死了下唇,久久,久久。
张平安的脑袋终于扛了起来,他没有追问满满是否承诺他的约法三章,只是说,满满你把药瓶子给我!
甄满满说,你再逼我,我就连瓶子吞下去。
张平安气得浑身一阵痉挛,像筛糠一样。张平安大骂,满满你个狗日的,我不领你的情,你活该一辈子受罪啊你。
甄满满给婆婆和男人提前做好了饭,就匆匆往矿上赶,矿上几十张嘴,等着她填肚子呢。她没有紧赶,而是轻轻捂着肚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开过怀的女人们早就叮咛过,三个月前的胎儿,娇气,千万不能不当个事儿。
路上碰见妹妹环环。
甄满满有些纳闷,问,环环你不上学,这是去哪里?
环环说,姐,我去看看姐夫,我不上学了。
甄满满说为啥?
问完了,甄满满晓得也是白问,只好把话题转了个弯儿,说,环环,我肚子里有娃儿,你不要气我,你……你你你……你是想坏了我的胎是不是?
环环当场吓住了,用手捂了嘴巴,眼睛睁得溜圆。
环环的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都渗出殷红的血了,说,姐姐,我错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高中读完的,我将来即便当婊子,也要上大学。
环环这样说其实是有由头的。环环利用暑假在矿上的歌舞厅里打工时,孙卫星就给环环说过,环环,和哥哥睡一觉,五百元,干不?
环环说,不,哦,也不叫你哥哥。
孙卫星说,傍了我,将来上大学的学费我全包了,干不?
环环说,不!
环环像一株嫩玉米,浑身上下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环环比满满长得好看。中学生环环让孙卫星想起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满满,想起什么叫花儿绽放的模样。拿下环环,满满会失败得更惨,他胜利的旗帜会迎风招展。
女人从怀胎到分娩,得去乡卫生院检查好几遭,就像伺候庄稼,从下种到人仓,要经历间苗、薅草、施肥、喷药、收割、打碾等十几道工序,缠人着哩。满满第一次去乡卫生院时是八个月的肚子,大夫摸了摸她的肚子,按了按她的肚子,听了听她的肚子,然后是抽血,化验,建立档案,最后张口说个数,甄满满口袋里仅有的一百元零八毛钱就全部奉献给农村医疗事业了。缴完钱,满满就愤愤地想,除了分娩,卫生院坚决不来第二次了。
回矿山的路上,迎面过来了一辆简陋的客货两用小面包车。甄满满认出是矿上的车。她万万没想到车是孙卫星开着的。所有的传言至此得到了证实。都说呢,金融危机使煤矿生产面临灭顶之灾:订单急剧下降,矿上都开不了工了。为了给农民工筹措返乡的工钱,孙卫星不得不卖掉了豪华的奥迪牌小轿车。
甄满满刚要躲,车却停了。孙卫星是邻村孙家湾的,在镇上上高中时追过甄满满,并放出狂言:别看我孙卫星学习差,但是将来是挣钱的料,找媳妇偏要找甄满满这样的校花儿。这世道,我就不信她甄满满不信钱。有次死皮赖脸地把甄满满堵在后操场,被甄满满结结实实扇了两巴掌。说起来孙卫星要比张平安的脑子活泛,但她实在讨厌孙卫星钻钱眼儿的做派。孙卫星中学毕业后,去南方混了几年,三折腾两折腾,兜儿果然鼓了。每次从南方回来,都是衣锦还乡的架势,连乡上的领导都追着他的屁股,求他在故乡投资办厂,惠泽桑梓。报纸上时不时有他捐资助学的报道,很风光的,在这小地方,好歹也算得上名流了。每次逢集碰上,孙卫星就当着她的面显阔,腰杆硬硬的,脖子直直的,脑袋昂昂的,鹅一样。鹅把她当鸭了,鹅比鸭脖子长又长。
孙卫星从车里钻出来,笑嘻嘻地说,满满啊,我咋说食堂里找你不见,你这是忙乎啥呢?
满满说,我刚从卫生院检查完身子。
孙卫星说,下次检查身子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亲自开车送你。你这大肚子,十几里路上一摇三晃的,可不是玩儿的。
满满的回答不卑不亢:女人家查身子的事情,就不劳孙老板费心了。
孙卫星哈哈哈哈的乐了。
孙卫星乐完了,眼眶里竟然罩上了一层潮湿的雾气,这让甄满满心里暗吃一惊。这不是孙卫星一贯的状态。他平时牛气冲天,三十好几了不结婚,养着个城里的年轻女人,逛舞厅,进酒吧,潇洒得很。有次还特意把女人带到了矿上,手挽手从食堂门口走过,把甄满满往死里气。
孙卫星说,你也看得出来,矿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我这是强撑着哩。我要告诉你的是,狗日的尤娜娜,她落井下石,卷了我不少钱,跑了。
尤娜娜,就是那个城里女人。
孙卫星继续说,这城里的臭女人,认我的钱,不认我的人。我如今明白了,她为啥一直磨磨蹭蹭不肯和我结婚,一场金融危机,让我清醒了。
甄满满说,你告诉我这些做啥?你这不是把人丢在我这里了吗?
孙卫星说,以前,一直想到你这里把面子赢回来,如今不这样想了,丢人,就丢到你这里。
甄满满说,你爱咋丢就咋丢吧,别挡我的路。
孙卫星没勉强,说,生娃时给我说一声,如今生个娃比生金子还贵,得三四千元哪,摊上剖腹产,可不得五千好几,这还不算红包呢。
甄满满说,这行情,我比你晓得。
让甄满满后背沁凉的还有那天的风,风是秋风,很硬,像刀子一样在脸上横拉竖剐。那天的卫生院一片萧瑟和肃杀,遍地是枯黄的落叶,光秃秃的杨槐树把干涩的枝头伸向天空,仿佛在贪婪地寻觅空气中的水分。惨白的墙上,历经三十多年风雨的标语尽管斑驳难辨,但凭着褪色的记忆,依稀记得那是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那标语的颜色还没有完全褪掉,如今若不仔细分辨,基本融入土墙的本色了。
三四千元哪!孙卫星的话又在耳畔响起来。不愿
想的人,不愿想的事,不愿想的话,偏偏又想了,虫子一样,生生地往脑子里钻。
甄满满冷笑一声,昂起了头。即便生猪下狗,也坚决不向他姓孙的低头。
有人却低头了。
低头的是亲爱的妹妹环环,妹妹是把自己亲自送到孙卫星身边的。环环当着孙卫星的面脱衣服的时候,竟吓得孙卫星目瞪口呆。他看见了环环的乳房,少女的乳房,难得一见的美丽、雪白、耀眼的乳房,像早晨初升的太阳。
孙卫星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说,环环,你想干什么?
环环说,哥哥,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身子吗?一次五百元,说话算数?
孙卫星甩手给了环环五百元,说,赶紧把衣服穿上,去上学。
轮着环环费解了,说,哥哥,你这是咋了?
孙卫星说,没咋,哥哥不想动你的身子了,需要学费就找我,千万记住,不要告诉你姐姐。
火车已经进入了河北界,过不了几站,真就到终点站了。满满有些紧张,甚至有些绝望,浑身冰凉得像是停了三天的尸体。她紧紧闭了双眼,让自己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绝。也许是心弦绷得过于紧了,她感觉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在颤抖、在紧缩,五脏六腑被压迫得没有一丁点的空间。她感到了窒息,呼吸急促得像救火的风箱。
一系列强烈的生理反应竟使体内发生了变化,甄满满突然感到来自肚子以下某个部位的疼痛,最初是隐隐的疼,后来是那种撕扯一样的疼。这样的疼痛让她欣喜,让她激动。她明白那是骨缝在悄然开裂。骨缝开裂,就意味着要分娩了。骨缝开齐是需要时间的,快的话,用火车行进的速度比照,也就一两站地的工夫;慢的话,或许到终点站也未必能开齐。好在,骨缝开裂无论如何算是个不错的兆头。
啊——啊啊——
这是甄满满的叫声。甄满满尽量把叫声渲染得夸张一些,虚张声势一些。叫声更像惨叫。满车厢的人毛发直竖。
车厢里瞬间乱了套,像蓄满了洪水的堤坝终于决口了。各车厢的列车员和乘警迅速集中过来。空气中传来播音员焦灼而急迫的声音:各车厢的旅客们请注意,旅客们请注意,八号车厢里有一名孕妇即将分娩,旅客中的医务工作者听到广播后,请您马上到八号车厢来!请您马上到八号车厢来!我代表全体乘务员和孕妇向您致谢……
这声音对甄满满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些耳熟,这大概是所有旅客的共同感受。甄满满从电视里已经看到听到多次了。那天晚上,甄满满守着后来不得不廉价卖掉的黑白电视机,炕上躺着男人张平安。就在那时,新闻频道里出现了耳熟能详的一幕:一个在火车上即将分娩的农妇,得到令人羡慕的救助……电视画面中,所有的人都为一个生命的诞生紧张地忙碌着,衣衫褴褛的孕妇和初见天日的婴儿像上帝一样得到尊重和爱护。镜头在晃动,人们在奔忙,警察在维持秩序,大夫在全神贯注地操作,播音员在满怀感情地解说着全部过程,比如列车工作人员如何就近与地面车站取得联系,车站如何火速与地方医院联系,医院的广大职工如何伸出援助之手为产妇和婴儿捐款捐物……当时的新媳妇甄满满真是一百个不理解,分娩是女人一辈子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咋就那么巧,偏偏赶在长途奔波中分娩,还有比分娩更要紧的事情非得赶火车吗?
当时,男人张平安气不打一处来,说,这个孕妇的男人太缺德,咋能让女人挺着大肚子出远门呢?
甄满满一句话也没说。火车上的孕妇,仿佛为她打开了一扇奇异的天窗,使她窥视到了怀孕的自己。
男人说,满满你咋不搭腔?哑了啊你?
甄满满生气地说,啥哑了?还疯了呢。
分娩,是在一个小站所在的县城医院。
火车属于特快的那种,小站不停,完全是为了甄满满分娩的需要而被迫临时停在这里的。甄满满自始至终像一只病危的大熊猫一样被许多人呵护着,一出站,甄满满一眼就看见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大红的十字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旁边还停着一辆新闻采访车,记者的摄像机在肩膀上扛着,镜头大张,像一张贪婪的大嘴。这些人显然第一时间赶到,个个翘首以盼,像是迎接一个从历史隧道中钻出来的大唐公主。
甄满满不失时机地喊叫起来。
甄满满听见有人在嘀咕:大家注意安全,孕妇是一个疯子。
甄满满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甄满满突然没有任何勇气喊叫了,两腿软得不行,但理智又在提醒她,她必须得喊,使劲喊,喊得越疯效果越好。她还要蹬,要踹,要吼秦腔,吼大净的行当,吼王朝马汉一声禀,吼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记者的摄像机镜头里,她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疯的女人。
甄满满生的是个男娃。甄满满躺在病床上,像一片刚刚抢收过的麦田,经历过一次雷阵雨后,在夏日的小南风中,在雨后的彩虹下,安详而静谧地沉睡着,休憩着。床边的小柜子上放着许多好看的鲜花,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还有一大堆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高档营养品……城市因为她而躁动着、欷歔着、激动着、战栗着,许多人闻讯都来看她,有老大爷,有老太太,也有中年妇女,还有和她年龄相当的小媳妇。人们的目光像春天的阳光,柔软而温暖,轻轻落在她的睫毛、她的嘴唇、她的鼻翼上。甄满满的整个身心完全被这迷人的人间气息湮没了,这让她陶醉,让她痴迷。她有些贪婪地呼吸着周围的空气,安静地听着人们对她的安慰和祝福。
此刻,甄满满竟一时忘了,忘记了最重要、最致命的一件事情,她忘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当有位老大爷问她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到何处去的时候,甄满满才倏然警醒,面对老大爷——这位可以当作自己父辈的老人,甄满满脸色大变,报以恣意的狂笑:哈哈……嘻嘻……嘿嘿……
甄满满希望把自己湮没在安静里。安静的时候,她可以更多地在如何带着娃儿返乡的事情上走走脑子,这是根本。甄满满始终紧闭着双眼,不开一丝缝儿,脸皮绷得很紧,像一块风干的树皮。她不敢正视那些鲜花和礼品,原本不属于自己,看了,眼睛有一种被灼伤的痛感。
护士捧着粉嘟嘟的娃儿来到她的床边。襁褓中那种特殊的味道,分明是来自她体内的气息。她的眼睛先是开了一条缝儿,然后马上就睁得溜圆,眸子里跳跃着通透而热切的光亮,脸上绽放出恬淡而甜蜜的笑容。这笑首先是真实的,是笑的本色。发自内心的笑,从来忘乎所以。护士却被她的笑搞得紧张起来,连连后退,眼睛里游弋着戒备和提防。
在护士看来,疯子怎么会有如此纯粹、如此自然的笑呢?
甄满满急切地伸出双手,几乎是哀求了:给我娃儿,快给我!求你了同志,让我抱抱我的娃儿!
护士吓得面如土色。护士大概被产妇眼睛里闪烁的那种罕见的、逼真的、生动的渴望震慑了,紧紧地抱着婴儿,转身就走。
记不得是啥时候睡过去的,甄满满睡得很死很沉。她梦见这个城市里有许多好心人送她回家。她和孩子都很健康。先是坐火车,再是坐汽车。汽车经过矿上的时候,她发现矿上已经被金融危机冲击成了一片废墟,有个女人在废墟上寻找着啥,寻啥呢?啊啊,看那眼神,不像女人,倒像是一个姑娘,是环环,对了,是环环。
啊啊,亲爱的妹妹,你在一片废墟上,到底在寻找啥?
就在甄满满做梦的时候,晨光已经从窗外飘洒进来了,光线很柔和,和大山里的光线一样,一丝一缕的。有个人风风火火赶到了医院门口。来人西装革履,企业家的派头,自称是疯子甄满满的家属,来接产妇和婴儿回村。
来人黑头黑脸,牙却自得耀眼,怎么看都像个大山里钻出来的煤老板。
煤老板的心都黑,谁不晓得?没有人怀疑院方的警觉和防备有什么不妥。在第一时间,院方首先考虑的是报警的时机。
原刊责编赵剑云
[作者简介]秦岭,本名何彦杰,男,甘肃省天水人,研究生文化。当过农民、农村教师、驻乡干部,已发表作品一百六十多万字,小说曾入选《2001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等选本7&2003年下半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集,多次获全国征文奖、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期刊优秀小说奖、梁斌文学奖等。2002年被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现在天津市和平区文联任职,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