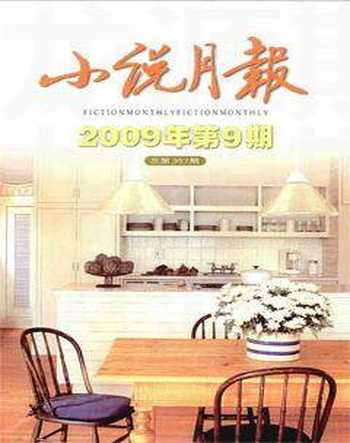考试记
陈 然
那天事情来得很突然。话是宁可自己说出来的,可他自己也感觉猝不及防。前一天办公室小唐送试卷来的时候,股长瞿炎还没来办公室。小唐说,这是你们股几个人的试卷,这是答案,做完交上来,明天我要出差,请叫瞿炎帮我收一下三楼的试卷。他说好。正说着,瞿炎进来了,省了他转述的麻烦。宁可当时正忙着什么,他拿了自己的试卷往抽屉里一塞,心想不急,明天把答案拿来抄一遍就是。这样的考试,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一次,刚开始他还表现得愤世嫉俗,说些风凉话,比如浪费纸张,认认真真做假事之类。可大家都不说,反而显得他太肤浅了。像这样的常识,谁不知道呢,你以为你说了就比谁高明了?所以渐渐地他也不说了。反正是例行公事,把试卷抄一遍交上去。他知道上面也是例行公事。谁都不会认真看试卷。只是他的逆反心理作祟,有时候故意把答案写错(甚至是原则性的错误),或者把后面一题的答案抄到前面的答题框里。可成绩出来,他几乎还是满分。这让他尝到了恶作剧的快感。以致后来,他大胆地把每一道题都答错了,结果他的得分仍未减少。
第二天,大家的试卷陆续送来了。宁可还没做,想找个空再抄。这时股长说,宁可,小唐没发试卷给你吧?他一听有些生气,昨天他拿试卷瞿炎是看到了的,难道做这样的试卷也成了某种特权不成?又不是去什么地方考察或旅游。他说,有啊,怎么没有。股长说,那你交不交?他不禁一愣,心想瞿炎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希望他不交,那好,他就不交,看天能塌下来?于是他平静地说,不交。并且他还补充道:坚决不交。说完这话,他感觉自己的头大了起来,两耳嗡嗡作响,身体好像嫦娥一号似的,被后座的力量从地面推向了空中。其他同事有些惊愕地望着他。股长瞿炎笑了笑,没说什么。
宁可转过头做手头的事。然而他的心思再也不能集中了。刚才还熟悉的字体现在一个个陌生地望着他。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他忽然明白他中了股长的计。他不交,股长正中下怀呢。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收回头呢?他责备自己总是这么不冷静。因为这样,他的性格总是被人利用。股长是个喜欢玩弄权术的人,针尖大的权力也会被他放大成公章那么圆那么大。大概,小唐叫他收一下试卷,他便觉得自己又拥有了某种权力。宁可心想,既然这样,他就硬到底吧,他又不是没硬过。他在乡下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乡政府和保险公司合谋,向教师们强制推行保险,他带头罢了一回课。像这种认认真真做的假事,如果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拒绝去做,那就根本进行不下去,社会也就进步了。
想到这里,他暗暗吃了一惊,你看,一赋予自己某种高尚的行动理由,人就变得理直气壮了。就像那次罢课,其实他当时正在和一个女同事搞婚外恋,想在对方面前表现一下,才冒冒失失那么做的。平心而论,至少有一半原因是这样。
股长带着有些诡异的神色下楼去了。每当股长拥有某种权力,或感觉胜券在握,便会这样。办公室刚才还有些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于娜说,是啊,经常要做试卷,烦都烦死了。何晓刚说,下次我们也学学宁可。于娜说,宁可,你这名字就取得好,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劲头。何晓刚说,要不,我们也改个名吧,你叫于(与)其,我叫何、何……于娜笑着说,你就叫何必好了。
倒是坐在办公室最里边的老涂,看起来跟那个角落一样平静和阴暗,他过来貌似关切地问宁可:小宁,你不是和老婆吵架了吧?或者,你和股长的那个疙瘩……
宁可说,你们别抬高我也别贬低我,我不过手头正忙,不想抄那答案罢了。
何晓刚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上面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以小见大”的实例,比如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其实起因于一个卖菜的老妇和卫兵的吵架,说不定,你下意识的一个举动,会带来机关里的革命呢。
宁可不想再延伸这个话题,便自嘲道,那倒好,我就成星星之火了。
宁可和同事的关系,不管在哪里,一向是这么若即若离的。他不想和同事离得太近。有人说,社会是一个大家庭,真的是这样吗?又有什么好处?不过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的确也是一个大家庭,机关里,大街上,处处可见家庭的痕迹。家庭的阴影在生活中就像嵌在岩石里的恐龙化石。比如经常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单位形象,要多参加集体活动,和同事和领导要多交流。要“交心”。领导说,我们来沟通沟通,交流一下思想感情吧。这段时间你在想什么?问题是,他怎么能把自己想什么也完完全全告诉领导呢?说真话,领导肯定不高兴;说假话,又欺骗了领导。领导给他出难题了。尤其是,很多人下班后还要和同事往同一栋宿舍楼里钻,让人感觉永远也没有下班的时候,单位无处不在,或家庭无处不在。这种太近的同事关系,让人像是走在青苔上,滑腻腻的,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当然也可能是被人从背后推倒的。有时候,他去参观一些古村的大宅院,经常会产生幻觉,仿佛密布的门洞里,会忽然伸出一只暗箭一样的手。
他父亲还在乡下。当年,他几乎是从乡下逃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他努力奋斗其实是为了逃避他的父亲。在家里,从小到大,他几乎时刻处于父亲严密的监视之下。他的每一个小动作父亲都看得清清楚楚。稍不注意,就会听到父亲一声断喝。幸亏他考上了大学,逃离了父亲的阴影,可参加工作后,父亲还想管他,经常进城来,敲开他的门,故意不脱鞋就直接奔进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有时候,坐在那里唠叨个不停,有时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又背着手离去,让他不寒而栗。他在学校,父亲追到学校,后来他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县里的机关,父亲又追到了城里。父亲才不怕他是公务员,似乎他越是国家干部,父亲也因为自己管着了国家干部而兴致越高成就感越大。父亲似乎随时都在提醒他,无论你宁可跑到哪里,都是他的儿子,儿子的地盘就是他的地盘,他有权在他的地盘上为所欲为。
如同和父亲的关系一样,宁可似乎永远也搞不好和领导的关系。尤其是那种贴身管着他的小领导。小领导总是比大领导更像领导。他们不希望手下人比自己强。一个人,如果又强又做了领导,那人家没什么可说;可如果能力强又不做领导,那就麻烦了,会让现任领导寝食不安,也会让同事自惭形秽。总之就是要得罪人。宁可真的不想当领导,也就无形中真的把很多人得罪了。在机关里,最让人头痛的就是这种不在乎。他越说自己没有上进心(股长曾多次试探他),人家越以为他有,甚至还更大呢。他的存在仿佛投下了某种阴影,让别人感到了威胁。仿佛他是一条冬眠的蛇,醒过来会咬人。
要说冲突,他和股长还真的没有过,只是气场不对。又好像两块磁铁,因同极相对,便总隐约有一股向外排斥的力。虽然股长没少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可他并没计较。当然,如果股长对他的不计较也很忌讳,那他只好由他去了。
凭良心说,这次他不肯做试卷,并不是针对股长瞿炎的。但不能否认的是,瞿炎是一个诱因。瞿炎为他设置了一个陷阱,他跳下去之后才明白上了当。
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电话响了。办公室主任周正找他。周正说,是小宁吗?你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办公室主任周正跟人说话向来是这样的口气,明明是通知你,可听起来,却似乎是在同你商量:行不行?好不好?像幼儿园的阿姨。当然,他是男的。
他说,好啊,我马上去。
想到周正,他有些忐忑不安起来。周正是个好人。全单位没一个人说周正不是好人。如果真有人这么说,那听到这话的人一定会认为说话者不是好人。按道理,办公室是事务最多矛盾也最多的地方,什么都会汇聚到那里去,动不动就听到有人吵架,有时候甚至还会打起来。可自从周正当了办公室主任,那里的矛盾就越来越少,从来没人在那里吵架。他仿佛是一架奇妙的天平,一桶生铁和一桶棉花,往那里一放,照样很平衡。如果领导开了什么机密会议,周正总是适当地透露一点风声。当然他不会透露那么多,事后领导知道了,都会在心里暗暗说他透露得好。当然,如果下面有什么心声,他也会向领导反映,让人称奇的是,下面后来知道了,也会说他透露得好,甚至还对他频频表示感谢。作为办公室主任,周正到外地出差的机会多,到北京、到广州、甚至到越南、到俄罗斯,他的出差是公开的,谁都知道。如果你要叫他捎什么东西,他都很细心地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等他出差回来,你要的东西也就跟着来了。所以他的出差往往最牵动人心,大家说,周正快回来了吧?哎呀,我昨天都梦到他回来了。等他真的大包小包地回来的时候,会发现大家都站在那里鼓掌欢迎。宁可刚进机关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懂,都是周正点化他的。周正说,小宁,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找局长申请一笔住房津贴。或:小宁,这次活动你也报个名吧,就是不参加也不要紧,但报了名都会有不错的纪念品。这样的机会,股长瞿炎一般是不会告诉他的,见他错过了什么,瞿炎会发出那种幸灾乐祸的笑声。那次,宁可正急匆匆往楼上走,周正站在办公室门口忽然叫住了他,看来他一直在等着他。周正说,小宁,市里来了一份评先进的报表,你看是不是填一下?他说算了吧,还是给其他人吧。他知道,要想评上这个先进,得没完没了地填表,而且还不一定评得上。他讨厌填表。在中学教书时,他甚至因此而放弃了中级职称的评选。中级职称是有指标限制的。周正说,时间上反正不急,要不,你先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好吗?他只好点头。他以为周正不过是说说而已,这样的机会,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不愁找不到人。没想到第二天周正真的打电话来,问他是不是想好了。他说我还是不想填那个表,周正说,你填嘛,别把它看得太复杂,你只要填一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好了。他说,我……他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么说下去,再拒绝,人家就会说他摆架子,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架子可摆。他只好稀里糊涂身不由己地答应下来。周正说到做到,后来真的没怎么让宁可自己操心,只是碰上不得不需要宁可自己解决的地方,才让小唐来找他。结果出来,他还真的评上了先进,周正比他自己评上了还高兴,一个劲地逢人就说宁可怎么不错。周正说,小宁,你是我们单位第一个被评上全市先进的,很不容易呢,以前报了好几个人,都没有评上。宁可说,那得谢谢你啊。可他心里总感觉怪怪的。这个先进,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并不需要它。它甚至使得股长瞿炎对他的冷漠又厚了一层。这件事也使宁可意识到,某种游戏规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周正的确是好意,但他怀疑很多人正是在这种好意之下不知不觉陷了进去,接受某种游戏规则并开始为它服务的。
宁可在楼道里和瞿炎擦肩而过。瞿炎冲他做了个鬼脸,说,不做怕是不行哩。
他想,这个家伙,居然还在用激将法。
周正正在等他。周正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小宁,坐。
他说,就站着吧。
周正说,坐嘛,别客气,有空吗?我们聊聊。
周正说,我知道你很忙,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事情上,可是我们也是没办法,这点一定要请你理解。
他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只是……
周正在认真地听着,手中习惯性地拿着一支笔,似乎准备做记录。
宁可脑子转了转,心想他该说什么呢?不是这样是怎样呢?是不忙,还是不愿理解办公室的苦衷?然而不管哪一样,都是不行的。
他支吾着,不知怎么说下去。
周正说,小宁,是不是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知道,单位这么大,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有,请你一定要指出来,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呢。
他说,哪里哪里,没有,从来是没有的。
周正说,可是,你……
他说,我……
他想说,早知这样,他像往常一样把试卷做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现在。
周正拉开抽屉,说,小宁啊,我这里还有一份答案,你还是把它做了,好不好?
他几乎要去接了。可他忽然想起股长瞿炎刚才那嘿嘿的笑声,又把手缩了回来。
周正说,不就那么回事嘛,这种事情,做了总比不做好,再说,成绩也许会写到你档案里去,对你以后有影响。
他说,那倒无所谓。
周正说,对你来说无所谓,对我来说就不是这样啊,你不做,我的任务就不能完成,你说是不是?
他说,主任你不知道,以前我虽然也做了,可我故意做错了,而分数还是那么多,这说明他们完全不会看卷子。
周正说,无非是个形式嘛,不管他们看不看,你把这个形式搞了不就没事了?
周正又说,就像开会,你可以睡觉,可以在下面搞小动作,但不可以无故缺席也不可以无故离场嘛。
宁可说,我不做,他们也不一定知道。
周正说,可是我交不了差,你不会是想让我交不了差吧?
说着,他把那份答案拿了起来。
宁可不禁往后退了两步。
周正笑了起来,说你这个家伙,真有意思,把假事看得那么真干吗?假事要假看,真事要真看,你看你,完全弄反了。
他说,主任,说实在的,我不是针对你。
周正依然笑着说,不针对我,那针对谁呢?在单位上,这件事硬是归我管。
他说,如果是别人管,我也会这样,它真的跟你无关。
周正说,你说得好听,可跟我有没有关系哪是你说了算?
他说,那怎么办呢?
周正说,这不很简单吗?周正又瞄了瞄躺在桌上的答案。
他说,我还是不想做。
周正的目光从答案上移开了。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可后来,不知怎么就改过来了,我知道不一定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社会就是这样。
宁可说,我也有三十多岁了。
周正说,跟我比,那还是年轻嘛,是不是?还是年轻好啊。
他说,你也很年轻,真的,我不是恭维你。
周正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不过是运动多,每天晚上都要打球,周末还要去游泳。这些都是从部队里带回来的好习惯。我看你,是好静的人,运动量肯定不够。
宁可老老实实说,是啊,我读书时体育老不及格。
话一出口,他又觉得不妥,主任爱体育,你不爱体育,这不表示跟主任对着干吗?他想
修改一下他说的话,可主任已经开口了。
主任说,你是读书人,用的是脑力,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用体力了。
宁可心想,果然,主任听出弦外之音了。可那并不是他的本意啊,他说的是实话,那些弦外之音是句子自己硬要发出来的,跟他无关。
于是他说,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主任说,甭管什么意思了,事情是明摆的嘛。
宁可说,你弄错了。
主任忽然把眼睛转向别处,叹了口气,说,是啊,我弄错了。一叹气,主任就显得老态了,眼袋沉重地下坠,零星的白头发也在窗子里透下来的阳光里若隐若现。
主任说,那就算了吧。说着,他把那份答案收了起来。
宁可着急了。主任对他那么好,他可不想得罪他。事情变得严重了,别看主任还是那么笑着,可这时他情愿主任训斥他几句,他心里还好受一点,那说明主任没把他当外人。可主任这样,他就心里没底了。他担心主任怪他,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啊,主任对他那么好,主任对所有人都那么好,可是难道他就不能帮主任一点点忙吗?何况这事最主要还是关系到自己。看着主任周正那有些苍老的面容,他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不知道事情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就像他骑自行车上班,下坡时车子忽然发起疯来,他这才发现手闸坏了,于是一切都变得不可控制了。
宁可明白,他又一次中了瞿炎的计。可他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往瞿炎的诡计里无法挽回地坠落下去。
他到会场的时候,座位差不多已经满了。主席台上也已经坐了人。他不自觉地弯了弯身子一排排地张望寻找,以便把自己的身体尽快地插进去。早知道这样,应该来早些。很久没开会了(其实不过半个月)。很久没开会再忽然开会,人便来得特别多。结果,他就走到了最前面的几排。往往是这样,来得最早的人,占住的是最后面的位子。前面倒是有座位。他便迫不及待地把他的身高折叠起来放进去。他松了口气。他听到旁边的座位上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嗨,你好。他低声说。对方以同样的问候回报他。刚才,对方的脸上是多么不幸啊,那么忸怩不安和孤独无助,现在,它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他来了。当一种不幸由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承担时,不幸就会减半。这就是生活的哲学。他们说起话来。嗡嗡嗡嗡的,大家都在说话。开会前不说话又干什么呢。开会前说话就像夏天的鱼群要到水面来喘气。要是不说话,你根本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你一说话,至少还听得清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吧。大家的嘴巴都在动。远远看上去,像是五颜六色的花丛。声音像蜜蜂一样从花丛中嗡嗡飞起,以致后来互不相干,在嘴巴与嘴巴之间无主地流浪着。失去了声音的嘴巴孤零零的,为了战胜孤独,不得不和周围的嘴巴团结得更紧密了些。渐渐地,人也似乎没有了,虚化了,化作气体跑掉了,只剩下嘴巴还在那里一张一翕。
他忽然对说话厌恶起来。他抱歉地对那个在他耳边喋喋不休的人笑笑,然后转过头去闭紧了嘴巴。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不喜欢浅薄和无聊。比如说开会,他要么干脆不来,点名就点名,他不怕。但既然来了,他往往就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一上午,就当自己死了一上午吧。这样一想,他心里就好受多了。一个人,只有他的脑子是活着的时候,才算是活着。现在他后悔来开会了。其实每次都这样,明明知道开会是怎么回事,他完全可以借故不来,但到时候,他还是来了。因为他总是希望这一次或许和上次不同,有些小小的进步。自然,结果总是令他失望。但下一次,他又忘记他的失望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却无力自拔。很多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害怕孤独。他是多么渴望过上一种健康快乐的集体生活啊。上帝把人一个个地创造出来,然后撒手不管了,人因此有义务把心里的通道打开。他们有必要经常性地举行一些狂欢。
当然,这种狂欢,绝不是有着严肃的主席台和庞大的听众席所能代替得了的。在很多时候,会议的目的是蒙蔽、愚弄、强制、灌输或欺骗,就像传销。只不过它传销的是抽象的东西,是荒诞。生物学研究表明,当人体的功能只退守到某一种时(比如听觉),便会厌倦、麻木和昏昏欲睡。
坐前面要什么紧呢?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呢?过于在乎这一点的人,要么是自卑,缺乏勇气,要么就是眼巴巴地也想坐到主席台上去。人,总是先由人少的地方逃到人多的地方来,再由人多的地方跳到人少的地方去。所以每次开会,总有那么几个人,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坐在最前面。他们互相都不说话。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说明他们存在的妥善和必要。
会议终于开始了。现在,大家的很多器官都可以休息了,只要把耳朵摆在那里就行。就像客厅里的花瓶,它们自己,是从来也不会开出花来的。作为声音的容器,耳朵能动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据说还是返祖现象。这时如果把整个会场抽象一下,就只剩下嘴巴和耳朵的关系了。他把自己的耳朵从众多的耳朵里抽了出来,独自换了一个方向,朝着窗外。他希望它们能听到别的声音,比如风、阳光、虫子、小鸟,还有人的其他活动的声音。很多年来,他一直让自己的耳朵洁身自好,拒绝语言的污染。
主席台上的嘴巴咳嗽了一声。那咳嗽从扩音器里振荡开去,耳朵们吃了一惊。不过它们马上心领神会。那咳嗽,是多么的庄严有力、平易近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当人们看到领导不坐进口轿车而亲自走路,便十分感动。看啊,领导亲自走路了,真是不容易。因此可以断定,咳嗽也一定是讲话的内容之一,而并不如某些人所想,是一种流感或支气管炎带来的语音事故。
接着扩音器里放了一个屁。耳朵们不由得面面相觑,好像没有听懂。什么什么?领导刚才在说什么?这时扩音器里又放了一个屁。这回,耳朵听腻了。耳朵有些尴尬,好像看到了领导正在扒女秘书的裤子,有些进退两难。不过它们立时欣慰起来。这个屁以小见大,让他们窥见了领导的平民本色。原来,领导也会放屁啊。
放屁的领导让人放心。当年刘邦在前方打仗,听说萧何在后方买田置地强抢民女,不由得笑逐颜开。虽然这时角色颠倒了一下,但很多人向来就喜欢关心帝王们的传奇,对他们的奇闻轶事津津乐道,好像自己也跑到里面去演义了一把。
他不禁嘲笑了起来。他的嘴巴暴露了目标,像交响乐中不和谐的音符,一下子引起了主席台上的注意。上面因此用了眼睛。他觉得上面的嘴巴和眼睛有一种让人害怕的关系,就像老电影里经常有的镜头:一个什么武装的头目在被堵截的人群面前训话,后面则有几挺机枪在瞄准,随时准备扫射。现在,那两挺机枪就冲着他移了移。
之后,是一个冗长的报告。它逻辑荒谬,又破又旧。耳朵们恹恹欲睡,或者露出一副难得糊涂的聪明劲儿。真是无耻。谁有资格说难得糊涂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难得。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清醒过。他们一直都是糊里糊涂的。他们陷于泥沼无力自拔,便说,泥沼真是一个好地方啊,舒服舒服,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出污泥而不染。
有人开始唧唧喳喳。蜜蜂又嗡嗡飞出来了。这时候,蜜蜂是很安全的。谁会因为一只蜜蜂蜇了人,而把所有的蜜蜂都杀死呢?所以蜜蜂越来越多。
但蜜蜂们似乎失算了。上头把讲话停住,机枪又在瞄准。就像预见了风暴前的乌云,蜜蜂一下子躲了起来。会场重新归于寂静。
他突然站了起来。
有时候,沉默是可耻的。沉默就是接受。说沉默是金的人,应该说沉默是金币。
是的,他站起来了。站起来就是说话,站本身就是无声而最有力的语言。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会场外走去。他的背影毫不妥协。他想,一定会有很多人跟在他后面走出来的。他们的眼睛、手脚、头脑都清醒过来了。说不定,他们其实早就醒过来了,一直在受着清醒的煎熬。但因为蜷伏在各自的妥协和孤单之中,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现在,他第一个站了起来。他要做一只真正的蜜蜂。
但是。
他眼一掠,惊讶地发现他们都低着头,做出一副事不关己和清白无辜的样子。甚至,他们仿佛都不认识他了。他的脚步像雷声一样在地板上滚过,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静寂,可怕的静寂,像一瓶浓烈的油彩忽然被打破,浇铸在他身上。他几乎踉跄起来。他忽然知道了什么才是最可怕的东西。它们铁板一块,毫无破绽,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它们又像木胶一样令人窒息,让他下沉。它们紧紧粘附在他身上。他的高度是那样地刺眼,谁也不能把它折叠起来。但是,这种奇隆的黏性会使他的内心紧缩,身体佝偻。可怕的静寂使得坚硬的地面忽然松软,于是他朝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倒栽下去……
这是宁可经常做的一个噩梦。他本不想进城,也不想进机关,但老婆在工业园的一个厂里上班,下乡很不方便。老婆说,你看你那些同学,你不会托人也调到城里去吗?再说,孩子马上读高中了,自己不在身边,谁帮你管孩子,很多乡下孩子,到了城里成绩就下降,不是上网就是打架,你哪放心?
他没什么人可求,也不会去求,只有发挥他的善于考试的长处。从中学到大学,他的成绩都是第一流的。什么考试他都不怕。就这样,他报考了公务员。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报的是报名人很少的部门,一考就考上了。感谢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可任何机关都是一样的。甚至在学校教书也是如此。同样要填表格,写各种应用文,开各种会议,参加各种检测和考试。
办公室主任周正说得对,就像开会,你可以睡觉,可以在下面搞小动作,但不可以无故缺席和离场。
宁可回到办公室,感觉里面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几个人故意装作没注意到他进来了的样子。股长瞿炎伏在桌前,把屁股搁在椅子上,桌椅的距离很远,好像要把脑袋扎进桌上的文件堆里去似的。何晓刚一碰上他的目光,马上把脑袋转了过去。好像很照顾他,怕看到他的难堪。倒是于娜,飞快地看了一眼他的脸,似乎那张脸刚才在外面饱受了蹂躏,现在热辣辣的,没有了皮只剩下肉裸露在外面。
宁可便知道大家刚才肯定议论了他的事,并猜想他一定不得不拿回了答案。瞧,他当时把话说得多大啊,现在,他被自己的话扇了一耳光,两边脸红红的,很久抬不起头来。宁可拿杯子倒了水,对大家说,那张试卷,他还是不做。
他感觉到,大家再次惊愕地抬起头来。就是股长瞿炎,大概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在楼梯口跟宁可说的那句话,无非是想趁机羞辱一下他。不过宁可注意到,瞿炎脸上的惊愕马上又变成了抑制着的幸灾乐祸,而且它的面积正在溃烂般地越来越大。
这时,何晓刚他们终于正面看他了,劝他说,何必那么认真呢?
宁可说,说句实在话,其实我刚才是准备把答案拿回来抄一遍的,可说着说着,我还是没有拿。
宁可已经做好了准备。让瞿炎之流幸灾乐祸去吧,他要让他们知道,他宁可不完全是中计跳下陷阱的,而是知道那是陷阱,偏偏要往里跳。
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话虽那么说了,可他的心仍在怦怦地跳。他一点经验都没有,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他又将如何去应付。他再次感到了孤单。就是单位上每次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时他感到的那种孤单。不知道是人群抛弃了他,还是他背离了人群。现在,他不仅仅远离了他们,而且激怒了他们。他把像周正这么好的人都给得罪了。得罪了周正就是得罪了很多人,得罪了一大片,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真的后悔没抄答案。即使他是一条不合群的鱼,本来他藏在水底,与人群基本相安无事,现在却自己暴露出来了。
这事似乎马上被单位上很多人知道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他发现大家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它们躲躲闪闪的。如果他抬起头来,它们便四散奔逃,而当他低头走路,它们又迅疾地在他背后聚拢。他们仿佛在自觉地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个人本来要下楼,但看到他在上楼,又踅回去了。一个人在快要跟他碰面时,忽然装模作样地拿出手机打电话。办公室里也静悄悄的,大家说话时彼此很小心,好像办公室里埋着地雷。他的电脑坏了,上不了网,他打电话叫单位上负责此事的小张来看看,小张说,哪位?宁可啊,我现在没空,明天吧,明天再说。他到收发室去看看有没有邮件,远在珠海的小舅子说寄了一个包裹来,好多天了还没寄到,收发室的董阿姨(某位副局长的老婆)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来了我自然会拿给你。听她那口气,好像是他怀疑她故意把单子私吞了似的。他到财务室去报销上次出差的账目,科长说,这几天账上没有钱,等下星期吧。
他不是项羽,却感到现在四面楚歌。
快下班的时候,股长瞿炎又从楼下领来几张表,说叫大家写个季度总结。大家说,又是总结啊。何晓刚说,这简直都成我们中国人的原罪了,谁说我们没有原罪意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便要写些“本年度(或季度)以来,本人政治上如何,思想上如何,纪律上如何,工作上如何”之类的废话。于娜快嘴快舌,看了一眼宁可,问瞿炎:股长,可不可以不写?何晓刚附和道,是啊,可不可以不写?瞿炎也看了一眼宁可,阴沉着脸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有一星期的时间,够你们考虑的。
其实,这个总结写与不写还真的是一样的,一星期后,单位上分组开会,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总结念上一遍,叫述职报告。你不写也要念的。各人念完,由负责人收拢,再每个人发一张表,选举年度或季度先进。一般说来,负责人往往会成为先进工作者。
股长瞿炎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宁可猜想,他大概又向局长“汇报工作”去了。隔不了多久,他便去向局长汇报一次工作。
于娜有些抱歉地说,宁可,我刚才没别的意思啊,不过是随口开个玩笑。
何晓刚说,要是每个人都像宁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老涂在角落里埋着头,什么也没说。
下班时,股长瞿炎请大家下馆子。股里有个小金库,他偶尔会让大家打打牙祭。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虽然上头说,不许各部门有小金库。宁可本不想去。以前很多次他都借机推辞了。他不喜欢酒场上那些虚假的应酬。但这次,他偏要去。他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若无其
事。他和何晓刚骑的是自行车。于娜骑的是摩托。老涂步行。几个人说好时间在一家酒楼的包厢里见面。宁可故意在路上磨蹭了好一会儿,结果还是他去得最早。他在包厢里等了好一会儿,还没见一个人来。他有些发慌,强装镇静又坐了一会儿,还是没人来。也没人打他的电话。是不是他们临时换了地方?
在他准备离开时,才接到瞿炎的电话。瞿炎说,抱歉啊宁可,麻烦你跟大家说一下,我家里忽然有点事,去不了,你叫于娜买一下单,明天再把单子给我。
宁可说,他们都没来。
瞿炎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怎么,他们都没去吗?那是怎么回事?
他明白,他被他们耍了。也许,他们并没有事先商量好,但他们都不希望他去,听说他要去,他们就都不去了。
晚上,宁可辗转反侧,失眠了。老婆呼呼大睡。工厂现在大多被外地人承包,那些外地老板在城里耀武扬威的,说这里什么都贵,就是房子和女人便宜。他们快活地买房和拼命玩儿女人。宁可老婆现在也经常晚上有应酬,要出去吃个饭或跳个舞什么的。孩子倒是听话,不要他操心,即使要操心,也不过提醒孩子早点睡觉。高中阶段学习任务重,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睁着失眠的眼睛,在暗中思前想后。他像是在一个沼泽地里,不挣扎还好些,一挣扎反而下沉得更快。
第二天,他刚到单位,局长就打来电话,叫宁可去他办公室。
局长办公室在另一栋楼上,平时他很少看到局长,所以局长每次到这栋楼来的时候,各办公室里的人都会自觉地站起来,有的人还鼓起了掌。刚来时,他不知道这个规矩,结果局长就认出了他,说,你是刚调进来的小宁吧。
局长的办公室像一艘巨大的舰艇,空旷而壮阔。他一走进去,顿时觉得自己很渺小,好像一只小虫子爬进了显微镜的大倍光照中。局长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等着他。办公桌很光滑,局长的倒影威严地映在上面,看上去有两个局长。
他嗫嚅着叫了一声局长。
局长对面有好几把空椅子,似乎一个小型秘密会议刚刚散场。但现在局长仿佛对它们视而不见。局长是不是唔了一声?宁可没听清楚,只听局长说:怎么样?
他说,是这样的,我……
局长说,哎呀,你这个人,别婆婆妈妈的,爽快一点。
他说,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局长说,这不挺简单嘛。
他说,本来挺简单,可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局长说,你看你,别犹豫了。
他说,局长……
局长说,快点说吧,我刚从外面回来,等会儿还有个会要开。
他说,局长,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
局长说,什么那么多?
他说,我知道,办公室周主任人很好,每个人都很好,我没想针对他。
局长说,你在说什么嘛!
他说,真的,局长,我说的是真心话,就是瞿股长,虽然我和他平时交流少,但我也以为他本质上还是个不错的人。
局长说,你怎么越扯越远了?
他说,可我说的是实话。
局长说,你怎么绕起弯子来了?
他说,我没绕弯子。
局长有些气极而笑了,说,还没绕弯子?
他说,真的没……
他想,他这不是在和局长对着干吗?他说,局长,我……
局长说,爽快一点,去,还是不去?
他试探着说,局长,到哪儿去?
局长说,什么,小瞿没跟你讲学习的事吗?
他说,瞿股长?我还没看到他。
局长说,原来是这样,那好,我告诉你,你上次不是评上了市里的先进吗,现在市里要组织你们到北京去学习一段时间,你没有问题吧?
他说,没有,没有问题,我的确需要学习啊。
局长说,没有就好,你尽快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好,按时去吧。
他说,好。
局长忽然想起什么,说,你刚才想说什么?继续说。
他脸红起来,说,是这样的,那天办公室发了普法考试的试卷,我没有及时做,我怕引起误会。
局长脸色凝重起来,说,办公室事情多,你们要多配合。虽然是个形式,但有时候形式就是内容嘛。这些事情你个人也许以为无所谓(当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对一个单位来说就不一样了,说不定会影响整个单位的形象,一旦影响了,所有人的努力都将白费,年终的各项评比也都将受到影响,对吧?单位形象好,你们在外面也有脸面,单位形象不好,你们在外面就会脸上无光。
他一个劲地点头,他感动地想局长说得真对,如果瞿炎有局长一半的好,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从局长的办公室出来,他吁了口气,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他怀着内疚,到办公室找到了主任周正,结结巴巴地对他说道:周主任,我想通了,请您把答案给我,我这就去抄。
周正看了看他,说,不用了,他已经请人代抄了一份交上去了。
[作者简介]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长篇小说《2003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病院》等。作品多次被多种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