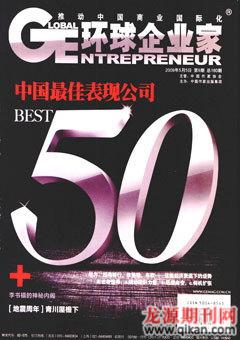贸易决定储备货币
即便是具备操作空间,以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仍然无法实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储备货币的思考引发了极大争议。几个星期之前,他撰文支持运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矫正国际支付中存在的扭曲现象。尽管他对于人民币对美元产生过度依赖的担心或许正确,但是他的以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可替代国际储备货币的提议恐怕更成问题。SDR不是一种货币,而是一种以人为的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财务单位。一篮子货币的权重取决于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所扮演的角色。截至2006年1月1日,SDR估值篮子中各货币所占权重如下:美元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
如果各国以SDR的方式积累储备货币,他们将会有效率地积累一篮子以上货币。但毫无疑问,没有人需要SDR去直接实现这个目标。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相信中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65%到70%都是美元——如果加上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以及中国商业银行的最低准备金,美元的占比会更高。
如果一国持有的美元超过了其外汇储备的44%,并由此扭曲了全球贸易平衡,使货币过分集中,为什么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愿意这样做呢?在人们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喋喋不休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这样一点:没有任何法律上或实质上的规定,对各国中央银行选择购买资产的自主能力进行限制。在过去的十年里,各国央行都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减少购买美元资产,增加对欧元、英镑和日元资产的持有。
问题的答案与地缘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全球贸易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资本和贸易流通的平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须保证其顺差循环到贸易赤字国家。正常情况下,这种循环是通过私人投资渠道完成的。但是随着1997年亚洲危机的发生,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开始大量储备购买外国资产,并由此压缩了私人投资渠道的空间。
贸易顺差国家的中央银行购买的资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些国家会面临贸易赤字。如果各国央行绝大多数购买美元资产,那么美国将成为对应的贸易赤字国。与盛行的观点相反,资金流动并不一定取决于贸易流动,通常情况下,更常见的是贸易流动会带来资金流动。
让我们假设一下,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各央行都决定以SDR作为外汇储备方式。这意味着,假定贸易顺差恒定,他们购买的美元数额只是现实中购买的1/2至2/3。剩下的都被欧元、日元和英镑取代了。
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由于需求的减少,美元对其它三种货币会走弱。这有可能引发美国可交易商品领域的相应扩张,并同时引发欧洲、日本可交易商品领域的相应收缩。伴随着美国可交易商品领域的扩张,以及扩张对就业引发的积极影响,美联储会保证利率维持在较目前稍高的水平,而美国消费在GDP所占比重会相应减少。当然,在欧洲发生的一切会与之恰恰相反。
低消费意味着低进口,反之亦然。在以上假设中,美国贸易赤字会降低,欧洲和日本的贸易赤字会升高,而升高的值大致是前后购买美元储备的差额。当选择购买欧元取代美元时,换言之,亚洲央行迫使相当一部分美国贸易赤字输出到欧洲。
但是,欧洲能够长时间地承受巨额贸易赤字吗?出于复杂得无从讨论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人们有理由相信欧洲没有能力背起巨额贸易赤字的重担。绝大多数亚洲政策制定者也知道这个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美元是世界上的储备货币,而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都用海外需求来刺激国内增长。在1997年之后扭曲的全球贸易环境中,美国一直都是唯一一个有足够的弹性去消化亚洲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制造的巨大贸易赤字的大型经济体,这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或者蓄意为之毫无关系。如果亚洲国家需要以海外需求来拉动国内增长,它们就不得不储备美元,而储备SDR不会达到类似的结果。因此储备SDR抑制美国过剩的贸易赤字也许对全球是件大好事,但对于中国和亚洲绝对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