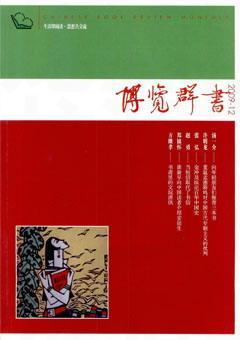莎翁巨作:话剧还是诗剧?
贺越明
今年4月23日,是世界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诞辰455周年。看到中国话剧《王子复仇记》其时在莎翁故里演出并赢得好评的消息,很自然会想到剧中人哈姆雷特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同时跳入脑海的,还有另一句:“莎翁巨作:话剧还是诗剧?”而这一句,是中国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几乎穷毕生之力发出的学术拷问。
孙大雨这个名字,现今文化学术界罕见提及,其生前却非等闲之辈。他祖籍浙江诸暨,1905年生于上海,1925年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翌年赴美留学,就读达德穆斯学院,1928年获高级荣誉毕业,随即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英国文学教授。除了教书育人外,他早年还发表不少诗作,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之一。作为英文专家,又属诗坛健将,孙大雨看莎士比亚剧作,字里行间不免挥发出一种独特的古诗之美。
早在1925年夏天,孙大雨就到浙江普陀山上闭门探索,开始研究新诗的格律。次年4月10日,以“孙子潜”署名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新诗《爱》。这首诗,不仅每一行有五个音节的格律,而且是新诗里第一首完整的意大利体或日佩脱拉克体的商乃诗(Sonnet,亦译商籁体)。此后,他负笈留学期间,又在国内《新月》、《诗刊》上发表《海上歌》、《一支芦笛》和《我的写照》等格律诗,还翻译勃朗宁的《安特利亚·特尔·沙多》和弥尔顿的《欢欣的人》各两百多行,都属于有格律的诗作。陈梦家的《新月诗选》对此有所论及:“十四行诗(sonnet)是格律最谨严的诗体,在节奏上,它需求韵节,在键锁的关联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为他从运用外国的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他提到孙大雨还有一首一千行长诗名为《自己的写照》,“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象,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正是这些创作实践,使孙大雨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莎士比亚,并用不同的文体适译其宏大的剧作。
大半个世纪以来,通过翻译把莎士比亚剧作引入中国的人士,先后有田汉、梁实秋、朱生豪、顾仲彝、曹未风、曹禺、方平、吕荧、英若诚等,均为大师或高才,其中,梁、曹(未风)、朱三位译的都是全集。孙大雨在长年的研究中,对他们的译作无一例外地细读而形成自己的评判。1987年,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第二期发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一文,向前述诸位表示敬意之余,率直地批评道:“曹不了解原作分行是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把原文一行翻成译文也是一行,但并无格律……朱也不明白莎剧原文基本上是用格律诗行写的,也不知怎样用语体韵文传达原作的风貌,故根本不对原文的诗行作任何考虑,完全译成了散文的话剧。”
孙大雨提到,上述先贤中,对莎剧实为“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有所认识的惟有梁实秋,因他在30年代出版的几种莎剧译本弁首的《例言》曾作说明:“莎士比亚的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BI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的排偶体(Rhymed COUplet)。”但梁考虑的结果,“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体裁;莎士比亚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较散文稍为齐整;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演员并不咿呀吟诵,‘无韵诗亦读若散文一般。”但对这一语言上的考虑,孙大雨并不认同:“莎剧在英国、美国舞台上、银幕上演出,虽然并不‘咿呀吟诵,但我们知道是用比较散文据稍慢的速度从容朗诵出来,有协和声调节奏之美,并不‘读若散文一般,因为有格律、有规则的节奏的韵文朗诵跟念散文是有微妙但显著的区别的。”他明确地指出:“莎剧是戏剧,同时又是诗剧,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韵文行所组成,所以古时叫做戏剧诗(dramaticpoetry),近今叫做诗剧(poetic drama),是浑然一体的一种文艺作品。”故而,他翻译莎士比亚的《罕秣莱德》、《黎琊王》、《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罗密欧与居丽晔》和《威尼斯商人》等剧作,无不在掌握原作素体韵文的基础上,出之用音组构成韵文行的方法,以求准确贴切地传达出大文豪语言中精美的诗意。
1951年11月,孙大雨到北京出席翻译工作会议,将他于1948年11月出版的莎剧译作《黎琊王》赠送北大西语系教授卞之琳。此后,卞之琳花了三年时间译出《哈姆雷特》,于1956年8月出版,被孙大雨视为除他的《黎琊王》译本之外,1983年林同济的译本出版之前“唯一懂得莎作原文基本上是有格律的素体韵文、并且译成了中文的素体格律韵文的译本”。直到1986年,卞之琳才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杂志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专刊》他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译本说明》一文中,就孙大雨早年译作所给予的教益和启发表示谢意。在孙大雨看来,这个谢忱整整迟到了30年,但虑及他本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又因“反革命罪”而获刑的经历,这一切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孙大雨和卞之琳,同为早期“新月派”诗人,后者曾师从徐志摩并深受赏识,但鲜为人知的是,前者早年的诗名绝不亚于后者,甚至徐志摩赠送诗作的题款称之“大雨大师”,而自谦“志摩小先锋”。不幸的是,生性耿直的孙大雨,在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中过于天真,以致身陷囹圄数年,出狱复遭监督劳动,无法从事正常的研究,更遑论著作等身,在学有专攻的“莎学”上虽有一家之言,但岁月蹉跎,生前已不及获得更广泛的学术认同和舞台实践的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