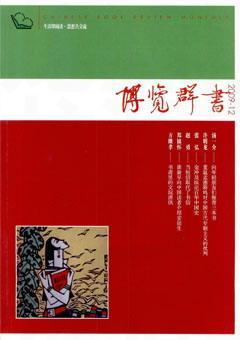何兆武:读书是一种享受
王 正
问:何老您好!请问您最近在读些什么书?
何兆武:我现在不读正经书了,因为没有精力做正经事了,都读点闲书,主要是一些回忆录之类的。因为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所以看着有亲切感。其他的新书就是看报上介绍,某某书怎么样,便拿来看看,不过并不是认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作为工作,某些东西你就得认真地看,而现在读书就是作为消遣,看热闹,和以前不一样,不是一种职业性、专业的看,而是一种休闲的看。学术性的看往往有一个目标,比如我要解决个什么问题,或者我要写一篇关于什么什么的文章,现在没有那个功利的目的。
问:您一生翻译卢梭、康德、罗素等西学经典书籍十余种。在这些书里,您自己最满意哪几种?
何兆武:谈不到满意。不过这些书里面很多都是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做起来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好比一个运动员喜欢踢球,那么尽管他踢下一场球来是很累的,但是他踢完了浑身是汗,却觉得很高兴。所以关键是看你的兴趣。
至于翻译的水平,我可没有严复说的那个水平,这个不能勉强。就像运动员,你不能勉强他一定要打破世界纪录;打不破世界纪录,并不是说他这个运动就毫无意义了。如果你一定要他打破世界纪录,这个就不现实了。
在我翻译的这些书中,我感觉费力费得多的是帕斯卡的《思想录》,因为这本书里的很多东西,跟我们太隔膜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统治的时候,有很多神学问题我们不懂,我们过去也不讲神学,可是他是通过神学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所以翻译起来就比较费力。这就比如说,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研究“文化大革命”,他就必须要明白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想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从技术的角度上说,翻译罗素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的文字非常浅近,非常清楚明白。不像有些个哲学家,文字非常困难,你摸不清他是什么意思。而且罗素的思想也非常清楚明白。另外他对中国的影响也大,从五四起就有影响。当然每一个学者或者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罗素在理论上也有他的缺点。
还有康德也是比较难翻译的。其实,就是他的文字难读,他的思想还是很一贯,很逻辑的。不像当代的一些哲学家,文字倒是很简单,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像康德他们这种古典哲学家,如果能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文字别扭。
问:在您写过的众多历史哲学、文化思考的著作中,您最看重哪几本?
何兆武:其实,我并没有写过一本正经的书,我的书大都是短文的合集。
我对历史的理解是,人类的历史有它的普遍性、普遍价值,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强调一方面,忽视另外一方面。比如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讲什么都把它放在第一位,那你把普遍性价值放在什么地方呢?同样,反过来,你只提普遍性,那大家干篇一律、干人一面,这样也不成。所以,在这两个之间怎样掌握好一个度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现在讲中国特色,可一到了盛典的时候,国家领导人都是穿西装、打领带,这就不是中国特色。不过你能说这个不对么?这也不能说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习惯、潮流、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再比如说解放以前,那时候有重要大典的时候,要人们一出来,都是长袍马褂。其实那个也不是汉族的,是满族的、清代的。这是一个风气,一个时代的习惯,不能走向绝对。
问:现在国学很热,各种书籍和电视节目都很多,您怎么看?
何兆武:国学热这个事情,在近代中国反复几次了。从清末就是中学西学之争,后来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后来一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乃至解放后的儒法斗争,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不如把这个观念改一下,不是什么中学西学之争,而是传统和近代化之争。我们要知道,近代化是在传统里面成长出来的,这就好像一个老人,是从青年时候变过来的一样,你不能把青年时代都否定了,没有青年哪有老年呢?所以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从它的过去成长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写的方块字,那都是几千年演变过来的,不能说我们现在就不要汉字了。这个不可能。可是另一方面,人类的知识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你如果老把老祖宗供在那,认为他是不可超越的高峰,也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进步。因此说,任何东西都是从传统里边演变出来的,所以不能对传统全盘否定;可是又不能永远停留在原来的那个水平上,总是要不断的提高、进步的。
让我开窍的几本书
问:您从小就开始广泛地阅读,在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您感觉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几本书?
何兆武:我想这里面包括哲学家罗素、康德的著作,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著作。司马光如果按现代的标准来说,他应当是个正统的守旧派,不过我觉得他有些看法还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历代文人都是表扬荆轲了不起,包括最超然的诗人陶渊明也说“其人虽已殁,干载有余情”,他还是同情荆轲的。但只有司马光看到了不同,我也认同司马光的意见。他认为,太子丹是荒唐极了,怎么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七寸长的匕首上?如果荆轲刺成功了,你就胜利了;他要不成功,你就失败了。这不是赌博么?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当代中国的著作,我现在看得很少了,觉得好的还是年轻时候读的书。首先是鲁迅。我之所以喜欢鲁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直面地、正面地来看中华民族文化里面的缺点,他有这种勇气,而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勇气。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总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对自己也要这样看,既不是全盘否定一点都要不得,可是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正视自己的缺点。这个很不容易做到。
另外,年轻时候读的一些武侠小说我现在想来也还觉得有趣。印象最深的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它之前的传统的《三侠五义》、《施公案》这种小说里的侠客不过是能力较大一点,武功较好一点,但到了《江湖奇侠传》,他就把法术加进去了,有点超人的味道。我觉得作者的文笔很好,写得很亲切。比如写黄叶道人得道那一段,我现在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
问:您觉得有什么好书可以向读者推荐么?
何兆武:我想首先推荐一本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这是一个小本子,是他的讲演集,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特别前边一部分讲历史的,非常有启发。另外还有克鲁泡特金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这实际上是一部俄国文学史,我也很欣赏。
中国的,我想蒋方震(蒋百里)的文章还是很值得一读的。他是军事学家,但文章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他的杂文,都非常欣赏。还有他翻译日本人朝永三十郎的《近代“我”之自觉史》,也很好,这本书是讲个人自觉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时,仿佛觉得它给开了一个知识的
窗户。当时很多名家都在一个叫做《中学生》的杂志上登文章,给学生做启蒙工作。比如顾颉刚、朱光潜等先生刊登的介绍清初三大家和谈美的文章,都让我觉得自己开窍了一样。因为过去不知道这些东西,而经过他们的介绍忽然看到,就等于人家带你逛公园一样。你发现:啊,原来还有这么一片美丽的风景。
另外,我觉得梁启超的书也很值得推荐。他的《清代学术概论》,虽然是挺薄的一本小书,而我当时的知识就全从那里来的。这本书就等于告诉你还有一片花园、还有一片美丽的景致。所以我一直觉得实在是应当给梁启超更高一点的评价。因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真正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康德;但还有一种人是宣传家,他的真正的哲学思想或者纯学术贡献可能并不算很高,但是他影响大,比如梁启超,包括胡适也是。其实这些人是给缺乏知识的年轻人开辟了新的园地。
读书就是自己的乐趣
问:您作为一位爱读书的前辈,有哪些读书经验和读书心得可以与我们青年人分享?
何兆武:其实也没有什么,非要说不可的话,我想还是兴趣吧。我其实是没有做一个学者的雄心壮志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像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一样,都是好奇,看了书觉得过瘾。也就是说不是很功利地读书,就是自己的一个乐趣,想看,觉得好看。当然也有比如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些对西方、对世界来说,都是基本读物的书,那是必须看的。就像你是中国人,就必须读一点孔子、孟子,这也是基本读物。
至于读其他的学术著作,就是看它有讲得好的地方对你有启发便是了,不能迷信,不能说它字字都是真理。我想看书应当带着批判的态度看,不能带着读《圣经》的那种宗教信徒的态度来看,书里有的地方是讲得好,可是有的地方,你也不必都同意。你应当带着批判的态度,不然人类就没有进步,都停留在原始那个阶段了。字字是真理,那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求知。
西方文化的精华是民主和科学
问:您一生致力于引进西方思想的精华,那么您认为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华是哪些?
何兆武:我想还是近代化的本质: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西方文化的精华也就在科学与民主。
科学如果要广义地说,是每个民族都有的,2+2=4,这就是科学。但近代科学有些不同,它是有系统的、有目的的、有方法的,它是个大工业。这是古代没有的,古代的都是猜测性的。而中国自身的传统没有民主,它有民本,但谈不上现代的民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最核心的是忠孝。
我想科学跟民主是有内在联系的,科学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专制下就发展不了科学。你看二战的时候原子弹是美国造出来的,希特勒原来也想搞。结果没搞出来,可见没有政治上的条件是不行的。不过民主的实现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科学的发展。比如说一个很落后的农业社会,就不太容易有民主。一定要到近代的工业社会,才会出现近代的民主。
问:现在后现代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您怎么看待它?我们又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何兆武:我想中国还没有完全现代化,还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在谈中国的后现代化,可能有点早。不过每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反动、反作用。比如工业化太过分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工业化。确实,人的追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我们的生活幸福不幸福,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如果我们近代化、工业化,仅仅把眼光看在物质财富上面,那就不够了。至于如何治疗现代化带来的病症,这个恐怕还需要慢慢的摸索,没有一个现成的药方。
问:中国的自然科学在世界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可是我们文史哲方面的学术,在国际学术界地位不高。您看我们的人文学科应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发言权?
何兆武:我想还是要多给点学术自由,在学术的领地多给点自由。因为我们过去在学术领域一直是政治挂帅,有些过分,这个不好。现在可以鼓励思想自由,只要不从事职业的政治活动,就不要扣政治帽子。
当然这里面有个人的努力问题,也有整个社会条件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条件不允许你做学术研究,你就不可能搞得下去。又比如现在虽然出版的书多了,不过我觉得,市场性太浓厚了一点,学术性少了一点,市场炒作的更大了一点。当然市场化不可避免,不过不要过分地追求经济效益。
另外,我想学术的发展也和我们现在的学术制度有关系。比如说现在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几篇论文才能毕业,而你如果去写通俗读物的话,它不算学术著作,那么你就毕不了业。所以现在变成核心刊物掌握你的命运,你要发文章就得给它版面费,这等于花钱买广告。这样就谈不上学术性了,只变成一种市场交易。但是,学术研究很多是长期的,得搞很多年。而政策制度却非要求三年内必须出成果不可,这样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再比如说现在的大学教师招聘,第一件事先问是不是博士,不是博士不要。按这个标准。以前的很多人都成不了教授,包括沈从文、华罗庚都不是博士。我不是说博士制度不能要,不过不能搞得这么偏激、这么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