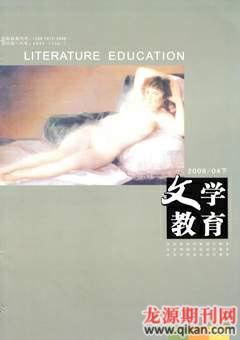符号学背景下的汉语研究
在符号学理论研究中,索绪尔、皮尔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单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概念,即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即符号的能指。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出发点。
皮尔士认为符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媒介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的符号能指),二是对象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的符号所指),三是解释关联物(即意指关系)。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并不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而是有理据、有某种关系存在的,这种关系就是意指关系。我们以汉字为例,来分析一下能指(字形)和所指(字义)的关系。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都可以根据字的形体结构分析出字的意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汉字有六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这里我们采用传统的“四体二用”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是造字法,转注、假借二种是用字法。
一.“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1]象形字摹写事物的形状,或用简单的线条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一看便知其义。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
二.“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2]如:“旦”,“日”表示太阳,指示性符号“—”表示水平线,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象征一天的开始。“本”,是在象形的“木”字之下加一个指示性的小横,表示树根。
三.“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3]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四.“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4]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形旁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如:河,形旁“氵”表示与水有关;声旁“可”表示读音;谋,形旁“讠”表示与语言有关;声旁“某”表示读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汉字具有理据性,它的形体(能指)含有对字义(所指)的解释理据。这是意指方式中的一种:能指对所指的影响。再来看另一种意指方式:所指对能指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人有了想要表达的观念才会选择语言材料进行表达。“语义的形成和表现,从客观事物到心理反映、认识、概括反应,形成大脑内层语义,然后由内层语义转换为内部言语底层,最后由言语底层变为外部的言语形式,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和言语表述的连续过程”。[5]可以推断,先民在造字表意时候的动机就是把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表达出来,这就必然的把他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所指)渗透到字形结构(能指)中。这是一个由所指到能指的过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生活环境、主观认识、民族文化心理等。先民当初的想法如何已不可知,但我们可以从汉字中分析出来。
汉字中与思想、感情有关的字都从“心”或其变体。如:想、意、怵、怕、悟、忍、忆、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而且,人的心理和感情是一致的,因此“心”还蕴含着人的感情成分。心、神、情合一的观念形成了汉民族的共同心态。因此,汉民族里凡是和思维活动有关的字、词,都有“心”。
和钱币有关的汉字,如:财、货、赈、费、赏、赚、贪、贿、赊等,都与“贝”有关。《说文解字》:“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在古代曾经用贝壳作交易的媒介物,到秦朝时才改用钱。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赘述。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字的意指性非常强,同样,汉语的词汇也具有很强的意指性,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加以说明。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言学界对汉语的研究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囿于结构主义的范围,难有突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皮尔士的意指符号理论可以指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汉语进行研究,汉语研究应该综合这两种理论,从多个角度切入,以此揭示汉语的全貌。
参考文献:
[1][2][3][4]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79.
[5]转引自葛本仪.汉语词汇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2002.
潘云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