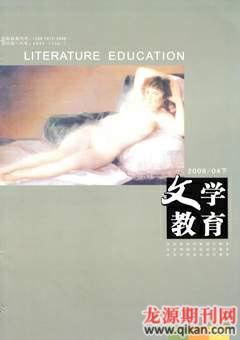夜渔是抒情的歌谣
高维生
沈从文选择丰收后的日子,走进了暮色中,看到茂林一家人围坐桌子前吃晚饭。收成好了,人的情绪不一样。沈从文特意着重写了一大钵鸡肉,辣子拌的牛肉,一碗酸粉辣子和一小碟酱油辣子。这样丰盛的菜,在乡村平常很少见到,年景好了,人的心中有底气了,破费一点,慰劳一下自己,这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沈从文放轻了脚步,没打扰一家人,而是躲在一旁,看着快乐的图景。他耐心地一一介绍了小说里的人物,笔墨不多,却出场了一堆人。沈从文像画家,眯起眼睛,端着速写夹,画出每个人的性格。一张纸上,不一会的工夫,鲜活的人物凸现出来。一根根线条涨满了情感的汁液,漫出一股真实的气息。沈从文很快就注意到了茂儿爹,他是一家之主,这时轻松许多了。茂儿爹放下手中的饭碗,“口里含着那枝‘京八寸,小潮丝烟管,呼得喷了一口烟气,不说什么。”烟气形成了一朵小烟云,缓缓地升起,向夜色中洇化。透过烟气,沈从文看见茂儿爹的眼睛,有一种满意和憧憬,无丝毫杂乱的烦躁。
五叔今天也和往日不同,竟然邀茂儿和他去守碾房。在平时大人不允许,天黑了孩子不能到处乱跑,更不能随便在外过夜。茂儿年纪不大,心计不少,从桌上的饭菜就知道,好收成给一家人带来的快乐,所以他胆子也大起来,没等爹爹同意,他随口答应了。爹爹一坐那儿,就显现出地位和权力,这里是他统治的世界,家长的威严是不能侵犯的。爹爹说的话就是真理,不允许反驳和打断。茂儿的心撒开野,他喜欢夜晚的碾房,充满了迷人的、新奇的事儿。有几次,他想去碾房过夜,在那里没人管,不像在家里,早早地便把他轰上床,在极不情愿中进入睡梦里。他可以趴在窗前望天上的月亮,听虫儿吹快乐的口哨,萤火虫儿,打着小灯笼四处游逛。沈从文小的时候,也和茂儿一样,所以他了解茂儿此时的心情。茂儿很像童年的他,不过沈从文离那个时代已经遥远了。过去的事情,一阵阵地跑过来,沈从文经受一场回忆的追赶。沈从文的一边是童年,另一边是现在的他,他们互相穿插分不清了。沈从文关注事态的变化,他还是有点偏心,对童年的自己偏向。童年消失了,被埋在记忆深处的深处了,但是茂儿和五叔去守碾房,这一简单的细节,却勾起了沈从文的情感。碾房是一条金线,穿起沈从文碎裂的童年的事情。他一步步地接近,伸出一双手,强大的岁月的大门,不会轻易地被推开。沈从文的感情被激活了,由此产生的力量,变作一群勇敢的豹子,比以往的时候更加凶猛无敌。
在茂儿的身上,沈从文看到了自己小时的影子,他动情了。沈从文停住了脚步,朴实的童年吸引着他,那种特殊的感觉,浓度极高的真情涌动,包裹住他不肯散去。沈从文吸了一大口这样的空气,他感受到从心灵往外冒出的情缕。沈从文观察茂儿有些得意了,爹爹烟管里挤出的烟,说明他的心情。沈从文还是喜爱让孩子回到大自然中去,在那里学的东西,不是书本里有的,也不是大人们可以教会的,沈从文看着茂儿的心动,他舒畅地写道:
他知道碾子上的床是在碾房楼上的,在近床边还有一个小小窗口。从窗口边可以见到村子里大院坝中那株夭矫矗立的大松树尖端,又可以见到田家寨那座灰色石碉楼。看牛的小张,原是住在碾房;会做打笼装套捕捉偷鸡的黄鼠狼,又曾用大茶树为他削成过一个两头尖的线子陀螺。他刚才又听到五叔说溪沟里有人放堰,碾坝上夜夜有鱼上了……所以提到碾房时。茂儿便非常高兴。
当五叔同他说到去守碾房时,他身子似乎早已往那飞转的磨石边站着了。
五叔放出了想象,它诱惑茂儿胡思乱想,也不正经地吃饭了。桌边的茂儿,心早跑到碾房去了。筷子在碗中扒饭,却不知怎么进嘴,如果平时早就被爹爹看不顺眼,大骂一顿了。今天日子不一般,一家人说话温柔,老少都没火气,脾气也就没有了。茂儿根本没心思吃饭,不住地问五叔,什么时候走。沈从文把一顿黄昏饭写得有滋有味,这都是丰收带来的喜庆。乡下人脸朝土地,背驮晴天,一年到头在地里淘着生命,如果风不调雨不顺,那么一家人在艰辛的边缘挣扎,哪还有清闲坐这里。在乡村这不过是一顿普通的晚饭,但沈从文一定发现了什么。沈从文择不同的角度,想融进这场景中,他想嗅一嗅,茂儿爹身上被汗水和阳光洗过后,散发的独特的气味。沈从文关心的不是表面的形式,关注的是生存状态和大地的情感。一声叹息,一阵笑声,一句粗野的话,沈从文体验他们的灵魂。萧红的小说和沈从文有些共同的地方,都是触摸生命的本质,原汁原味地将生活摊在阳光下,不是靠堆积词语,去修饰生活。萧红没像沈从文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她是直接地使用我,我在童年的亲身经历: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如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能几天就冒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帽摘下来说: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很多年了,萧红和沈从文漂泊在外,童年的树深扎在心灵上,越长越大。苦了,累了,绝望的时候,他们都躲在树下,在浓阴中寻找呵护。童年离生命最近,那时还没离开家,苦难没锈住稚嫩的枝权。沈从文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流满一股温暖。他不想让过多的苦难,早早地根植茂儿的心中。沈从文和萧红经受过大苦大难,当情感触及到童年,回忆漫长了。他们的思想深刻而又真切,没虚假的成分。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透出作家的思想寒光。通过普通的生活场景,体现了沈从文对人生的感概。沈从文和萧红性别不同,但对人的关爱和深切的感触相同,他们的精神土壤密不可分。在人生的路上漂流,童年和故乡支撑他们走下去。
沈从文控制情感的发展,没让五叔带着心急的茂儿去碾房。这是收后的好日子,一家人难得有闲情逸致,坐在院落中,漫无边际地聊天。沈从文让茂儿搬来板凳,坐在一旁听大人们说笑,欢笑中等待五叔领他去守碾房。茂儿是孩子,听不明白大人说的话,心里装不了太多的东西,他对大人们说的事情不感兴趣,他注视天边的晚霞,变幻出各种色彩和形状。茂儿丰富的想象力,如同绽开的花朵,跑出缤纷的色彩,漫出逼人的香气。茂儿看到那堆红云,薄得像一层“蒙新娘子粉脸的面纱”,黄云铺展天空,像一条金黄的锦锻。迷人的景象,堵住了茂儿的嘴,他在美丽的彩云面前安静了。沈从文给了茂儿太多的笔墨,把自己对童年的怀念,一古脑儿地倾泻到茂儿的身上。沈从文想起小时候,和母亲还有妹妹们围在炉边,喝莲子粥,吃冰糖白煮鸽子蛋的情景。大门外,卖面人一面敲着竹绑绑,诱人的吆喝和绑声像两条蛇,纠缠一块,不分上下,忽左忽右,它们一齐扑来。沈从文花了很多的文字写那些经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打发走的,它长在生命里了。跟沈从文同一个时期的鲁迅,对童年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他的很多小说都与童年有关:
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不久豆熟了,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都回来了!哪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大家都说已经吃了点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第二天,我晌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卖了豆回来,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我点一点头,说道,“好。”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他于是打着楫子过去了。
三位大师都写了童年的事儿,发生地点各不相同,都是那么真性情,去掉雕饰,没一丝造作的表演。他们面对本质的童年,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了,这种关怀,不是教课书上的提示。乡村的虫子是一个不知疲劳的歌手,在它的伴唱下,大人们的谈话内容,融进茂儿的记忆中,今后无论离开故乡多远,当他浮出思乡的念头,一定会想起童年的暮色。这声音和话语声生在心上,不是时间能摧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乡情反而越长越大,那种幸福缠绵一辈子。
夜色击退了白天的暑热,凉爽的风拂在脸上,身上的汗褪了。秋天悄悄地来临,潜伏、等待时机,一夜间横扫大地。沈从文盯注田塍上行走的茂儿和五叔,天空上的月亮,还没完全露出脸。田地上割过的稻地,残留的根茬诉说收成后的喜悦。这样特殊的语言,没在田间播过种子,插过秧,守过夜渠的人理解不了,翻译不出的。沈从文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不但听懂稻子的话语,而且还为它配上一段文字的音乐。“身前后左右一片繁密而细碎的虫声,如一队音乐师奏着庄严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铃子的‘叮……像小铜钲般清悦,尤其使人沉醉。”沈从文把画面和音乐用文字拍摄的清淡而美丽,他把镜头缓慢地推远,叔侄的身影有了传统水墨画的韵味。
水车咿咿呀呀的呼喊,在夜色中清脆地传来。碾房中透出的灯光,引诱茂儿加快脚步。沈从文笑了,因为他看到茂儿脚步的频律,像虫儿的叫声,敲打着通向碾房的田路。拐过一个山口,溪水甩落眼前,数不清的萤火虫在半空中游走,如同一盏盏小灯笼,为他们带路照明。茂儿听到溪边有人说话,他问五叔:
“咦!五叔,这是怎么?”
“嗨!今夜他们又放鱼!我还不知道。若早点,我们可以叫小张把网去整一下,也好去打点鱼做早饭菜。”
茂儿的思绪顺着五叔的话想到逮鱼的情景,他的心动了。
沈从文没了困意,他和茂儿还有五叔走进碾房,守着美妙的夜晚,等待放鱼的人,送来鲜活的鱼儿。在水车旁,熬一锅鲜鱼汤做夜宵,那是无论无何要写在记忆中的。
(选自《青年作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