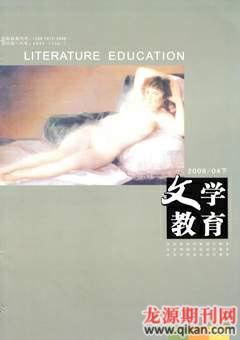莱辛及其《野草在歌唱》
当瑞典学院2007年10月11日宣布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时,创下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得主已经88岁了——而且,据莱辛自己透露:她最少有12次成为候选人又最终失之交臂——这似乎也是“候选”的一个记录。莱辛的终于获奖使她和她遍布世界的欣赏者、读者、译者、论者,当然也包括希望赚钱的出版商,大概都会长长出一口气:一件应该的事终于发生了。
诺贝尔文学奖重终身成就。从这一点说,莱辛名至实归:她从7岁开始习作,14岁拥有一台打字机,其写作历史已近80年;从1950年发表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至今,也已57年;她迄今已有近三十部长篇小说——2007年仍有新作《裂痕》(The Cleft)问世(尽管不无否定甚至嘲弄之声),她不仅“量”大,同时也“质”高: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①(1950)就获得一片赞誉,后来的《暴力的孩子》(五部曲,1952-1969)和《金色笔记》(1962)等也同样是赞誉一片,它们同样地被视为当代小说中的杰作甚至经典。莱辛创作上的又一特色,是她在文体、风格、题材等方面的多变与善变。从前述几部作品说,《野草在歌唱》是现实主义一类的,《金色笔记》是现代主义一类的,而《裂痕》则是科幻一类的,小说风格可谓多样,其手段自然也不断翻新。依莱辛自身经历讲,也可说是色彩丰富或斑斓:她生于伊朗、长于津巴布韦、因病辍学、自学成才;她的身份或被带上的“帽子”包括“共产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种族主义”“神秘主义”等,如果加上她两度婚姻又皆终于劳燕分飞的曲曲折折,她的“戏份”也真是够足了。以作品的量大质高,风格之丰富多变,个人色彩之斑斓异类,加之88岁之高寿记录,莱辛之“获奖”成为热议“话题”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如果读莱辛,读哪部小说好?这当然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要有所建议,依笔者之见,对于文学爱好者或传统文学读者,不妨先读《野草在歌唱》,它或者更容易、更合适,也更可接受些;莱辛的《金色笔记》一类因其实验性阅读起点要求稍高;而《裂痕》之类科幻小说则显“遥远”与“抽象”。何况,成名作多是作家的“高点”之一,更何况已历近60年时光考验之《野草在歌唱》还有其特殊的“中国缘”。
说起《野草在歌唱》的“中国缘”,其一是它1950年问世英国后,“红色中国”在几乎第一时间就译介过来(1999年10月译林出版社所出乃属另一译本),这是很少见的现象,这当然与她的“共产主义者”身份有关,与这部作品写所谓“第三世界”的“非洲”有关;其二,莱辛曾经造访中国:1993年她在中国社科院与外文所专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与英语系师生做过小型座谈、交流,坦率表达了关于“作家”“批评家”“批评”等文体的看法:她的作品的中国翻译者陈才宇(他译了莱辛的《金色笔记》),1998年9月29日在伦敦西汉普斯蒂德的贡达花园路24号——莱辛的寓所——关于她的作品作了面对面的交流;此后不久的1999年6月21日,以译介世界各国文学为宗旨的《世界文学》杂志的编委邹海仑又再次访问莱辛,单独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似乎可以说,莱辛是中国介绍得较早、翻译得较多、也有一定研究成果的西方当代小说家之一。如果再考虑她先信奉“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后因“斯大林主义”而大大失望、重新回归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作家的超越性立场,我们中国读者应是有些亲切而苦涩的共鸣的。
回到《野草在歌唱》这个话题。关于它,最具代表性或主流的解读多在“殖民统治”“种族歧视”“穷白人移民的艰难”“女性的生存境况”等“焦点”上。无疑,这些视角都自有道理、自有其合理性。小说也的确写了殖民主义的罪恶、种族歧视的事实、“穷白人”的生存不易与“女性”生存境况的艰难等等,但我更愿意在超越或脱离“殖民统治(时期)”“种族歧视(的揭示)”“穷白人(的艰难)”“女性(生存境况)”这样(些)的层面去阅读它、解读它。也许这样更近于“文学”自身或者对文学的“欣赏”。作朴素的表述,即:它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关于一对寻常的男女、取用一种平静的叙述、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典范。
先说“一个普通的故事”。虽然小说一开头就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女子突然被她的黑仆摩西杀死这多少显得有点“噱头”的事件,但也仅止于此:从第二章开始,“杀人”的“悬念”故事就被“暂时”(实际上,当谜底揭开也已是故事终了了)扔下了,开始的则是玛丽的幼年时代、少女时代、成婚、失望、迷惘、抑郁、与仆人的暧昧与仍属暖昧的被杀。玛丽虽系白人,却土生土长于南部非洲,家境贫苦,父母感情不睦且每每詈言相向,如是环境自然使幼年的玛丽产生“摆脱”的愿望,心理上也不免留下了关于“家庭”“婚姻(爱情)”甚至“生育”(之痛)及“性爱”(恐惧)的阴影。终于走出了寄宿学校、终于找到一份虽单调刻板但可独立的工作,她也终于体尝到了生活的所谓“幸福”——从16岁到30岁,这是她短暂一生中不算短暂的幸福——上班、聚会、打网球、看电影、郊游、收入可观、友人成群——但世俗社会的力量如无形之网渐渐向她收紧:30岁、老处女、异样的目光、不无恶意的玩笑、难耐的孤寂感等等。她被迫走向婚姻。她与丈夫迪克几乎彼此全然是“偶然”的“礼物”:一个想赶快嫁出去;一个想成个家——一个过得不错的女人与一个过得很差的男人(当然是白人)都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对方。但这却是一场漫长厄运——不是突然的打击,而是日复一日钝性的、有如滴水穿石般的寻常拮据岁月的折磨——的开始:迪克懦弱又偏执,行事总半途而废,不时生出种种新念头而结果总是不变如一的失败;玛丽一次次改变现状的热情与愿望在迪克和他的农场经营中屡屡受挫、失败。贫困窘迫的现实生活沉重地打击着她那优越的心理,她在抑郁中浑浑噩噩地打发时光。她看到了自己正走在母亲曾经走过的生活道路上。她曾经弃家而去,欲进城求生,但路被她的“现实”堵死了。她不得不在绝望中随迪克重回农场那墓穴般的破败小屋。在孤独、痛苦甚至歇斯底里的绝望中,善解人意、举止有度、体格健壮的黑仆摩西悄然进入了她的生活,甚至接触到她的“身体”(要注意到,莱辛对于他们在“性”意义上的接触用笔轻浅、篇幅有限,甚至暖昧不明)——她感到了一缕阳光、一股暖意、一种朦胧的召唤与引诱——然而一个白人女子、白人女主人与她的黑仆的暖昧关系在彼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何等的巨恶而不可赦!玛丽最终屈从于白人社会的压力、驱赶走摩西,而深感羞辱的摩西在电闪雷鸣之夜向玛丽举起了泄恨的钢刀……将这样一个故事放在文学故事的汪洋大海中,的确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没有大起伏、没有大曲折、没有大事件(如果不把“杀人”看得太过特别的话)、没有浓墨重彩或五色斑斓——它不过是一个极其“日常化”的故事而已。
再说“一对普通的男女”。玛丽我们在上文已有较多叙述,迪克也有所介绍。从这两位主人公看,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命运只不过是因“贫困”而成的牺牲品罢了。玛丽的贫困出身与家境影响了她的心理、她的性格、她的命运。而迪克也同样是因“贫困”而狼狈,他懦弱、偏执的性格又强化、推动着他不幸的命运步步前进,愈陷愈深,难以自拔。比起我们曾经谈到的大量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司汤达、巴尔扎克、果戈理(莱辛说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她提及的作家包括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她在与来访者的谈话中两次提到果戈理)、狄更斯们笔下的人物,玛丽与迪克甚至更显得“普通”:没有了不起的经历、没有了不起的作为(甚至无作为)、没有可以说得上的“戏剧化”的冲突,叙述出来关于他们的一切,几乎是琐琐碎碎的“一地鸡毛”。他们为环境、为命运任意驱遣,自身只是在随波逐流,他们没有做出哪怕一件使他们能增色添彩的事。如果一定要对他们做出某种概括的话,只能说他们活得窝囊、活得狼狈、活得庸常。将他们放置在人群中(自然是“穷人”中),他们立刻就会消失而没有了“自己”的模样。
仿佛是与“普通的故事”“普通的男女”相匹配,莱辛的叙述(她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第三人称”叙述:他,她,他们/她们)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平静”:没有对穷苦太多的叹息与同情,没有对不幸太多的悲悯与怜念,没有对出现的丑恶有外泄的愤怒与谴责,只是在叙述没有故事的玛丽的故事、迪克的故事、玛丽与迪克的故事、玛丽与摩西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体验、他们的心理、他们脚下贫瘠的土地与头顶酷烈的日光、他们简陋破败的小屋。然而微妙或有趣的是:当我们打开小说为“杀人”情节刺激吸引之后,渐渐感到的是缓慢行进中的沉闷,我们勉强自己继续,又渐渐,我们为女主人公玛丽的内心变化所吸引:她幼时的阴影与恐惧、她少女与青年时代的明丽与幼年阴影的顽强存在与执著复出、“老处女”生活对她行为举止与心态的纤细影响、对婚姻的迫切与对男性的陌生以及对“性”(亲吻、拥抱及其后的做爱)的莫名惊惧、终于成家后对婚姻与生活的朦胧热望、对迪克的期望与失望以及性格博弈中的彼此角力、对黑仆摩西由恨到暖昧的依恋等等,其细致若丝又拧合为线的娓娓叙述为女主人公之命运提供了极为自然又极是明晰的心理轨迹。我们被莱辛的“平静”叙述控制、支配。我们关心玛丽——我们自然也同样关心迪克,他们作为小说前台区的主人公渐渐从平面成为浮雕、从浮雕成为雕塑、从雕塑成为雅典娜口吐仙气后活生生的“人”。我们由之发现的是莱辛的力量:用平静的叙述、说寻常的故事、讲普通的人——靠生活图景的逼真如日常、靠“普通寻常”的宽广覆盖(我们谁又不是生活中的“普通寻常”?)、靠隐秘心理行进轨迹的探究与渐次明晰的呈现,莱辛让我们认识、感受到了与我们同样普通的人在穷困(或可能的穷困)中的日常煎熬与走向死灭。她唤起了我们的经验、想象、理解与同情。换言之,莱辛以“普通”与“平静”创造了艺术效用上的“不普通”与“不平静”。是为“现实主义”之“大难”。
莱辛在当代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命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要有真切的生活体验(《野草在歌唱》无疑与她在南非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只要有生活图景的逼真描述(在2007年初有了非洲坦桑尼亚之行后,我对莱辛笔下的非洲的“真实”有了经验意义上的判断与尊敬),只要有生活中“人”意识或心理之流的成功展现(如玛丽、迪克和摩西),只要有性格、情节、情感逻辑支配下的冷静叙述,现实主义便具有力量、便具有生命、便有来自现实世界生活中人的阅读与称颂,尽管《野草在歌唱》出生在“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上世纪50年代。
以上的解读自然只是我作为读者而不是批评家想跳开“主义”或“标签”的“一说”。莱辛像世界上的大多数作家一样也讨厌批评家,她把批评家称为“爬在作家身上的跳蚤”。但对于读者她宽厚多了,在获奖之后的第二天——2007年10月12日——接受诺贝尔官方网站主编亚当·斯密斯电话采访时,她说:“读者自己作出阐释,作者只能听之任之。即使他们完全误解了你的意思,你也无可奈何。你不能发表声明说:‘噢,亲爱的,根本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另外的意思。事实是,你写了出来,他们去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做读者确是幸运得多,唯一要小心的是,我们尽可能不要辜负了作家给予我们的理解与宽厚。
还有一个困惑留在这里,即莱辛为什么要以“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n Singing)为题。从小说的“题记”可知:此标题出自象征主义诗歌巨匠、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埃略特(1888-1965)的不朽名著《荒原》的第五章“雷霆所说的”。其上下文为:
在群山中倾颓的洞里
在潺潺的月光下,小草在
倒塌的坟上歌唱,而教堂
则是空无一人的教堂,只是风之家。②
从上下文看,莱辛引“野草在歌唱”的本意是和“倾颓的山洞”、“苍白的月光”、“倒塌的坟墓”、“空寂的教堂”营造的“死亡与绝望”环境或氛围联系的。如是看来,与其说是“歌唱”,其实不如说是痛苦、无助、无望的“呻吟”。如果依中译“野草在歌唱”的明朗字面看,就很难解在“标题”与“内容”间的彼此相悖了。或者这也是我们阅读、欣赏《野草在歌唱》时要留意的。
参考文献:
①【英】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一蕾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②T.s.埃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93页。
仵从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