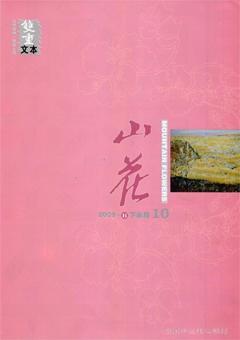试析《儒林外史》中“名士”之心态
余冬林 王雅清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成书于18世纪40年代的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它精心地描绘出一轴色彩斑斓的士人风貌长卷,可以称为宗法专制社会末世士林百态的浮世绘。士林中有儒士和名士两大支。因《儒林外史》以较大的篇幅刻画名士,故清代有学者指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对《儒林外史》中名士心态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把握明清末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名士大多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名望高,不做官,喜欢议论朝政;二是有学问,尤以诗文著称,常常聚会饮酒赋诗。吴敬梓笔下的名士,除杜少卿、庄绍光等少数人名副其实外,其他多是假名士,如湖州莺脰湖名士娄氏兄弟、杨执中、权勿用等;杭州西湖名士赵雪斋、景兰江、浦墨卿、支剑锋等:南京莫愁湖名士杜慎卿、季苇萧等。这些假名士虽然多如过江之鲫且来源复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心态特征,这就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自欺欺人,自私无根。
一、沽名钓誉
假名士沽名钓誉的心态往往在他们举行的“雅集”中暴露无遗。如杭州西湖斗方诗人的一次聚会中,浦墨卿提出一个问题:“比如黄公同赵爷……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儿孙满堂。这两个人,还是哪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哪一个?”景兰江道:“可知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斗方名士们认识到:诗名也是一种功名!更重要的是,这种诗名也会博得官府中人的垂青,由此可提高身价。其艳羡功名富贵之心昭然若揭。正如有人评论日:“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另一派名士相府公子湖州娄氏兄弟。他们偶然听说一名叫杨执中的贤士,大起倾慕之心,为其还债赎罪,出名保释。事后,不见杨执中来谢,他们还不惜降尊纡贵登门拜访。经过三顾茅庐,把这位高贤请回府中尊为“上客”,终于完成了战国时期信陵君“礼贤下士”般的伟业。而张铁臂在娄氏兄弟眼中俨然是“仇必雪,恩必偿,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侠客,慷慨赠其五百两银子,并广招宾客举办“人头会”,结果发现张铁臂所谓“人头”竟然是“六七斤重的猪头!”娄氏兄弟因沽名钓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二,哗众取宠
假名士大多喜欢作惊人之论,以示与众不同。羊枣本是一种小甜枣。《孟子·尽心下》记载,曾子因去世的父亲喜欢吃羊枣,所以自己不忍心吃它。金东崖做《四书讲章》,偏要另立新说:“羊枣,即羊肾。俗语说:‘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吃。”杨执中则批评朝政道:“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另一高士权勿用,前往拜会娄家公子时,模仿古代名士,穿着一身白的孝服,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晃荡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那路上却挤,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掮着一根尖扁担,对面一头撞将去,将他的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乡里人低着头走,也不知道,掮着去了。他吃了一惊,摸摸头上,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是我的帽子!”吴敬梓让权勿用的高孝帽子被人“挑”走,意在嘲讽他徒有其表的“怪模怪样”。
三、自欺欺人
杨执中在科举乡试上失败了十六七次后,他在潜意识里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做高人名士的梦幻,以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和心理期待。高人首先要有学问,于是他“便袖口内藏了一卷(书),随处坐着,拿出来看”;于是到处“说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仿佛自己也“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只可惜他不肯以自己“管、乐的经纶”管理盐店,以致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锒铛入狱。同时,他竭力装出一副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模样。在因科举失意患有同样梦幻病的娄氏兄弟面前,把自己辞掉沐阳县儒学教官的事迹大肆渲染,使得娄氏兄弟肃然起敬。而娄氏兄弟的“求贤若渴”,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政治理想,完成什么事业和抱负,而仅仅是因为这种虚幻的游戏可以满足其对虚荣心的渴望,填补无所事事的空虚,借此进行精神上的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杨执中、娄氏兄弟等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着猥琐的欲望,用无所事事的忙碌点缀着空虚无聊,他们给自己以及同类戴上“贤士”、“高人”的桂冠,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梦幻世界里,并在其中煞有介事自得其乐。
四、自私无根
《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都自认为是名动一方的大名士,没有一个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慷慨互赠大名士的封号。他们往往极端自私,毫无节操可言,道德上呈现一种“无根”状态。季苇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充满“帮衬智慧”的揩油士,他心中没有什么仁义道德,没有什么是非曲直,一切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旨归。譬如,停妻娶妾是宗法专制社会的道德、法律不可宽宥的,他却指着“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的对联,堂而皇之地辩解道:“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他抵达南京,与杜少卿刚见面,便“豪迈”地提出“这买河房的钱,就出在你!”仿佛与杜少卿是一见如故,同气相求的至交。可当高侍读诋毁少卿时,他却缄口不言置身事外。被誉为“为人忠直不过”的杨执中,极力向娄氏兄弟吹嘘权勿用。可突然有衙役来捉拿权勿用时,真相尚不明朗,他就急忙对二娄说:“‘蜂虿入怀,解衣去赶。……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如此急于洗脱干系,如此绝情寡义,只是为了推卸作为推荐人的责任,保住自己在娄府的位置,表现出十足的自私。杭州西湖名士支剑锋、浦墨卿、景兰江、匡超人等“雅集”散后同行,支剑锋喝得大醉,把脚不稳,前跌后撞,结果被盐捕分府下令一条链子锁起来。“景兰江见不是事,悄悄在黑影里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内俩人溜了,转到下处,打开了门,上楼去睡。”对朋友的安危,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由于这类“名士”太多,南京的“妓女们相与的老爷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来嫔楼妓院的聘娘,结识了一个“名士”叫陈木楠的,他向国公府徐九公子借钱,又向药店赊取人参、黄连等贵重药品来送给聘娘,终于欠了一屁股债务,逃之夭夭。还有一个自称“名士”的测字先生,听说聘娘会看诗,居然出演了“呆名士妓馆献诗”的丑剧。
《儒林外史》中假名士的上述心态特征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致。对假名士的心态问题,我们可以从宗法专制时代末期的政治制度、假名士的人生态度和社会氛围等方面探究其原因。
一是政治上徒具形式的荐举制度。隋唐以降,主要实行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但察举、荐举、征辟等办法一直相辅而行。清朝统治者更是兼容并收,如设置孝廉方正科、博学宏词科,推行荐举征辟,网罗和笼络有声誉的名士。在科举制度中,也有贡举、经明行修、优行等含有举荐因素的名目。这种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品行本来就缺乏相
应的评估机制,因此所举荐的人,大都是有名无实虚伪无耻之徒。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就为形形色色的假名士提供了夤缘的阶梯。如匡超人本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农家子弟,进学后,受到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追名逐利,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变成一个忘恩负义毫无廉耻的衣冠禽兽。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被温州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这种制度无疑会刺激和诱发五花八门的假名士的滋生。他们纷纷装腔作势,呼朋引伴,想造成虚假的声望,沿着名士这条“终南捷径”,谋求“异路功名”,高则可以平步青云,为官作宦,低则可以依附权门,充幕客,当帮闲。
二是假名士投机混世的人生态度。这些假名士本来都是热衷于科名的人,只因场屋失利,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但是,他们又不甘寂寞,于是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博得虚名,以此作为附庸风雅、结交官场的“敲门砖”。这些人大都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只能接受社会的随机性的雕塑。季苇萧来到南京,是个“此刻不知下刻命”的漂泊者,但他却靠着社交过着诗酒风流的小日子。季苇萧也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利不求大,只要能有饭吃;名不求高,只要闻名一地即可。谁的饭都可以吃,跟谁在一起吃都可以,没有什么规矩和原则需要遵循。“莫愁湖高会”的导演杜慎卿,出身于名门世家,精神极度空虚无聊,常常顾影自怜。他还想出一个不同于俗套的“希奇”办法,召集了全城一百多个做旦角的戏子来表演,品评他们的“色艺”,“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这次莫愁湖高会,不但满足了他的好色渴求,也为他博得了风流倜傥的美名,使“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
三是社会上追名逐利的风习氛围。明清末世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了普遍性的企慕和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氛围。科举制度以及荐举征辟等辅助性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品行本来就缺乏评估机制,对知识的评估也越来越失去科学性。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再加上追名逐利的社会氛围的推波助澜,形形色色无文无行的假名士产生就在所难免。赵雪斋是一个“学书不成,弃而学剑;学剑又不成,弃而学医”的角色,做不好“八股文”,只好学几句诗,充当名士,结交官场人物。“倒是我这赵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哪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得不怕。”正是凭借这种诗名,才有可能与权力阶层勾结起来,才有可能在其他社会下层面前骄横跋扈。牛浦郎在芜湖甘露寺读书,得知一位会做诗的牛布衣死在甘露寺,而牛布衣颇有声名,临死前把遗稿托给老和尚。牛浦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因此,他偷走牛布衣的诗作,冒充牛布衣四处招摇,居然也能招致董瑛等老爷慕名来访。他听说有位候选知县路过芜湖,曾前来拜访过牛布衣。这位知县后来在安东,他便前往安东投靠,公然在安东打出“牛布衣代做诗文”的广告,以致牛布衣的遗孀千里寻夫,说他害死了牛布衣,闹了一场笑话。由上可见,明清末世追名逐利的社会氛围,正是形形色色多如过江之鲫的“名士”得以产生的温床。
作者简介:
余冬林(1972-),男,汉族,湖北浠水人,硕士,九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史与旅游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