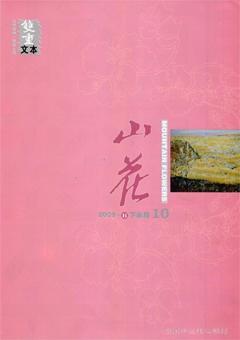纸条
1
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李文一个人在家,洗漱间的电灯没关,他就去了卧室。这样做,可以解释为李文对妻子段瑶的关心和体贴。这一年春天以来,段瑶晚上经常出去,她总是换上过去一点也不喜欢穿的高跟长筒靴,带着一个以前不习惯也几乎用不着的挎包,差不多都是深夜才回来。本来,段瑶一进家门,完全可以方便地摸到门边的开关,打开过道上的灯,顺手挂起挎包,随即换上拖鞋。但李文还是想用与过道连在一起的洗漱间的电灯,向段瑶委婉地强化“家”这个概念,同时,多少有些讨好地传达一个丈夫所能给予的温暖。
午夜时分,李文醒了过来。由于段瑶不在身边,李文的睡眠就不太好。洗漱间的灯光,照射进卧室里。对于这一点,李文之前还没有注意到。床对面是衣柜,衣柜有两组,十四门,其中的一门是打开的,一定是段瑶换完衣服,匆忙之中忘记关上了。这种情况,之前也好像没有出现过。灯光正好照射在门内的穿衣镜上,光线反射,射到了靠近窗子的相框上。相框里镶着李文和段瑶的结婚照。与后来很多夫妇的结婚照不同,他们只照了这一张。照片上,段瑶涂着口红,比平时要妖艳一些。五年前,李文看起来比现在更年轻,完全是一副大男孩的样子。当然,照片的情景,不是他现在看到的,而是想到的。相框再次反射光线,在窗帘上打下了一团比较暗的光斑。
李文看到窗帘上的那团光斑里,有一团暗影。是蝙蝠吗?显然,小区住房里飞进一只蝙蝠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正是这团暗影吸引了李文。这时,李文发现,段瑶将换下的胸罩随手丢在了床上。他把胸罩的两边叠在一起,嗫手蹑脚地走过去,准备罩住那只猜测中的蝙蝠。要罩就要罩个万无一失!罩住了,打开窗,把它放出去。想到这里,李文的心情是轻松的。李文长着一双相当女性化的手,非常之小。夫妻欢愉之时,这双小手掌控不了段瑶饱满的乳房。段瑶却长着一双大男人的手,喜欢把“小李文”握在手心,让他动情。他们的夫妻生活热烈奔放,充满了快乐。
实际上,那团暗影只是窗帘的皱褶。如果李文不拉开窗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李文拉开窗帘的时候。完全适应了卧室里的光线。他看到楼下一辆刚刚停稳的车子,车头对着单元门,车灯照亮了前方。他看不清楚这辆车是什么颜色的,一个人从副驾驶位上下来,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这个人应当可以看到,楼上没有灯光。李文所在的二楼,从洗漱间里几经周折而来的灯光,已经十分微弱,从下面是看不出来有光亮的。这个人从前方绕到车子左侧,弯腰,与开车的人打招呼。这个人的声音比较低,李文听不清内容。开车的显然是一个男人,只说了一句,但是说得高声大气,李文就听得明明白白:“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你要好好留着!”说完大笑几声。由于不清楚两人对话的语境,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这句话的准确意思,但从笑声上判断,一定与性有关。
在两人说话以前,李文就看清了段瑶。他先看清的是那双长筒靴,其次是那个挎包,最后才‘是她这个人。
开车的男人笑声一停,李文打开卧室的电灯,又回到拉开了一条缝的窗帘前。段瑶仓皇地抬起头,李文似乎清晰地看到了她春天以来开始涂的口红。这时,段瑶做出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动作。她的上身想弯下去。再和开车的男人说一两句什么话,下身却想跑向单元门,回到自己的家中。
2
那天深夜,李文在家里的窗前看清了那辆越野车,平县最常见的公务车,那一辆是黑色的。车子掉过头来,他还看清了牌照。开车的男人把一个烟头往单元门的方向使劲一扔,烟头穿过车灯之外的暗区,划出了一条微红的线条。仿佛一根已经点燃的引线,足以引爆一吨炸药。越野车相当暴躁地起步,像一头受到刺激的西班牙斗牛,然后它冲了出去。李文知道,开车的男人不是单位的专职驾驶员,而是陈主任本人。
3
这一年春天,上边一行人来到平县。此前一个月,包括段瑶在内的二十余名县直机关单位的年轻女性干部职工被选拔为接待人员。
这次对接待人员的选拔,是按照相当严格的程序进行的。段瑶在平县第三幼儿园上班,幼儿园根据上级的要求,动员年轻阿姨们报名参加。段瑶一天下午回到家告诉李文,她也想当接待员,已经报了名,听说还要初选,还要培训,还要筛选,不知道最终能不能选上。话虽这么说,但她却忍不住扬了扬脸,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李文参与了由陈主任亲自负责的接待方案的草拟,所有这些,他都知道,只是不曾料到妻子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就说:“没必要去,不能去!”段瑶自己很开心,在李文脸上轻轻地咬了一下,放开他,嘻嘻哈哈地说:“你这种人呀,不是我说你!娶了一个拿得出手的老婆,却不准她抛头露面,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太缺乏自信了?”说着,用一只大手,拉住他的小手,进了卧室,兴奋地捏了他一下,接着说:“赶快给我参考参考,到时候穿什么衣服去,我得抓住机会给你长脸啊!”段瑶丢开李文的手,把衣柜门一一打开,李文似乎这时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虚荣的女人,五六年来买了那么多衣服!他们的收入,一半以上就被她这样花了。想到这里,李文很生气,一甩手去了厨房,开始做晚饭。李文生气的表现,通常就是这样,因而,段瑶也不想理他,扑哧一笑,干脆一个人试起衣服来了。
过了三天,段瑶回家告诉李文,她们幼儿园报名太踊跃了,居然有二十五人之多,而全县的名额,也就是二十个左右。段瑶十分不屑地说,连一位四十多岁,穿短衫时胖肚皮上露出消退不了的孕斑的老阿姨,还有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但是有狐臭的小阿姨,她们都报了名,确实是太自不量力啦。幼儿园初选出两名阿姨,段瑶自然是其中之一。
为期十五天的培训,段瑶懒得给李文细讲。因为李文对这种事情不热心,又一直反对段瑶参加,所以她也很生气。段瑶生起气来,就很少说话,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比如,她平时说:“这菜盐放少了,不咸,再加一点嘛!”一旦生气,就说:“盐少,加。”语气上倒也不算强硬。除了少说话,还谢绝过夫妻生活。李文很容易生气,好处在于生起气来几乎没有危害性,像他那种气,就是天天生一生也关系不大。段瑶一般不生气,一生气就麻烦。李文采取的办法是,让麻烦自己过去,他从不央求她。所以,所谓“谢绝过夫妻生活”,其实只是段瑶单方面的姿态,在她生气的时候,李文是不会碰她的。段瑶却做得煞有介事,在床上,不是与丈夫背靠背,而是匍匐着睡觉,生怕身边这个男人乘虚而入,以高度的警惕,坚决不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培训的内容,段瑶即使一个字也不透露,李文照样是清楚的:主要是让接待人员掌握一些礼仪常识,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习俗。其次,为了让小地方的这些女人更有气质和魅力,对她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也得进行一番必要的训练。这些训练都相对轻松,比较艰苦的是对形体本身的训练,包括站立、扩胸、迈步,等等。穿着八厘米高跟长筒靴,两条腿尽量并拢,保证膝关节那儿夹着的几页纸不滑落,哪怕一次只站立三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也是够受的。通过扩胸、迈步,
迈步、扩胸,让乳房在不戴胸罩的情况下挺拔起来,难度比想象的大得多。这些训练,指向的目标,是希望在平县为上边安排的那个联欢晚会上,所有接待人员都能有出色的表现。对于整个接待工作的重头戏:联欢晚会,平县期待的效果是:不仅要营造出上边与民同乐,与基层打成一片的良好氛围,而且还要用基层的一片真情,给上边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任务,而是一种使命。某项工作一旦上升为使命,就不是谁都能胜任的了。因此,接受培训的年轻女性干部职工,又被淘汰了十多名。段瑶她们幼儿园的那位阿姨,小段瑶好几岁,肌体上还能散发出少女的芬芳,按说,她比段瑶更让人感到愉快,但还是不幸被淘汰了。
也许,段瑶并不想将这次生气的时间拉得那么长。她之所以在培训结束之后,上边来人之前,那四五天的休整期里,与丈夫依然话少,依然匍匐在床将他拒斥在一边,完全可能是一门心思放在了联欢晚会上,把为什么生气,是否还要继续生气的事情彻底忘了。
4
联欢晚会到午夜零点前后告终,也只开了四个钟头左右。
对于平县来说,接待人员个个年轻,人人漂亮,平常就能歌善舞,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专门培训,她们都是不甘于寂寞,更不甘于平凡的知识女性,如今有了一个平台,有了一次机会,大家都像开屏的孔雀,在联欢晚会上大胆地展现。
她们当中,最为出色的也许是段瑶。从投入上讲,段瑶也比别的接待人员多一些。陈主任很可能是一个想当然的人,他开口要十万块钱,但只要到七万块,这笔钱是这样花的:用两万多块钱买化妆品,剩余的钱,买高跟长筒靴来穿,只买这一样,越高档越好。陈主任的想当然还在于:买化妆品要买就买特别好的,但只买两种——香水和口红。联欢晚会上的化妆,不准再使用别的化妆品了。平时没有修过眉毛的,千万不要再修。修过的就修过了,联欢晚会总不能等你的眉毛长好了再开。要的效果不是俗艳,而是素雅。吃惯大鱼大肉的人,喜欢的其实是山茅野菜。但山茅野菜也不能清汤寡水地端上来,该加葱的加葱,该放糊辣子的放糊辣子,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才用香水和口红。而长筒靴,颜色要米黄,材质要全皮,款式要有带子的那一种。本来,陈主任准备一人配一条裙子,一件风衣,大红的,就像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穿的那样,但钱不够,也没有办法。而段瑶就以一己之力,部分地实现了陈主任的构想,自己掏钱买了红裙子和红风衣,那是她买得最贵的衣服,花了三千多,为此还背着丈夫欠了外债。
在联欢晚会上,每个接待人员都穿上了统一的长筒靴,穿上了各自最漂亮的衣服,在颜色上,没有谁和段瑶雷同,单就这一点,她也显得更出众了。李文并不知道段瑶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买的红裙子和红风衣,平县是买不到的,市里也未必有卖,她不可能去省城,那就一定是从网上购买了。段瑶当初在家里的衣柜前让李文参考,她穿哪一件衣服参加联欢晚会最合适,同时也最漂亮,他生气了,她打算买红裙子、红风衣就不耐烦跟他商量了,买来了也藏起来。段瑶这样做,也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要给李文一个惊喜,让他在特定的场合,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妻子原来如此漂亮!段瑶在家里换上红裙子、红风衣的时候,李文还在单位。作为联欢晚会的工作人员,李文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还是第一次看到段瑶身穿红裙子、红风衣。段瑶想,联欢晚会结束之后,她要偎依在李文的身旁,一起回家,让看到他们的平县人民知道,她是他的妻子,他有这样一个妻子!那些被淘汰的女性干部职工,如果知道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会不会嘴角一翘,相当不服气,议论纷纷:“有什么了不起的,朝中有人好做官!”“不说不知道,怎么会无缘无故选上她呢!”这种假设的情景让段瑶很不快,她遗憾的是,那些嚼舌根的落选女干部,不能到联欢晚会上亲眼看一看,她是多么出类拔萃!段瑶打算在回家的路上,以及回到家,让李文讲一讲,看到她穿着长筒靴、红裙子、红风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路上,李文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可以不限制他。回到家门口,就要给他提要求,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在家里,要求更苛刻,用两个字。当她的大手握住小李文,李文开始动情的时候,就只给他一个字的空间了。段瑶猜不出来,李文写材料字斟句酌,让他说奉承话,他会怎么说呢?在不加限制的阶段,无论李文怎么说,段瑶都将随便听一听,根本不去在意。到了一句话,两个字,一个字,不管李文说得多么好,段瑶都不可能心花怒放。因为,那一个字,段瑶已经给自己预备好了,这无疑是李文想不出来的。段瑶计划,骑在李文身上的时候,她才把这个字说出来。
可以想象,身为丈夫,在联欢晚会上一个小小的角落,见证履行接待员职责的妻子如何鹤立鸡群,李文的心里应当是十分复杂的。
上边来的一行人,谁是谁,李文在作会议记录的时候就基本上记住了。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三四个人轮流与段瑶跳舞。当第四个人发现,有一双眼睛始终停留在穿长筒靴、红裙子、红风衣的段瑶身上时,就把她带到了那个人的身边。李文知道那个人是谁,自从平县的主要领导称他为“老首长”之后,虽然每个人都清楚他不是真正的首长,但谁都跟着称首长了。李文想,也许是段瑶的红裙子、红风衣过于扎眼,才引起了首长的注意吧。段瑶向首长点头,颔首,弯腰,伸手,一切都训练有素,落落大方,彬彬有礼。首长没有立即接受段瑶的邀请起身跳舞,摆了一下手,摆手的意思不是谢绝,而是让她在旁边坐一会儿。这对任何一个接待人员来说,都是一种荣耀。由于距离的关系,李文看不清首长的表情,但从接下来的事情上判断,首长与在会议上架子大、火气重的形象已经完全不一样,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了:他用牙签戳了一点什么水果,递给段瑶。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平常的礼节,但在首长那里,却是对段瑶的恩赐。幸好段瑶接受过良好的培训,要不然,受宠若惊的她,就会手忙脚乱。段瑶那只大手,并没有引起首长的关注。李文想,也许,他是因为自己的手特别小,才会觉得段瑶的手格外大吧。那么,这就是说,首长有一双大手。差不多所有男人都有一双大手啊。李文有些自卑。
平县的陪同者,主要领导和陈主任离开了,他们叮嘱段瑶与首长跳个舞,但不能让首长太累。
在剩下来的三个多小时里,段瑶都没有离开过首长。说明首长确实喜欢这个幼儿园的阿姨。跳舞的时候,首长的一只手放在段瑶的腰上,李文看到,那只手比他的大多了。他们一边跳舞,一边说话,但李文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
李文心烦意乱地假设他们之间的对话。
首长:“你这裙子和风衣很漂亮嘛。”
段瑶:“谢谢。挑来挑去,还算穿得出来。”
首长:“你这长筒靴——”
段瑶:“县上发的。”
首长:“裙子风衣也是?”
段瑶:“我自己买的。”
首长:“一双长筒靴值多少钱?”
段瑶:“说是一千多——”她立即后悔了,改口说:“不值钱。”
首长:“裙子风衣呢?”
段瑶:“更不值钱啦!”
苦地发现,以前,他们是情不自禁,现在,他们是坚持不懈。李文的小手,也还喜欢摸奶,但以段瑶的敏感,完全能够察觉他是在努力抓住她。
李文永远不会相信,直到这个初夏的夜晚,陈主任至少把段瑶从家里喊出去十次了,才知道他是她丈夫。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李文相信这一点,也仍然不能减轻他对陈主任的仇恨。原因很简单,你以一个主任的权势,以一辆越野车的行头,以接待工作为名,三天两头喊一个外单位的女性干部职工出去,根本不去管她丈夫是哪个,这简直欺人太甚!
这个初夏的夜晚,陈主任和段瑶单独待在一个包厢里喝一种叫“云南柔红”的葡萄酒。陈主任喝得多,段瑶喝得少。在陈主任送她回家的途中,段瑶已经意识到,这是改变她人生的第二个夜晚。第一个夜晚,联欢晚会将段瑶从李文身边拉开,走到今天,已经走得太远了。但也不是就远得回不去了,这个夜晚,与陈主任的单独相处,将她朝一个相反的方向推,她完全还有可能回到李文的身边。
陈主任酒至微醺,就跟段瑶谈起了那张纸条。应当说明的是,谈那张纸条,是陈主任把段瑶喊来的初衷和目的,而纸条的事情,毕竟不太好谈,所以需要借助一些酒。这一点,段瑶已经明白了。
而陈主任之所以要谈纸条,是因为段瑶在一个月以前,接到陈主任喊她出来的电话,她告诉他,自己在省城,已经到了三天了,还要待七八天。这是真的。而省城,正是“首长”在的地方。据陈主任调查,幼儿园组织阿姨们去成都考察,段瑶也跟着离开了平县,既然独自滞留省城,她一定是使用了那张纸条,成为首长身边的人了。陈主任是在黄昏打过去的电话,从声音上判断,应当是段瑶一个人吧。陈主任为此而庆幸,要是他的电话不小心让“首长”尴尬,而涉世未深的段瑶又说出了打电话的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实际上,段瑶在省城十来天,一直是她一个人。她滞留此地的原因并不复杂,仅仅是,她发现,联欢晚会不仅改变了她自己,而且还改变了几乎所有同事对她的态度,由于各种嫉妒,也由于多种谣言,她们对她怀着的敌意和不屑,在松散的旅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让她非常难受。于是,她以接到老家电话,家里有急事为由,不得不放弃这次旅行,谎称要返回平县。她把这些都告诉了李文,还在电话里对李文痛哭了一场。李文建议她不要急着回去,最好在省城散散心,一个人安静安静。李文的用意,段瑶是明白的。他们曾经就读的那两所大学,都在省城,两人毕业前谈过一年恋爱。李文认为,七年之后,哪怕是再坐一回当时坐了无数次的那一路公交车,也能唤起久违了的甜蜜记忆。这样,他们生活中或者说婚姻中已经出现的小裂痕,就能很好地得到修复。现在,从谈话中,段瑶已经猜到了陈主任对她的猜想。
陈主任对纸条不厌其烦地提示,漫无边际地延伸。那意思,第一层是说,段瑶遇到了贵人,而贵人不是谁都能遇到的:至于第二层嘛,要攀上贵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段瑶的幸运并不是说她可以例外,而是她毕竟获得了这种机会和可能。
陈主任谈纸条还有一个原因,那倒是段瑶不知道的。最近,平县要调整驻省城的办事处主任,主要领导已经发过话,这次要向女干部倾斜,只要是优秀人才,即使不属于公务员,没有干过副科级,也可以破格起用。陈主任费尽口舌。终于表达了一个请求,尽管这个请求是相当模糊的,但段瑶通过反复琢磨,总算基本明白了:陈主任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起色,希望段瑶帮助他在首长那里建立印象,首长高兴了,说一句“小陈这个人不错”,他的命运就会得到改变。
在联欢晚会上把她从李文身边拉开的那段日子,段瑶曾认为李文是世上最没有起色的男人。只会在单位写材料,六七年不见长进,一直没有钱,她买件衣服也捉襟见肘。频频外出的段瑶,穿着八厘米高跟长筒靴和红裙子、红风衣,带着陈主任用公款买给她的那个真皮挎包,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的漂亮,她的优雅,都是可以通吃的l当她的自我意识膨胀到了顶点的时候,段瑶进一步认为,直到今天,如果说李文也有出色之处,那就是他娶到了她这样的妻子!
现在,听到陈主任的倾诉,段瑶忽然不用那样的眼光看待李文了。前不久,段瑶还在省城的那路公交车上,成功地重温了她和李文读大学时谈恋爱的幸福时光。当年,在一个个慵懒的午后,在乘客稀少的车厢里,段瑶常常靠着李文安详地睡去。七年后,在同一路车上,只要闭上眼睛,就能闻到李文更年轻时的气息。作为丈夫,李文让她对未来感到放心,她无数次地骑着他奔向快乐,他的生气,多么宽厚,而他的小手,也是一种温暖啊。她每夜必回家,以及回家后的具体表现,为的是向李文反复传达一个信号:她只是不甘于寂寞、不甘于平凡,爱慕时尚、爱慕虚荣,至今没有背叛过他,也绝不会出轨。这么多年了,她清楚李文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并不笨,绝不傻,他的种种反应表明,他接受了她传达的信号。
最后,坐上越野车,陈主任的话相当直白:“说不爱慕你的美貌,那是骗鬼!你手头有首长的纸条,我也不敢动你!也有人对你蠢蠢欲动,我就拿纸条警告他们,拿你在省城待了十天忠告他们,一个两个才乖碌碌的。哦,你还以为,都是一帮正人君子!怎么可能?简直太天真啦!”段瑶忽然对春天以来的生活感到了深深的厌恶,她很吃惊,自己居然在这个泥淖中待了那么久。她已经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好好待在家里,待在李文身边,再也不出来。陈主任借着酒性,在为她系安全带时,握住了她的一边乳房。那是一只大手,段瑶十分反感地把它推开了。
陈主任这是头一次亲自送她,而且直接送到了楼底下。如果在前些日子,段瑶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现在,她发现这种越野车毫无尊贵可言,坐在里边确实憋闷,李文说它是一口移动的棺材,它就是一口移动的棺材!从越野车上下来,段瑶为自己终于清醒过来,这种已经使她深感厌恶的生活将马上结束,而庆幸不已。
段瑶为了结束得干净利落而非拖泥带水,所以就绕到越野车的那一边,告诉陈主任:“那张纸条和你想的不同,我放着还是扔掉都一样!”
7
当首长对已经度过的这段快乐时光感到十分满意,表示已有些许倦意的时候,联欢晚会立马戛然而止。段瑶与平县的领导一道,将首长送回下榻处休息,趁众人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她把一直藏在手心的条子塞进长筒靴,然后偷偷溜走了。她想马上回家,回到李文的身边,一刻也不想再逗留。这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在陈主任安排的夜宵上,段瑶不在,别的接待人员反而很快活。女人都有天生的嫉妒心,段瑶在联欢晚会上出尽了风头,本来就不该再来夜宵上显摆了!段瑶自己先走,可见她的聪明之处。陈主任只是随便问了一下,并不坚持一定要把段瑶喊回来。
而段瑶先走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些。在联欢晚会上,她并不是没看到李文,恰好相反,李文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眼睛的余光里闪现。这样一来,就等于给了首长一种她左顾右盼、心不在焉的印象。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一个女人能保持这样的姿态,反而使她平添了几分魅力,
也许会让首长产生一丝不快,但更有可能让他心猿意马啊。事实正是那样,否则,首长就不会给她写条子了。李文在联欢晚会上的心思和感受,段瑶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她在丈夫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魅力。而一个男人,会对与他的妻子在公开场合礼节性相处的另一个男人生发嫉妒,甚至仇恨,说明他有多么爱自己的老婆。所以,段瑶既感到骄傲,又感到幸福。但不管怎样,这对李文来说,也会造成伤害。作为工作人员,不到联欢晚会结束就走了,已经充分说明,李文的嫉妒心和仇恨心有多深了。段瑶想马上赶回去,好好安慰李文一番。再说,她这次“生气”未免太久,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也许连段瑶自己也认识得不够清晰,那就是:她穿着八厘米高跟长筒靴,穿着红裙子红风衣,在联欢晚会上压倒群芳的惊艳之美,现在,她要回去,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好好欣赏欣赏!叫他仔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比婚礼上更漂亮动人?接下来,他们将热烈而奔放地度过又一个“新婚之夜”!
段瑶回到家里的时候,李文刚刚挂断同事喊他去吃夜宵的电话。段瑶不去吃夜宵,也回来了,李文的嫉妒和仇恨之心就消了许多。
段瑶在一进家门的过道里就抱住了李文,一阵狂吻之后,她对着他的一只耳朵,轻声说:“就这样做爱吧。”
不知为什么,李文的反应很强烈,他推开段瑶,粗暴地说:“我不和红裙子红风衣做爱!”
遭到丈夫的拒绝,这对段瑶这种骄傲的女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耻辱。她一脸通红,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段瑶脱下了红风衣红裙子,但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
李文又说:“我还是不和长筒靴做爱!”
在李文的注视下,段瑶再也不能脱掉长筒靴了,因为,里边藏着一张纸条。段瑶很清楚,李文正是看到了首长失态的那一幕才愤然离开的,因而,纸条的事情,现在也不好说。
本来,段瑶准备和丈夫放开了调情,让他用一个字来描述她穿上长筒靴红裙子红风衣的感觉。她清楚,那个字,只有在夫妻生活过得火热的时刻,说出来才恰当。现在,段瑶再也不能说出那个“骚”字了(尽管他们过夫妻生活时一向喜欢说些粗话),那不成了自我作贱吗?
但在此后的一两个月,气候转暖,已经不太适合穿长筒靴了,段瑶却几乎天天穿,以至于两只脚掌被沤白,只要一脱下来,就发出令人厌恶的酸臭。好在段瑶找到了一个办法,她按一张报纸中缝上介绍的生活小常识去做,要求丈夫每次做饭都留着淘米水,用来泡脚,酸臭有所减轻。因红裙子红风衣需要换洗,段瑶就在丈夫的协助下,用一把剪刀,以及一个在某地住旅馆带回来的针线包,改短了两条长裤,把膝盖和胭窝露出来,以搭配那双长筒靴。而要去买一条新短裤,他们手头又不方便。买红裙子红风衣欠下的债务,一直还没有还上。
8
到了这个初夏的夜晚,李文也还不知道那张纸条。
所以,陈主任在楼下吩咐段瑶“你要好好留着”的纸条,就被李文理解成,要自己的妻子留着身体,拿去献给首长,这给一个丈夫带来了莫大的屈辱。
卧室里忽然打开的电灯告诉楼底下的段瑶,丈夫已经看到了陈主任深夜里送她回来的一幕,这是一件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她一定心乱如麻,在自己的家门口迟疑了很久,想理出一个头绪来,把事情给丈夫说明白。
段瑶听到他们家的门锁响了一下,她的心就更加慌乱了。如果李文要去追陈主任,手里还提上一把菜刀之类,那她该怎么办呢?而李文并没有出门,段瑶又有些许的失望。她用钥匙开门,发现已经被李文从里面反锁上了。这时,李文发过一条信息来,内容如下:“委屈你离开一晚。我俩的事,明天再说。”段瑶打李文的手机,已经关了。她一边拼命拍门,一边哭喊,但李文始终不为所动。段瑶的拍门和哭喊声惊动了对门的邻居,毕竟是午夜,邻居十分光火,将门打开一条缝,瞄一眼,又狠狠地撞上。
李文听到段瑶下楼的声音,因为她穿着八厘米高跟长筒靴。他担心她还会在楼下哭喊,那将让多少被吵醒的人心烦啊。然而,段瑶并没有那样做,她在高跟长筒靴声音的陪伴下,走出了这个夜深人静的小区。段瑶的脚步声已经远得听不见了,李文的心里才掠过一丝怜悯,但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就变成了怨恨。
对于一个不敢找陈主任泄愤,不敢找首长算账的男人,李文洗刷耻辱的方式,就是与段瑶离婚。
李文在屈辱之中,回想了联欢晚会上的那一幕。他忽然意识到,原来驻省城办事处主任的人选,不是别人,竟是自己的妻子。既然段瑶要去省城了,那么,让她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李文人穷志不短,他已经想到,要给这套房子折个价,折价就高不就低,马上向所有的朋友借钱,迅速把段瑶那一半如数交给她!想到这里,李文的屈辱就减轻了很多。
接下来,李文甚至已经心平气和了,他开始收拾段瑶的东西,明天,让她把自己的东西带走,彻底将这个女人与他生活过的痕迹清理干净,而且越快越好!段瑶最多的东西,其实就是衣服,干脆让她连衣柜都搬走。
天亮的时候,李文刚刚躺在床上,就看到了他和段瑶挂在对面墙上的结婚照。在他的记忆里,那个相框自从挂上去就没有动过,上边一定落满了灰尘。这个相框取下来,是要砸碎、扔掉的,但在取的时候,李文仍然很小心。李文把相框拿在手里,看到它确实落满了灰尘,但他也发现,上边有一些指痕,也就是说,段瑶最近动过它。仔细一辨认,段瑶在相框上留下了一只手掌几乎完整的痕迹,李文一边想她到底是怎么留上去的,一边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手掌去合,因为他的手掌要小得多,盖不住。把相框翻转过来,李文就见到了那张折叠起来夹上去的纸条,取出,打开,有这么两行字:
“朱小翠。
姓易。”
最后一行,是首长的名字、办公室电话号码和单位地址。
作者简介:
徐兴正,男,1976年3月出生于云南省鲁甸县乐红乡徐家寨子。1999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从事过乡村教师、机关勤杂及文秘、报刊记者及编辑等工作,现供职于鲁甸县文联。写作小说、散文随笔等。2007年与文友在昭通创办同人文学杂志《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