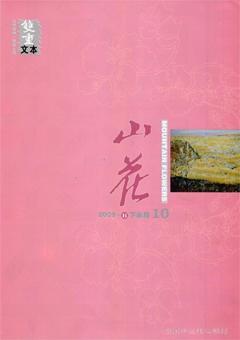呼吸沉重
爹说:“你千万要吃饱啊,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吃三个馒头觉着饱了,还要再吃一个,粮食吃在肚子里瞎不了。”歪头说:“我知道啊爹,现在我一顿饭能吃五个馒头,还能喝一碗菜汤去。菜汤里都有肥肉。”父亲咂一下嘴:“你这孩子,小日子比我过得滋润。昨晚上,我就着两根萝卜条咸菜喝了二两酒,喝完后下了一把子清水面。”歪头说:“你也别过得那么紧巴巴的,给你的钱呢?去老刘那里割块肥肉来吃。”爹说:“钱我是有,我得给你攒着,都快四十的人了,连个媳妇都没有,我不放心。”爹说着说着声音就细了,扭回身沿着屋后那一道山梁,一晃一晃,往树林子里走。歪头就问:“爹你去树林子里做啥?”爹嘟嘟囔囔说了句什么歪头没听清,再眨一下眼,爹就从山梁上消失了。那道山梁看着离树林很近,可是此起彼伏的。歪头觉得爹是隐到凹面去了,似乎还听到爹混浊的咳嗽声。
歪头就在那一刻醒过来。
同屋的二柱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摁着歪头旁边的褥角站起来,一抬脚跨过歪头的脑袋,说:“好人哪能叫尿憋死啊。”就站在靠门后的位置,哗啦哗啦撒尿。歪头说:“你去外头尿去,外头又不冷。”二柱说:“你起来试试冷不冷。”“昨天在工地上还穿背心呢,你就一个懒,看尿得屋里一股子臊臭味儿。”二柱嘟囔:“娘的个天没点儿准数了。我不骗你歪头,现在外面少说也得零度以下。”二柱把眼睛往堵着门框的破塑料布凑了凑,还伸出个小手指头挑一挑:“我说你还是不信,你起来看看可不是下雪了。”歪头忽地一下子坐起来:“你满嘴里跑火车,什么季节了还下雪?”二柱只顾在那里瞧:“下雪好啊。下雪就不用上工了。”歪头说:“不上工,没钱可赚有什么好?”说着也起来了,刚从被窝里出来就有一股凉风袭来,冻得他吸溜一下嘴巴。二柱转回身来笑:“我说过冷,你还不信哩。”歪头在穿裤子的时候突然止住:“刚才,我梦到我爹了。”二柱说:“有什么稀罕的,我还梦到媳妇了呢。”歪头说:“拉倒吧你,你哪儿来的媳妇?”歪头在穿鞋,突然又说:“我还是觉得不对,我爹跟我说的那些话,蹬不着天,踩不着地的。”二柱说:“你那是做梦啊。梦里头的事儿靠啥谱?”歪头说:“不行,我得回去一趟。”二柱说:“你回哪里一趟?”歪头说:“回老家啊,我去看看我爹去。”二柱说:“犯不上,你一去一回得花多少钱?这个月再耽误几天就白干了。”
果然天上飘起了雪花,起初是雨夹雪,雨的比例稍大一些,到午前一段时间雨基本消失了,漫天的雪花,地上是湿冷的。二柱的期望落空了,按戴墨镜的砖窑老板的话说,“只要天上不下刀子,咱们就得开工。”砖坯得倒到暖和的地方去,要不一上冻一化冻就全废了。歪头背了一阵子砖坯,身上冒出汗来,他觉得干点活儿还是好的,至少防冷。歪头干了半天活,脑子里一直是他爹。歪头说:“不行!我真得回去一趟看看。”
爹只露着个脑袋,身子躲进被子里,那脑袋像是叶柄,被子及被子下面的内容就像叶片,薄薄的,轻飘飘的。
歪头说:“爹,我是歪头啊!”爹说:“哦,你说歪头啊?他到砖窑上干活去了。”歪头说:“我就是歪头,我回来啦!”爹说:“歪头这孩子孝顺。五个儿子里头,数他心眼儿少,可就数他孝顺。每回来家都给我买肉,还打上桶散酒。”
歪头看一眼冰冷的屋子,看一眼一丝温乎气儿也没有的炉子,说:“你等着我去烧火啊,我给你打碗鸡蛋汤,喝上你就暖和了。”又说:“我一会儿就去给你找大夫,你这是让病给烧迷糊了。”
那一片山的每道沟里都隐现着三五户人家。方圆一片,只有一个大夫,外号叫做“一斤半”。歪头翻山越岭蹿了好半天才找着他。已经在一户人家里喝了一斤左右了。炕上的老太太挂着吊瓶,“一斤半”就坐在吊瓶底下喝酒。桌子上,摆一碟葱炒鸡蛋。老太太干瘪着嘴,说:“要变了。”“一斤半”的秃顶,一喝酒就是红润润的,好像那酒不是喝进肚子里,而是拿来擦了脑袋一样。他说:“婶子,什么要变啊?”老太太说:“寒食都过了还下雪,要出事儿啦。”
“一斤半”一扭头:“咦,歪头,你咋能找着我的?”歪头说:“你活蹦乱跳的,我哪里找不着你。”“一斤半”说:“我叔的病又犯了是吧?他那个病很黏糊,找我也是白找。上年我就对你家老大说得赶紧送大医院,你们没一个听我的。”歪头说:“我听啊可我没钱。”“一斤半”点着头:“你听不顶个屁用,你一根光棍儿,自家能管住自家吃就不错了。”
老太太转过脑袋来:“歪头你爹又咋了?”歪头说:“我爹和你一样,躺下啦。”
“一斤半”抓着歪头爹的胳膊,眯缝着眼看了好半天,说:“血管倒是好找,你看,到处都是,槐树根一样。”歪头说:“你行不行啊?要是酒管事了,就让我来。”“一斤半”虚张声势:“我是大夫你是大夫?你要是能行,你开药铺啊,干吗出去背砖头?”歪头说:“你忘了那回,你喝多了就是我扎的。还有那一回,你给我扎针,打完了我自己拔下针来的。”
爹突然说:“咦,听动静像是歪头回来了。”歪头说:“是啊,歪头早就回来了。”“一斤半”说:“他这头歪得这么厉害,都快掉地下了,叔你还认不出来啊?”说着捏起针头来,眼睛凑到胳膊上开始找血管儿,却又说:“刚才明明看着很多的,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爹说:“歪头不可能回来,你哄我。歪头在外头下苦力挣钱呢。”歪头说:“你还是把针给我,我来扎。”
歪头捏着那根针,像是举着根棍子。说:“你看看这一根血管行不行。”一扭头,却见“一斤半”半靠在炕边,脑袋垂着,嘴角流出涎水来,居然睡着了。歪头嘟囔:“这么粗的一根血管儿,我就不信我扎不进。”
爹问:“歪头你啥时候回来的?”歪头答:“头午就回来了。”爹说:“歪头你别给我扎针了,扎了也是白扎,拿着钱打水漂,不如去割块肉来给我吃。”
歪头不管爹,开始往那根血管里推针头,终于推进去了,却有一股子血顺着针管返回来,吓得歪头一下子抽出针管,捏住爹胳膊上的针眼儿。歪头说:“还真是不行!”爹嘿地一声笑:“我说你缺个心眼儿你还真缺心眼。你没打开水龙头水能自家淌出来?”歪头歪着头看看针管,也笑了:“光顾着你这头,忘了另一头了。”又扎了一次,成功了。
爹的呼吸沉重。爹说:“日头出来了吧?”歪头看看外面:“出来是出来了,可外头冷哪!”爹说:“我想晒太阳。”歪头说:“晒什么太阳啊?你还打着吊瓶怎么出去?”爹说:“打几天了这是?”歪头说:“第三天,一斤半说要打一星期的。”爹说:“你这孩子纯粹烧包啊,钱多了咬你手了?”歪头说:“钱咱有,没了再去挣,爹要是没了我可就真没爹了。”爹说:“爹也想多活两天,可病在我身上我心里有数。”歪头嘁了一声:“你有个什么数啊。”爹又说:“你背我出去我晒晒太阳。”歪头说:“等打完这瓶。”
歪头把爹扶起来的时候,觉得手底下像是推着一团棉花。他用被子把爹包起来,伸手抱起那团棉花往院子里走。爹的脑袋靠在他肩膀上,嗓子眼儿里像堵了什么东西,每呼吸一下都吹一声哨子。
爹说:“把我放在墙根那块磨盘上。”又说:“你今
天拾鸡蛋了没有?”歪头说:“总共就两只鸡,一只还是公鸡,你寻思能下多少鸡蛋啊?都催我两遍了。”爹说:“鸡蛋是好东西,用香椿芽一煎,就着喝点小酒,给个皇帝咱也不当。”歪头说:“你不当啊?我当。”爹说:“就你长得那个熊样,连个老婆找不上还想当皇帝。”歪头说:“你这话不对啊,当皇帝不一定非得长得有样子,你不是说过朱元璋长得也歪瓜裂枣,人家咋就当上了?”爹说:“当皇帝的都是真龙现世,咱爷儿们怎么端详也不像。”爷俩对着头笑。爹的脸上所有皱纹都凑到一起,浑身一抖一抖的。爹又说:“后脊梁上痒痒,歪头你给我抓一抓。”歪头说:“哪里啊?”把手伸进被子,“你后脊梁在哪里啊?”爹说:“后脊梁那么大块儿地方你找不着啊?”歪头说:“我说咋找不着手还在棉袄外头呢。”爹说:“右边,再右边,往下一点儿,跑远啦又,再往上挪挪,嗯,就那地方,使点劲儿抓。”爹眯起眼睛,舒坦地呻吟一声。歪头说:“你这身衣裳穿了多少日子了?都臭了。”
爹拄着一根槐树棍儿在前头走,歪头跟在后头,沿着山梁断断续续地走。爹说:“歪头,你看看咱家那片地,都荒了,草都长到齐腰深了。等我好一点,咱爷俩来把它整出来,栽上点儿地瓜,到冬里,不想做饭了,就煮地瓜吃。”歪头说:“行啊,栽上点儿红瓤儿的,我烤给你吃,你不知道啊爹,现在城里头卖烤地瓜的都挣大钱了。”爹说:“算了吧,城里城里的,说破了天,咱也变不成城里人。”歪头说:“我要是有了钱,就去城里给你买套房子让你住,你就不这么说了。”爹说:“你大哥二哥都在城里卖水果,好几年了我也没看着挣多少钱。”歪头说:“人家挣了钱拿来给你显摆啊?你一提他们我就生气,就我是你儿子,他们四个就不是?躺在炕上一星期,你就不会叫他们给你看看?”爹说:“我不敢朝你大嫂和二嫂的面儿,她们真打我,我打不过她们。”歪头说:“老三和老四呢?”爹说:“唁,别说这个了!歪头,我走不动了。”歪头说:“歇歇呢还是我背你回去?”爹说:“你背我去梨树地。”歪头说:“去梨树地干啥呢?要去你自己去,还有一里多路呢。”爹央求说:“好孩子,你从小到大就听话。”歪头说:“谁听话谁吃亏。”爹嘿地一笑:“谁说俺五儿是个傻子啊?”
歪头一只手托着爹的屁股,一只手抓着那根棍子戳戳这里戳戳那里。歪头说:“要是有蚂蚱就好了,我逮蚂蚱给你下酒。”爹好半天不说话,像是睡着了。歪头就说:“爹,爹!你别睡着了,还没到地头你就睡着了吗?”爹说:“我睡不着。”歪头问:“我小的时候你背过我吗?”爹又不说话。歪头说:“我就从来没记着你背过我,你们都拿我不当回事儿,要不我的头也不会这样。”爹似乎有气无力:“你的头,成这个样子,都怨你自家,那么高的钻天杨,你呼呼地往上爬个啥劲儿?”歪头说:“那上头不是有一个老鸹窝吗?我寻思摸两个鸟蛋煎着吃。”
过了好半天,到了梨树地。爹说:“背我到你爷爷奶奶坟前转一圈。”几个坟头在地的一角,爷俩一深一浅地晃过去。爹看着那几个坟头,说:“歪头,你爷爷奶奶的房子顶上荒了,改天你扛着铁锨来,添上点新土。”歪头答应:“行啊。”爹又说:“你看,你娘的房子边有一道裂纹。”歪头问:“哪里有裂纹了?”爹说:“那么宽的一道你没看见?”歪头说:“你别吓唬我。”爹说:“放心吧老婆子,我很快就来陪你,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冷,没人给你暖被窝。你说什么?喝鸡蛋汤?我也想喝啊,可你看看哪里还有鸡蛋?”歪头说:“爹,你咋又说胡话呢?”爹说:“老婆子你等着,我这就到山下去,打电话叫咱歪头回来。我知道你不放心这孩子,我也不放心啊。”
歪头觉得爹的身子越来越轻。歪头说:“爹,你别吓唬我,咱这就回家去。”他顾不得拿那根棍子,就忙不迭地往山下奔去。歪头说:“爹,你跟我说会子话。”
一路上,爹一句话都没说。
“一斤半”瞪着大眼,看着满脸热气腾腾的歪头:“你咋背到我这里来了?快背回家背回家。”歪头说:“你没看我爹不行了吗?你得赶紧给他扎针啊。“一斤半”说:“我说过扎不扎都没用处了。”歪头说:“你那天扎了针,今日还拄着棍子上山了呢。”“一斤半”说:“我跟你没法解释,行啊,你赶紧背回家,我这就跟着你去扎针。”歪头说:“在这里扎不行吗?你扎上针不就好了吗?”
“一斤半”吼起来:“死在我家里怎么办?”
歪头嘴角动了动,扭回头边往家跑,边说:“狗日的你赶快跟着我走!要是我爹出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一斤半”说:“你个歪头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你爹的病,是我吹口气给他装上的?”
歪头背着爹一步一步爬上那段上坡路,“一斤半”在后面追上来,后背上一个脏乎乎的皮箱子晃过来晃过去。歪头一脚踹开屋门,把爹放在炕上。爹的眼睛闭着,身子却像一个柔软的面团,任歪头摆弄过来摆弄过去。
“一斤半”捏过爹的手腕,又伸出两根手指头掰开他的眼睛,端详了半天,回头说:“不用扎了,真不行了。”歪头说:“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你赶快给他扎针!”“一斤半”说:“我叔他不行了,扎上也没用!”歪头说:“狗日的一斤半,赶紧给我爹扎上针!”“一斤半”张张嘴,一声不吭地去打开药箱子。
老三和老四一前一后进了屋,走到炕前打量一眼,都扭回头去。老三说:“得给老大和老二打电话,叫他们赶快回来。”老四皱着眉头,半天才说:“爹病成这样子,你不知道啊?”老三一拧头看着老四:“你要是知道,你怎么不来告诉我?整整半个月了我在山底下修公路,你说我咋知道?”老四说:“那我三嫂呢?她不是在家吗?她就从来没过来看看?”老三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嫂子得上坡种地,还伺候着家里鸡呀羊啊猪啊兔子啊一大群牲畜,她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老四说:“牲畜要伺候自己的爹就不伺候了?”老三挽起袖子来:“老四你故意找茬是不是?你个没良心的,别忘了,你老婆是我跟你三嫂费事劳力帮你找的,你现在成精了是不?”老四也叫:“那也算是个老婆?我一个大男人给人家养活俩孩子。”老三说:“你这样的,能找个寡妇就不错了。”
歪头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墙角水缸旁边,拿起水瓢舀了些水,咕咚咕咚喝下去。老三和老四继续辩论,好像屋里根本没歪头这个人,也根本没爹那个人。歪头喝完水,伸出袖子擦一下嘴,从案板上抄起菜刀来,走向老三和老四。
老三和老四突然停住话头。
歪头竖起菜刀,说:“滚出去!”
老三和老四对视一眼。老三说:“老五你干啥呢?爹没了我们也难受。”歪头说:“我叫你俩都滚出去!”老四说:“老五你咋了?拿菜刀对付你哥啊?”歪头呼吸沉重,突然抡起菜刀一下子砍掉地上一张桌子的角:“滚出去!”
歪头坐在一个马扎上,趴下身子,两手抓着爹树枝一样的手:“爹你不是说和我上山栽地瓜吗?你咋这么不讲信用呢?”老三和老四在外面拍门框。老三说:“老五,你别这样,爹走了咱得商量一下怎么办后事儿。”歪头说:“我要不带你上山就好了,你是累的。”老四说:“歪头你别闹了,是你四哥不对,我不该心里
憋屈守着咱爹发脾气。”歪头说:“爹你走了我咋办啊?只要你还在这个屋里,还躺在这个炕上,我在外头干活也有劲儿,心里也有个盼头。过年过节的,我回来还算有个家,你这一走,闪下我可怎么办?”老三叹口气:“这样吧,老四你去打电话通知老大和老二,我去喊几个有年纪的来。”
不一会儿,主持红白事儿的三叔来了。三叔喊:“歪头,歪头,我是你三叔,好孩子你给我开开门,我看看你爹。”歪头趴在被子上,不声不响好半天了。三叔搓着手,又说:“歪头,你是个好孩子,你爹现在走在半道儿上,咱不得好好送送他啊?你开开门,有啥事儿我给你做主。”老三嘟囔:“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犯了病吧?”三叔骂了一句:“歪头从来就没病!倒是你们几个白眼狼,一个个的病得不轻!”三叔还想说几句的,门开了。
第二天,老大和老二都回家来了。
家族里主事儿的长辈也都蜷缩着身子凑了来。
三叔问老大:“还雇吹手吗?”老大说:“雇吧,瞅着也像个样儿。”老二媳妇却说:“雇啥吹手啊?花那份冤枉钱。”老大看看老二,老二看看老三,老三看看老四。老四说:“雇吹手我没意见,反正所有花销咱五个人平摊就是。”老二说:“其实,雇不雇都无所谓,人都死了,也听不着了。”歪头自从昨天开了门后就没怎么说话,突然说:“雇!为啥不雇?这钱我出。”老二媳妇说:“既然这样那就雇吧,孬好得听听动静。”三叔说:“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那里有整套的锅碗瓢盆,等会儿我打发几个人去搬了来。你们五个孝子从现在起得守在这屋里,外头的事儿,交给我办。”
歪头一整天就窝在炕脚的旮旯儿里一动不动。老大出去一趟,哈着手回来了,说:“又飘雪花了。”老二说:“今年的年景肯定又不好。你说,这样的天气桃树还能坐住果吗?”老三说:“就你那几棵桃树,就是结满了也发不了大财。”老四说:“去年我那片果园收入还行,早早就被预订了。你说现在城里人啥点子想不出来?在苹果上打上字儿,年底的时候送礼用。”
老二站起来,绕过头朝门口躺在地上的爹,到墙角一个乌黑的桌子上去翻找。那里堆满杂乱无章的东西,酒瓶、茶叶盒、碗、筷子、装饼干的纸袋、火柴盒、油桶。老二说:“咱爹的酒呢,喝上几口也暖和暖和。”老大说:“你就知道喝酒,啥时候你也不看看。”老三说:“这么冷的天不喝点儿酒,咋熬下半夜啊!”他翻了半天,没找到,又说:“咱爹这人有意思,临走前把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老大说:“俩月以前,我回来给咱爹打了五斤,估计早就没了。”老二说:“就连点儿菜也找不着啊。咱爹不是养着鸡吗?鸡蛋呢?”歪头仍然一动不动。老四说:“谁家有牌啊?回家拿两副来。”老大说:“我家倒有,不过肯定不够两副。”
歪头站起来,谁也没注意他。一整天就没人注意他。歪头慢慢走到墙角,打开炕头的一个箱子,掏出一床揉成一团的被子来,又慢慢地走到躺在地上的爹身边,蹲下身子把被子展开,盖在爹身上,起身转到另一头爹的脚底下,往里窝了窝被角,又转回来,坐在爹的旁边,悄无声息地脱鞋子,一掀被角,整个人钻进去了。
那四个呼吸急促。老大问:“老五你干啥你这是?”
歪头说:“咱爹刚才说他冷啊。”
一支白晃晃的队伍,顺着山路往山下村子走。吹手是山下上来的。两口子,男的吹喇叭,女的打小锣。男的鼻尖上有一滴透明的水,一直悬着。他仰了头,喇叭呈四十五度向上,呜里哇啦吹一通,头上围一片黑围巾的女的,就低了头,轻轻敲一下小锣。喇叭声唱着主角,小锣声不仔细听听不分明。
吹手在前头走,后面跟一溜儿孝子孝孙。弟兄五个和四个媳妇全身皆白。老大捧一个罐子,老二提一个礼盒。儿子们都不哭,都低着头,女人们有的哭,有的不哭。老大媳妇是会哭的,老四媳妇也会哭,声音却低一些。老大媳妇哭得很有节奏:“俺那亲爹啊,有你吃的,有你穿的,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咋就走了哇?”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也哭,但没有话也没眼泪。只有老四媳妇与老大媳妇此起彼伏,互相接应。歪头不哭也不叫,揣着手往前走,眼睛自始至终一动不动,盯着最前头四个人抬着的用苇箔卷着的爹。爹的头朝前,脚朝后,穿着一双很大的花鞋。鞋底是白布做的。在庙口站着一匹纸马,停着一辆拖拉机。纸马是用来给爹骑着走的。拖拉机是雇来拉着爹去火葬场的。拖拉机手快五十了,戴着军用大棉帽,穿着黄军大衣,油渍麻花的,用一根绳子揽腰捆着,脚上穿着大棉鞋,正蹲在一边的堰墙下烤火。
队伍停下来,三叔站在最前面,声音有点儿嘶哑,又尖又细。一道一道程序走完,三叔举着一根草棍向天,大喊:“上路啦!”老大高高举起手里的罐子,狠狠地摔向地面,罐子哗啦一声碎成数片。紧跟着,喇叭声小锣声哭喊声在庙碑旁边的古槐树下响作一团。孝子孝媳妇们向爹冲过去又被拉回来,被人架着,一个个顿足捶胸,大声哭喊。那匹马被点燃了,火光冲天。
歪头注视着那群人,嘿地一声笑了。
天快要黑下来,歪头捧着一个盒子回来了,那盒子看上去很沉很沉的。老大他们早在梨树地等着,在地头一块大石头底下燃起一堆火在烤。歪头始终抱着那个盒子,站在娘的坟旁,端详着早就挖好的那个坑。三叔说:“歪头,放进去吧,让你爹好好歇歇。”歪头没反应。老大走过去,想把盒子接过来,抽了抽,没抽动。老大说:“老五你干啥呢?”又抽了抽,抽出来了。老大把那个盒子慢慢地放进坑里去。老二、老三、老四开始拿铁锨铲起土来埋那个盒子。歪头呆愣愣地站着,突然扑通一下跳进那个坑里,抱起那个盒子,躺下了。
三叔说:“你看你这孩子!”
歪头说:“我不想回家,家里很冷,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三叔说:“你这不胡闹吗?你有哥有嫂子还有你三叔呢!”又说:“你兄弟四个下去把他拉上来。看来,他又犯病了。”老三和老四跳进坑里,老三夺下盒子,老四拖着歪头往上走,歪头不走,连踢带打,老四挥手就给他一巴掌。老四说:“你再闹我就收拾你,你信不信?”歪头说:“从小到大你就没少打我,你收拾我吧,我死都不怕了,我怕你收拾我?”老大说:“老五你上来,你上来看我不一外攫头敲死你!”歪头说:“你敲啊,你敲!你是老大你敲死我我也愿意。”老大和老二也跳下坑,弟兄五个扭扯到一起,最后,把歪头弄上来了。
埋下爹的第二天,太阳兴高采烈地出来了。歪头本来躺在炕上,身子轻得像在云彩上飘,但看看窗子外面的太阳,就决定起来了。歪头穿上棉袄,一步一步,走到门口,烈烈的阳光刺了他眼睛一下。歪头扶着墙,慢慢走到磨盘那儿,靠着墙盘腿坐下来。那只母鸡刚产了蛋,挺着胸脯,一边叫一边斜着眼端详歪头。歪头的脑袋向左歪着,看上去嘴巴也有点歪。日头暖暖地照在歪头身上,他觉得身子里有一股热气在腾腾地升起来,很舒坦。歪头眯着眼睛,看看梧桐树,看看樱桃树,看看公鸡,看看母鸡。
爹在屋子里叫他:“歪头,你还不去拾鸡蛋来?你没听见那只芦花鸡在叫吗?”歪头说:“什么眼神啊你?还芦花鸡呢,分明是一只红色的。”爹说:“你还就是傻呢,什么颜色的鸡你都分不清啊?”歪头说:“我不跟你犟,跟你犟也犟不出个结果来。”爹说:“你别磨叽,收拾收拾家什,咱爷俩上山,记着拿把镰刀,先把地里的草割一割。”歪头说:“你今年没畦瓜苗吧?”爹说:“咱种个三棵两棵的,值当的烧个瓜炕?到集上买两把子来栽上就行。”歪头说:“你就是懒啊。”爹说:“歪头你说得对,我是懒,从去年一入冬,就浑身散了架一样不想动弹。——你拿回来那些钱啊,我都给你存着,留给你娶媳妇用。”歪头说:“正说着瓜苗咋提到钱了呢。我要是娶了媳妇,你咋办啊?”爹说:“你少操那份闲心。”歪头说:“要是我也离开你,你喝凉水都成问题。”爹说:“你这孩子说的,我就不信你跟你四个哥哥一样。”歪头说:“也不好说,人和畜生比起来差不多啊。”爹说:“胡说八道。你过来给我抓抓痒痒。我觉着地边上再栽上点豆角啊南瓜什么的。”歪头说:“关键是得种红瓤儿的瓜,红瓤儿的好吃。”
作者简介:
宗利华,1971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山东青年作家班高级研讨班。已发表小说作品15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作品被译介到加拿大、韩国等,曾获2003-2004年度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著有长篇小说2部、小说集4部,两部小说集被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现供职于山东淄博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