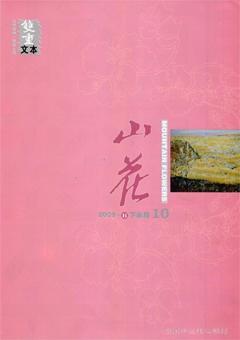丹砂的味道
肖 勤
1
爸爸把红布拿到奶奶面前的时候,奶奶生命的烛火已经完全熄灭了。爸爸知道,奶奶走得不甘心,因为他没能找到奶奶要的丹砂。自从泥石流吞没了山谷,我们已经四十余年没有采砂了。早在奶奶死十年以前,村子里的人下葬就已经没有丹砂了。
奶奶不爱种庄稼,也不爱织布绣花,她每天早晨都去半山那棵大皂角树下,对着山坳哼哼唧唧地唱山歌,唱完后就满山遍野挖草药。在又热又湿的丛林里挖草药比种庄稼辛苦,还很危险——林子是野物的天堂,青竹蛇、蜈蚣冷不防就从哪一棵药草下窜出来,把要命的毒液注进你的身体里。在大家看来,奶奶是个怪人,她喜欢到大山深处去采药,一个人静悄悄地去,一个人静悄悄地回。可这个敢到深山采药的奶奶偏偏又很胆小,只要太阳一落山便坚决不出门,她说,天一黑就有东西。
妈妈一听这话总是满身起鸡皮疙瘩,嗔怪奶奶:“您乱说什么?夜里有什么东西?”
“那些白天不敢出来的东西,它们到处窜。”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孩子似的四处环顾,低声细语,脸上充满了神秘。
爸爸刚把红布铺进奶奶的棺木,我便出世了。当时妈妈还没感到阵痛,羊水好像也没破,总之用妈妈的话说,分娩之前一点预兆也没有我就来了。妈妈说到这里的时候总是很自豪,因为在寨子里,会生崽又生得顺利的女人是吉利的象征。谁家有这么个女人,就预示着五谷丰登、家族兴旺。
奶奶墓里那块红布,爸爸说,那是奶奶去另外一个世界的灯。从阳世到那个世界的路很黑,得有灯引着去。路上还有很多鬼魂,也得靠这盏红色的灯为逝者驱赶。本来那块红布应该是丹砂的,丹砂红是驱魔的利器。可是,爸爸找不到丹砂。
2
关于我的出生,跳傩的堂祖公沉着脸说:“时辰太巧了,搞不好他奶奶的魂走时刚巧撞上他,附了他。也说不定这崽的魂还没醒透,半路不巧随了他奶奶去。”
爸爸忧心忡忡地看着他怀里的我——他怀里这个婴儿的确有点古怪,白天不醒,晚上不睡。
妈妈疼我,不许人说我坏话。她说这崽打小懂事,白天知道我们要薅草,不吵呢。妈妈上山干活时把我放在木栏过道中间,点燃一支艾香后才走,山风清凉地吹着,和着艾香味,一直把昏昏入睡的我熏到五岁。
我五岁时爸爸很严肃地与我交谈了一次。他说:“崽,不能这样睡了,你得上学,没有哪个学堂是晚上开课的。”
对于上学的意义,我并不太懂,但是因为爸爸严肃的表情,我不得不认真地听,可我做不到爸爸要求的事——每天去学堂,我总是趴在课桌上睡觉。
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我一直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我确信我是从出生那天就开始做这个梦的。梦里总有那座红色的山,山下堆满红色的砂,人们忙碌着,手中也沾满了红色的砂。你无法想象那铺天盖地的红色天长日久地出现在一个孩子的梦中,这对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来说具有多么大的魔力,它像一个咒语,不断地召唤我走进那片红色的海洋。而这鲜艳的海洋只有在黑暗的映衬下才显出它夺目而璀璨的光芒。当太阳升起,世界绿成山岭、黄成田地、灰成房屋的时候,那片海洋便被这些色彩搅得乱七八糟。
这样乱的色彩让我异常疲惫,我宁愿睡着。
我一闭上眼睛,我要的红就回来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木屋里,桐油灯火苗美丽地扭动着旖旎的身姿,风从窗子缝吹进来,它跳舞的样子是朝我这边飘的,风从灶房的篾席缝里吹过来时,它又跳着舞朝沉默地吸着水烟筒的爸爸那边飘。透过橘红的火苗,我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我看到火苗的深处有一个红色的世界。我看着那个世界快乐地笑着,爸爸以为我是看着灯那面的他笑,便也笑,吐出一口烟说,乖崽崽。
3
跳傩的堂祖公老了,跳不动了。自从放下傩具,堂祖公的夜就长了,大把大把的时光沉淀起来,多得让堂祖公难受。刚开始的时候,堂祖公一个人坐在火塘边,把他的大半辈子的岁月一页页地往后翻,翻到伤心的那页时,挤出一两颗浑浊的老泪:翻到娶堂祖婆那页时,就咧着缺了一半牙的嘴笑。
但是再精彩的书总是有看腻的时候,何况是自己写的书。这样过了大半年,堂祖公实在是无事可做,整天就跑到奶奶以前爱去的皂角树下咿咿呀呀地哼歌。
夏天的皂角树下是很凉快的,难怪奶奶常坐那儿悠然自得地唱她的歌。奶奶命好,娘家是有名的淘砂王,当年带过来的那些嫁妆足以让她清闲自在地过一辈子,她想采草药也好想唱歌也好,爷爷都由她去,只负责把她采来的草药晒干,攒足筐后担到山那边的集镇上去换钱。
巨大的皂角树像一把翠绿的大伞。我偷偷跑到那里睡觉,等放学的钟声响了后,才背起书包回家。可是这片领地被堂祖公发现而且侵占了,那天风正好,凉凉爽爽的,侵占了我领地的堂祖公站在上风口,不但不报以歉意,还一把揪起我,脱了我的裤子就要打我屁股。
我急得哇哇叫,说:“你敢打!你打我我就告你!老几十岁的人了还唱情歌,不要脸!”
堂祖公高高举起的大手陡然停留在空中,堂祖公是寨子里威望最高的人,这样一把年纪还唱情歌实在是件丢脸的事情,何况是我这样一个半大不小的娃崽发现的。
“嫩臭娃儿!你晓得个屁!啥子叫情歌?你祖公啥时候唱情歌了?”
“昨天你就唱了!”我气咻咻地提起裤子,心想从明天起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一条裤腰带,免得哪个都可以拉下我的裤子。
“昨天我唱啥了?”老谋深算的堂祖公瞅了我一眼。
“你唱:呀咿呀唉,妹妹的荒瓜不开花;呀咿呀唉,哥哥不在怎开花!”我学着堂祖公的嗓音像模像样地唱起来。
这一唱不要紧,吓得堂祖公一把过来捂我的嘴。他侧过身来的样子太急,像是扑着跪倒在我面前,逗得我咯咯咯地笑起来。
“鬼娃崽!该死的鬼娃崽!”堂祖公气急败坏地咒骂道:“读书不行,学人家唱歌记性倒好!”
我昂着头说:“祖公你自己说的,我是奶奶投的魂,奶奶会唱歌,我当然也会唱。”
堂祖公再次吓坏了,用老狐狸一样的眼神望着我。拍拍草皮坐下来说:“来,我们试试看——我再唱首歌,看你会不会学。”
堂祖公清清嗓子唱开来。歌很长,可难不倒我——不是唱山就是唱水不是唱水,就是唱树,还有山里寨子里常见的鸟儿花儿。
堂祖公唱完后,扬扬眉毛看着我,挑衅似的。
我撇撇嘴,也扬扬眉毛,得意洋洋地唱开来,一字不差。
堂祖公这回真被我吓呆了,他瞪着一对死鱼似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呆若木鸡地咽着口水。半天,他突然一把抱起我就往山下走。我也吓坏了,拼命挣扎着叫:“没放学呢!你放下我!我爸要打我了,我就告你!”
堂祖公不听,擒我像擒着一只小鸡崽,顺着山坡一溜小跑就到了我家。
“坏了,这娃崽真中邪了。”气喘吁吁的堂祖公焦急万分地对刚放下箩筐的爸爸说。
爸爸茫然而木讷地看着我说:“他不是好好的吗?”
“不对!”堂祖公指着我,斩钉截铁地说:“他和他奶奶真撞上了!”
4
堂祖公的论断,爸爸不太信。他是读了几天书的人,
他读的书和堂祖公看的那些不一样。思忖了半天,爸爸说:“他祖公,那您说咋个办呢?”
“给他冲个傩吧,把那啥……冲走。”堂祖公甚是忧虑地望着靠着木栏杆摇摇欲睡的我:“你看看,白天不醒,晚上不睡。不是那啥了,会是啥?”
“咋冲法?”爸爸一时没了主意。
“今天晚上,把他领我那儿去,我先给他烧个蛋,看看吉凶再说。这傩可不敢乱冲!”堂祖公说。
我一听到蛋,猛地醒了。
上次妈妈走夜路回寨子,阴风吹歪了她的嘴,堂祖公也替妈妈烧蛋了。热腾腾的熟鸡蛋从草木灰里刨出来,剥开壳,香死人了。堂祖公剥开蛋黄后,指着中间斜斜的一道裂缝说:“女娃,你是撞上落沟魂了。”
妈妈被吓得哭起来,半边僵硬的嘴巴扯着,很吓人。
堂祖公让妈妈把蛋吃掉。我想吃,却被堂祖公一巴掌打在手背上,他厉声喝斥道:“给你妈烧的蛋,只有她吃了才能解!滚一边去!”
只要能吃上香腾腾的热鸡蛋,我才不在乎撞上了什么魂!
吃过晚饭,堂祖公带着我回他的宅子。爸爸不放心地跟在后面说,叔,顺便给他看看作业。
堂祖公瞟了我一眼,说:“这崽崽聪明得很,等冲走了那啥,他自会是个好学生,不着急。”
堂祖公的宅子太深,一样的木栏式木屋,堂祖公家却一式盖了三转,只留着进门那一转没建,从远处看去,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我随着堂祖公走进那张“嘴巴”,只觉得冷。
我说:“祖公,屋里缺太阳。”
堂祖公说:“屋大了都这样,热天凉快。”
我说:“不好,缺气。”
堂祖公愣了愣,说:“啥气?”
“人气。”
堂祖公呆若木鸡地站在空荡荡的院子中间,微张着嘴巴,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
我没理会堂祖公那诧异的表情,径直往里走。
走进堂屋,我突然嗅到一股奇异的味道,那味道我好像很熟悉。可这味道在寨子里从没有出现过,我确定我也从没嗅到过。我站在堂屋正中,冷不丁地对堂祖公说:“祖公,我要!”
“你要啥子?”自从我说屋里缺气开始,堂祖公的表情就一直挂着莫名的疑惑与忐忑。堂祖公是跳傩的,他能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他也许又看到什么了吧?
“你屋里藏着的东西。”我歪着头说。
“我屋里藏什么东西了?我屋里除了几斗米、几坛油,还有啥子?”
“有。”桐油灯闪了闪,我嘟着嘴说:“那红色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表情。堂祖公临死前说,我当时的表情是“神秘而诡异的”。堂祖公被我的表情吓坏了,两条可怜的腿不断地哆嗦着。那一刻,堂祖公确信我来时的灵魂与奶奶走时的灵魂冲在一起了,奶奶的灵魂附在我身上没走。五岁的我站在祖公的堂屋里,理所当然地盯着祖公,等着祖公把红色的东西交给我。
祖公的表情在我看来才叫怪异!他用那双充满恐慌与自责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从神龛后面拿出一个木盒子,放到八仙桌上打开来——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仡佬土布,等最后一层土布打开后,我眼前是一簇幽暗的红砂。
祖公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小簇来,不敢多用一分力,也不敢少用半寸劲儿,然后瞪大了眼,万分小心地半鞠下腰,递到我面前。
那簇砂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咚咚直跳,开始那声音只是在心里轻而细地响,后来汇成溪汇成河汇成澎湃的海浪,轰隆隆地响在耳畔。梦里那座山就是这样的红色!梦里风中穿越过的气息就是这簇砂的气息!我睁大了双眼,控制着自己胸中升腾的欲望——莫名的欲望——我想吞下它!吞下这捧红砂后,它便永远与我相依相伴了,我再不用在黑夜里睁大了双眼找寻它,再不用在白天的梦境里奔跑着追赶它!只有吞下它,我才能真正地拥有它!
桐油灯的火苗静而直。没有风,砂的味道就直直地扑进我的鼻腔和胸腔。
堂祖公用通灵时才有的独特神情恭敬地对我说:“崽他奶,你要,就拿去吧,想给我留就留,不想留就都拿走吧。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到了那边,别忘了等我过去时,半道上接接我。”
崽他奶?
我往身后看了看,背后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屋子里只有我和堂祖公两个人,可堂祖公却盯着我叫崽他奶。
我吓坏了。心又开始咚咚响,堂祖公的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点夸张地扭曲、变形,祖公的眼睛变成了一张黑色的网,把我的身体拉着不断引向网的深处……
我突然惊跳起来,嘶声尖叫着冲出屋子,屋子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使劲地想把我揪回去,我便使劲地挣脱,一头扎进雾色苍茫里。
寨子睡了,白天所有的气息也睡了。可是山的深处却有着一股浓郁的气息还醒着,在不断地向毫无方向地奔跑着的我温柔地呼唤:“来啊!来!”
我光着脚,朝着那个方向奔跑去。夜浓成了一团墨汁,可前面却有一串火苗在燃烧。堂祖公站在背后,还在幽灵一样急促又低沉地叫:崽他奶!崽他奶!
5
当爸爸找到我时,我正安静地睡在武陵山脉的怀里,巨大的泥石流截断了祖辈采砂的路,也阻断了幼小的我狂奔的脚步。我靠在一块红色的砂石边上,那是一块遗弃的废料石,我却宝贝似的抱着它,嘴里还含着没咽下的红土,幸福万分地沉睡着。
爸爸摇醒我的时候,我困涩地睁开眼睛,对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鸡蛋呢?”
鸡蛋到底没吃着。堂祖公在我面前也再不提冲傩的事情,只是每次都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我。那目光里有慈爱,也有惧怕,有亲切,也有惶恐。我整天反复推敲堂祖公的眼神,这严肃认真的思考占去了我不少睡觉的时间,端起碗的时候我在想,坐在课堂上我也在想。到了晚上,运转了一整天的脑袋累得不行,倒头就睡了。这在别人看来是个好兆头,说明白天不醒晚上不睡的我终于渐渐恢复了正常。那天我放学回来,堂祖公正坐在我家灶前和爸爸喝酒,看到我气喘吁吁地冲进门扑到水缸边舀水喝,堂祖公长长吐了口气,对爸爸说:“幸好把丹砂给他奶奶了。要不这孩子怎么会好?”爸爸转过头,一把揪过我,拍着我的脑袋认真地问我:“你奶奶走时你有感觉吗?”
我不太听得懂爸爸的话,只得茫然地摇着头。却突然想起那晚上堂祖公盯着我叫崽他奶的情形。我生气地指着堂祖公说:“祖公骗人!他唱山歌被我听到了,怕我告他的状,半夜三更的把我骗到他屋里冲着我乱喊,想把我吓疯。”
堂祖公欲辩又止,一脸苦笑,长叹一口气,揪心揪肝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想把谁吓疯!这丹珍!”
丹珍是奶奶的小名。
听堂祖公这沉重的一唤,爸爸确信了堂祖公所说的一切,他把我像宝贝一样搂在怀里,生怕我再有什么闪失。
此后的十余年,堂祖公对我始终敬而远之,不冲傩了的堂祖公闲来无事,便教些半大不小的娃崽认字。我不想睡觉的时候便混于其中,看他教别人,每次堂祖公看到我走进他堂屋,都会极认真地和我打招呼:“来了?”
我觉得堂祖公对我的态度很奇怪。我只是一个孩子,他却偏偏当我是大人一样。有时候,孩子们在齐声念书时,他会走近我,讨好似的对我说:“怎样?我教得还行吧?”
我蹬鼻子上脸,拿腔拿调地答:“唉,还行吧。”
这时候堂祖公脸上便会挤出菊花似的笑纹来,把头
不停地点着,颇有点接受表扬后的激动。教孩子的时间长了,总有人觉得欠他人情,便要给钱和米。可他通通不收,只浅淡而懒散地说:“收了米油在手,不如存了丹砂在心。”
这话让人听不大懂,可自有一朵莲花盛开的气息。从堂祖公那推辞不已的语气中弥漫开来。
我稍大一些后,堂祖公就领着我走山串寨收山歌。白天我听人唱,晚上回来堂祖公听我唱,边听边在灯下眯着眼睛把它们写在牛皮纸上。
装满第一箱歌集后,我已经到了看见异性会莫名脸红的年龄。那年暑假,山腰的妹仔唱:“风不吹松,松不动哦。”我听了,想也不想就在山这面回唱:“妹不逗哥,哥不疯嘞。”堂祖公打趣我道:“长大了,心活了哦!”
那天晚上,堂祖公终于坐在火塘边,郑重地和我提起了我的奶奶。
原来奶奶是仡乡出名的才女,在二十里外的县城里,没人不知道学堂有个比男孩读书更“行实”的她。可是富有的砂矿老板——我的外祖公不让她去县城念高中——那时候,守着一座砂矿比读书强多了。再说,在外祖公看来,女子读书最终是替夫家读的,何苦花那几串冤枉钱。可奶奶不愿意回山里,因为奶奶的心已经被县城中药房里那个抓药崽揪走了。奶奶教他学会了许多诗,他教奶奶认得了许多草药。拧不过外祖公,任性的奶奶干脆在一个雷雨夜与抓药崽失踪了。
“大半年过去了,我在县城豆腐街找到她——我听说豆腐街里有个唱山歌唱得特别好的女人,我想那一定是你奶奶。”堂祖公叹息着说:“我当时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孩子,要是知道,我就不会把她的落脚点告诉你外祖公!哪怕你外祖公给的钱再多,我也不会的。回到寨子,你奶奶跪着求你外祖公,要他放她回去,这时候我才知道她怀孕了。可你外祖公不肯,大发雷霆,强迫着给你奶奶喂了打胎药。”
“你奶奶机灵,一喝完药就自己抠喉咙催吐,又猛灌绿豆汤,然后捂着肚子上山找草药——看来那抓药崽还真教会了她不少东西,最后居然把孩子保住了。”
我瞪大了眼,仿佛听着一个遥远的神话。以我的年龄来说,接受这样的现实和这样的故事太沉重也太陌生了些。而且在妈妈给我的记忆里,奶奶单纯如一个女孩子,一生不知道织布绣花种庄稼,终日唱歌采药。她命好,爷爷宠她,啥都由着她,田间地头的活儿,从不让她沾。
“她唱歌,是在等人。她采药,是在想他。你爷爷宠她,其实是不愿管她——他是不喜欢你奶奶的,当年娶亲只是因为需要你奶奶的嫁妆。”堂祖公说到这里,表情很痛苦:“是我害了她,我不该图那一百元赏钱。”
我还是不信:“奶奶那么胆小,才不敢干这样的事情哪!”
“她是被你外祖公咒的。你外祖公说,等她死的时候恶鬼要来收她,丹砂也照不亮她过那边去的路,她会在劫难逃。这话天天说年年说,你奶奶听着听着就听进了,人也像是听糊涂了,有时候,大白天指着空荡荡的院子神经质地喊,来了来了!赶出去赶出去!倒是吓得你外祖公一家心惊胆战。后来干脆把她嫁给了你爷爷。那时你爷爷刚死了你大奶奶,一个人带着三个娃崽,包谷饭都吃不上。你奶奶嫁过来时,嫁妆厚实得几个寨子的人都来看稀奇。”
“我奶奶怀的那个崽崽呢?”
堂祖公放下毛笔,郁郁地说:“嫁妆厚实,当然是因为多带了个人嫁过来。”
说完,看了看我,欲言又止,忍了半天,终于说出来:“就是你爸爸!”
我傻了。半张着嘴巴,口水从嘴角流出来也不知道。
堂祖公摸摸我的头,又开始埋头在牛皮纸上写字,我迟钝地看着堂祖公花白灰乱的头发,隐隐地感受到了堂祖公对于这个机灵却又敏感的奶奶的那份愧疚之情——他带着我跋山涉水地收集山歌,是在替一生都活在山歌般梦幻里的奶奶续梦呢。
灯光暗下来,该剪灯芯了。堂祖公抬起头,拿起剪刀剪了两下,灯光一下子欢喜地跳跃起来,蹿出红亮的火苗。火光一闪一闪,映出堂祖公眼睛深处的愧疚和忧伤来。
6
堂祖公对我一直很客气,因为他直到死时都确信无疑地说,我五岁那晚和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奶奶在和他说话。
十多年后,我一再对躺在床上薄得像片叶子的堂祖公说:“祖公,那是迷信。”
“不是,是你奶。”堂祖公痛苦地答。
“祖公,世上没有鬼魂。”
“那你怎么解释你一进屋就闻到了丹砂的味道?又怎么知道它是红色的?”
是了,我的确不知道祖公屋里那特殊的味道来自于一种叫做丹砂的矿物,我更不知道它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黑还是白。那年我才五岁而已。
可我当时分明不假思索地说:“红色的东西。”
看我答不出来,祖公才痛苦万分地道出了另一段往事:
“你奶奶临死前来求过我,问我讨丹砂。你奶奶说,她怕过那条路时太黑,又怕红布不够亮。她说她爸爸咒她咒得那么凶,她没有丹砂一定会落到河里去。她落下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她与他约好了,生时没能在一起,死也要在那边相聚。
“她知道我有一捧,她说她只分小半捧。我没给——你想啊,我一年要冲多少傩!要开罪多少鬼魅邪物!砂少了,我也怕我走不过那段路。所以没有给她。你奶奶当时哭得可厉害了,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跟个小姑娘似的哭!”
祖公绵长又愧疚地叹了口气,又说:“她怕,没敢走,半路撞上你来投世,就附了你。我要早知道她那样怕,我给她就是!可我偏不给她!你奶奶生时没能好好过上一天自由的日子,死了还得附在你身上游荡那么多年!都怪我啊!怪我!我一辈子替别人冲傩驱魔,却冲不了自己的傩驱不了自己的魔!我害了她一次又一次啊!”
看着千悔万痛的堂祖公,我终于明白那个夜晚堂祖公为什么会用那种怪异又诡秘的表情对着我。
人一老,便成了孩子,胆小而敏感。干巴巴的堂祖公躺在病床上,已瘦成一片树叶,全然不像以前那个威风八面通灵得道的傩师。我安慰他说:“祖公,奶奶不会怪你,你也不要担心什么了,世界上没有魔,人死了也没有灵魂。奶奶不需要丹砂,你也不需要!”
哼哼。堂祖公讥笑我:“你懂什么?你懂,那你说给我听听——你一直偷吃着矿石长大,为什么?”
我愣了,无言反驳。从跑到山谷口睡了一夜后,我便经常跑到那里选成色好的矿石,放在书包里偷偷吃。
“那是因为,你的骨头里流着咱仡乡的血,我们需要丹砂,你也需要丹砂。我们的灵魂和骨血里都缺不了丹砂!”堂祖公一字一顿地替我答。
关于丹砂的诱惑,我一直无法破解,直到高三那年,爸爸突然进城来,在校园的枫树脚,他望了一眼落下的枫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去看看,找准了病,安心。”
爸爸说的安心,既有安他自己的心的意思,也有让我安心好好考大学的意思。
我听话地和爸爸上了一趟省城,找医院的时候我牵着爸爸的手,因为爸爸没有进城的经历。找到大夫后爸爸便牵着我的手,因为我永远是他的儿子。他把我引到大夫面前,万分仔细地将我小时候的事说给了大夫听。这一说就说了四天半——因为每个医生的回答他都不满意。
直到有一个医生也用很认真仔细的口吻回答他说:“也许是那时候生活困难,缺营养,孩子缺锌,睡不好,有
异食癖。一般来说,有这毛病的人,会有自我选择的意识,他身体里缺什么元素,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带有这种元素的东西来进行补充。也许,这孩子缺的东西,正好丹砂里有吧?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你是否赞同,但是你的确不用太担心——你的孩子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这个解释终于让爸爸不停走着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比较相信这个答案。
“只要不是脑子有病就好。”爸爸忧郁地看了我一眼,长吁了口气。我是家中的老小,尽管在学堂上课我经常趴着睡觉,但我仍然成了寨子里最优秀的学生。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寨子里的神童。可我越优秀爸爸越害怕——他总担心我突然有一天会一头再栽回五岁以前的状态中去。这样的担心一直困扰着爸爸,这些年,爸爸的烟酒量越来越大。我可怜的爸爸!
我知道,爸爸心头还埋着一层心事,犹如不接纳奶奶一样,寨子里的人也并不甚接纳爸爸。别人家插秧时有人帮忙,我家插秧时是没有人帮忙的,那几个伯伯,爸爸的哥哥们,总在那一段时间里忙,“忙得实在是顾不过来”。在寨子里,我是妈妈唯一的骄傲,堂祖公是爸爸唯一的酒友。这些年我和爸爸都在共同为彼此做着相同的事情——我替他坚守着那个人人皆知的秘密,怕他受伤害;他也替我抵挡着这个人人皆知的秘密,怕我受伤害。
应了医生的吉言,十九岁那年,我嚼着家乡的砂石,骄傲得像头小山羊似的昂首走出了大山。
7
就在那年冬天,堂祖公去世了。走的时候一直念叨说,过那段路时奶奶肯定会来接他。
“你奶奶她记情,心好。”堂祖公不断对我说,仿佛奶奶的灵魂还在我的身体里一样:“我把砂全给她了,她一定会原谅我,会来接我的!”堂祖公说着,目光里充满了渴求与希望。
我不想继续与堂祖公争辩下去。这个病床上的老人对他要去的那个世界是执著的,尽管要走一段艰辛的路,可他还对路前面的世界充满着希望,我没有必要打碎他的希望。就像我现在还生活着的这个世界,路何尝不是艰辛而坎坷呢?可我也还得要走,充满希望地走。
所以我对堂祖公说:“会的!会的!”就像是奶奶在作出承诺。
祖公这才安详地去了。走时身下放了偌大一匹红布,红布不是普通的红棉布——爸爸用编箩筐换的钱给祖公买了一块耀眼夺目的绸布,它在阳光下放射着夺目的光芒。
祖公安详地闭上了眼。也许,他这一路走过去的,是一个平坦而幸福的世界——因为他的坦诚与忏悔,已经把他去往那个世界的路清洗得一尘不染。而那块耀眼的红绸布,已把通向那个世界的路照耀得光华灿烂。
作者简介:
肖勤,女,仡佬族,贵州湄潭人。1976年生。喜爱文学、漫画创作,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诗歌、散文、杂文,于2004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发表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杂文月刊》、《新青年》等报刊。贵州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