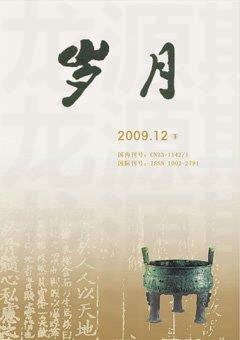论《长恨歌》的艺术特色与叙事手法
董 卫
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上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而这种“独立的思考”的结果便是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恨歌》来窥探一位女子在上海40年巨变中的生活。
《长恨歌》从王安忆众多类似题材的小说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众多的奖项,是王安忆写作历程上的一座丰碑。至今学界对《长恨歌》仍褒贬不一,有文学评论将之归为张爱玲的“延续”,认为它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
而事实上,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仍继承了她以往小说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角度。同时也竭力突破自己,增添了更多细腻而诗意的环境描写,微妙而独特的心理刻画。在结构上则大开大阖,收放自如。创作风格虽沿袭海派,但又有所创新,自成一格,蔚然有大家之风。下面就从这些层面详细解析《长恨歌》的艺术特色,希望由此发掘出《长恨歌》超越作者本人和前人的独特之处。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一贯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可以使作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摆脱视角限制使作者获得充分的自由。叙事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而王安忆在小说中的具体叙述中却不采用这种“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退缩到一个固定的焦点上。所有的叙述只围绕这个焦点进行,这个焦点可以变换,但变换之后的叙述也只围绕变换后的焦点进行。王安忆对这种叙事人称把握得相当纯熟。《荒山之恋》中甚至不出现一个人名,全用她和他来替代,读者看了也不会混淆,原因就是作者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将男女主角的叙述分开进行。讲男主角的时候只讲他以及跟他有关人的生活和心理,讲女主角的时候也只讲她以及跟她有关人的生活和心理,一直到他们在故事中会和。这种叙事方式其实和中国古代小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长恨歌》的叙事人称虽然也是这种变体了的第三人称,却在具体的叙事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所形成的行文风格也各相异趣。在《长恨歌》中最能体现这种叙述变化的要数小说第二部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描述王琦瑶与康明逊情感碰撞和交融的部分。小说第二章以王琦瑶为叙述焦点,着重描述王琦瑶的生活和心理,其他人物只写跟王琦瑶生活交汇的部分,无从探究他们的心理。康明逊对王、康情感的态度均来自王琦瑶的猜测和推断,从而给读者设置了很多悬念。而小说第三章11节以康明逊为叙述焦点,重新讲述他与王琦瑶的故事,同时插入了康明逊的心理活动。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是前一部分王、康情感故事的一个补充叙述,将前文中王琦瑶和读者的疑惑一一解开。这样,同一个故事用不同人的角度分别讲出来,每一次叙述又都提供给读者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彼此间并不相悖,因此每一次叙述都会给读者一种新鲜、陌生的感受,刺激读者阅读下去。这种复沓式叙事的成功运用不仅可以激发读者对小说内容的兴趣,也可以方便读者更深入地透视小说人物的思想个性。
显然,作者在《长恨歌》的小说布局和结构安排上耗费了不少气力,从而成功地拉开了与作家以往小说的差距。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了一章22页的巨幅笔墨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这段描写以潜藏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观察所有的人和物,使它们染上了深深的叙述者的印痕,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为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感情基调。
王安忆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个写作中篇小说的高手,她成功地将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移植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长恨歌》的总体结构分为三个看似独立,实则相连的部分。第一部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王琦瑶风光一时的少女生活;第二部则以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王琦瑶无疾而终的第二段恋情;第三部以七、八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王琦瑶母女的情感及生活。小说的三个部分分开来看,每一部都有开头、发展、高潮、结局,每一部都可以切割开来、独立成书,丝毫不影响各部分的结构和故事的行进。可是,纵观全局,每一部又都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难以完全割裂开来。这种“藕断丝连”式的结构安排体现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炉火纯青的功力。它不仅使得整部小说在结构上大开大阖、收放自如,而且延长了读者对作品的感知时间,适度偏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读者始终保持高涨的阅读兴趣。
《长恨歌》始终给人结构清晰、条理分明的感觉,不仅得益于它结构上的收放自如,更归功于作者对小结构的细致把握。小说的每一部都按照故事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局分为四章,每一章又按内容的丰富程度分为若干节,而每一节都有一个标题,故事就围绕这些标题的内容缓缓展开,使得整部小说的进程显得徐缓有度,错落有致。
在读者看来,《长恨歌》更大的艺术魅力似乎在它的淡然轻盈却又细致精湛的人物心理刻画。作者用自在、轻微的笔触平淡、耐心地叙述着自然发生的故事情节来揭示人物的微妙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无时无刻不和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发生着细致的互动。这种不断变化中的两性心理及两性关系描写是《长恨歌》最精彩感人的部分,它们在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女性视野中的同性关系及同性心理描写,王琦瑶与吴佩珍,王琦瑶与蒋丽莉的相识、亲密到决裂过程中双方心理的微妙变迁。第二,女性视野中的男性心理及性格特征,无论是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还是阿二、萨沙、老克腊,他们都具有上海男人的特性懦弱、自私和无情。第三,亲情关系的淡漠,王琦瑶与母亲以及外婆有着巨大的心理隔膜,她们之间情感的表达近似于无情和淡漠。
王安忆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不断变化中的两性心理及两性关系,虽然在创作风格上继承自海派张爱玲,可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体验,在人物心理的变迁以及人物关系的转变上描写得更细致入微、引人入胜。
王安忆的小说充满着作者自己的生活痕迹。上海平淡安闲的市民生活,文工团独特的氛围与体验,文革时下乡的艰辛,女性成长中微妙而奇特的心理,这些都是王安忆驾轻就熟的题材。她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中透露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最能体现这种女性意识觉醒的,在王安忆看来就是女性“性”意识的觉醒。然而在男权社会中,这种“性”意识的觉醒带给女性的只有毁灭。因此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尤其是早期作品中,情欲和死亡一直是故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主导着故事的发展。如《荒山之恋》中男女主人公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莫可名状的情欲而抛家弃子走向死亡,女主人公在这段关系中的大胆和主动让人心惊;《岗上的世纪》和最富有争议的《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竟然只是因为身体的接触而爆发出无法遏止的情欲,这种灾难性的情欲带给前者毁灭性的后果是牢狱之灾,带给后者的则是屡次没成功的自杀行为。这种触目惊心的情欲描写以及情欲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在《长恨歌》中不再凄厉和可怖,转而变得温情脉脉,甚至滑稽可笑。小说中王琦瑶“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缓慢的小溪入河、河流汇江的过程,越到最后越是汹涌澎湃、不可遏止。王琦瑶和李先生的生活是情欲的萌芽,朦胧而无知觉;她和康明逊的“围炉夜话”以及之后的挑逗和试探,是情欲的发展,这里的情欲已经变得温婉细腻,带有感情色彩;而她和老克腊的畸形的“爱情”是情欲觉醒的高潮,最终导致她死于非命。王琦瑶的死带有浓重的荒诞意味:老克腊和众人眼中的王琦瑶有魅力、有品位、神秘而迷人,但在杀死王琦瑶的长脚看来,她既老又爱装俏,显得古怪又滑稽。最后她的头发留在枕上的那一滩肮脏的染发剂彻底消解了王琦瑶在读者心中美好的印象。她的死就显得荒诞离奇,甚至引人发笑。
《长恨歌》之所以获得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和喜爱,不仅因为它具有超越以往的独特的叙述角度,精巧的结构布局,细致的心理描写,强烈的女性意识,还因为作者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独特的写作模式,在这个沧桑巨变的时代中留下了自己独立思考后的辉煌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安忆.荒山之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3]王安忆.小城之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4]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董卫,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