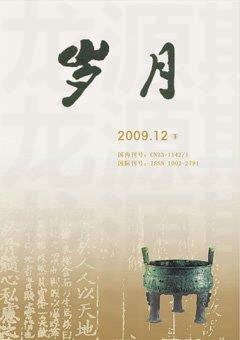从“人化物”到“异化”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许多元命题的提出,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对这些元命题的阐释——这一踵事增华、与时俱进的探讨,既丰富了思想的蕴含,也推进了思想的发展,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探讨此类元命题,对认知思想史之精髓、给人以多元的启迪大有裨益,也便于扬弃,古为今用,立足传统思想而促进新思想的形成。
《礼记》一书,乃汉代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儒家学者以儒学思想为本,兼收并蓄,以期建立适应大一统局面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目标是基本上达到的。职是之故,《礼记》一书,尤其值得重视,从上层建筑这一层面上来理解,《礼记》所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意蕴将会彰显出来。上层建筑,儒家称之为“礼乐”,有时亦简称为“礼”,《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儒家也特别重视“礼”、“乐”的相辅相成——“礼”在于严肃等级,修明道德;乐在于感化人心,和谐情感。《论语·泰伯》曰:“立于礼,成于乐。”极其重视“乐”的教化养成——因为“礼”使人循规蹈矩,而“乐”使人化于规矩,成为自觉的行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儒家的理想则是:要以“礼”来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要以“乐”来教化人民,使得人人习惯于那样有秩序的生活,同心同德,并且感受到唯有那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为建构大一统帝国的上层建筑而尽职责的《礼记·乐记》,专门探讨音乐,自然会比较深入地探讨音乐的政治教化作用,着重说明音乐是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部份,而非谈论音乐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礼记·乐记》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具有丰富的认识论的意义,值得深入探析,如“人化物”这一命题,就蕴含了丰富的意蕴,有着辩证法的思想。
《礼记·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1]
旧注以为此一节所论,乃“人生至道也”。《正义》曰:“此一节论人感物而动。物有好恶,所感不同。若其感恶则天理灭,为大乱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礼乐而齐之。”认为,“物”(客体)为人(主体)所认识,并不是人之天性使然,而是人本性中的一种冲动、知性——“欲”,与外物相接触,便发生认识作用,并能形成喜好和厌恶两种欲念,故尔郑注以为:“言性不见物则无欲。”如果对人之本性中的这种冲动、知性——即“欲”,不加节制,而外物又一直在引诱着,人则追随着无限的贪欲而沉浮,最终会妨碍、甚至消泯了人的天生的理性,如此则“人化物”——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即仅仅保留了人的自然性,而消泯了人的社会性。人为物欲所支配,最终走向了人的对立面,人成为异己化的力量而存在——即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相疏离。在《乐记》作者看来,这样的所谓“人”,就会萌生“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逞其私欲,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此大乱之道也”。因此,就应特别注意于教化,使之节制“欲”而秉有人之本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物至而人化物也”,是《乐记》一个具有深刻而丰富意蕴的命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孔颖达说:“外物来至,而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欲也。”[1]孔氏的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由于受经学之束缚,并不通透深刻。“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有机械论的倾向,并未探抉到其根本。在孔颖达看来,人一旦丧失了自己的理性,由其自身的欲望所操纵,不能有所抉择,则为外物所役使,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即“人化物”之后,人的“善”“恶”完全由物之“善”“恶”品性所决定。因此,要竭力创造好的社会环境,铲除“恶”物,使人接触“善”物,从而达到大治大化。
孔颖达的这一认识,也是由《乐记》的基本思想所决定的。《乐记》着重探讨乐的起源及其政治作用,并且从上层建筑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因“物”而动“心”,由“心”而生“乐”,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情所必不免;而乐又能够摇荡性情,影响于人,因此,《乐记》更重视乐对人的教化作用,要慎其感之者: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1]
正因为《乐记》认识到乐对人之教化如此重要,对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积极反作用,孔颖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层意思:
夫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乐之善恶,初则从民心而兴,后乃合成为乐。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1]
这样看来,孔颖达所说“人化物”,主要是指“恶”物感人而为“恶”,是应该禁绝的;至于“善”物感人而为“善”,则是应该积极提倡的。按,惠栋校宋本云:“‘而人化物也下脱注‘随物变化四字。”卢文弨云“惠栋据《史记集解》增。”[1]那么,所谓“人化物”,则指人之“随物变化”,即人的心智随物迁化,而受物欲的支配,物最终成为人的对立面、异己化。孔颖达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人一旦为物所役使、操纵,则会丧失其自身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仅仅保留其自然属性,人外化为物的役使对象——即人为其自身所生产的“物”所役使,如此,则无论物之“善”抑或“恶”,对人来说,都最终会役使人(主体),从而使得人(主体)物(客体)之和谐共处变异为物(客体)与人(主体)之对立。也就是说,在万物一体的世界中,由于人(主体)的无限贪欲,破坏了人与物(客体)的“互主体”之“天人和一”的和谐共处关系,人试图无限占有、控制物,人(主体)的这种活动致使原本和谐共处的物走向人的对立面,成为异己的东西;也使得人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也使得“互主体”的人与物关系走向其对立面,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效应的现象,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异己的力量,即异己化——异化。职是之故,无论“善”物抑或“恶”物,最终都会成为控制、役使人(主体)的力量,成为人(主体)的对立面、异己力量,从而使人(主体)丧失其人之为人之“天性”——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此,《乐记》所提出的“人化物”之深刻处,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命题的思想所在。
当然,《乐记》及其疏注者无法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既有其历史局限性,也与《礼记》的写作宗旨相关。《礼记》是为适应大一统的形势而建构上层建筑,重在上层建筑的和谐平衡,《乐记》乃是在“礼”之“为异”(区别等级)之后,阐明“乐”之“和同”(和谐共处)的。故尔,《乐记》有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1]从礼乐之相反相成以建构上层建筑,致使“无怨”“不争”和谐共处这一现实目标来看,《乐记》之“人化物”之意旨所在,乃要求人节制自身之知性、欲望,从其自觉理性出发,使之合于封建的社会规范要求。因此,《乐记》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乐之“和同”之同时,特别重视礼之节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并且强调礼乐之相反相成。因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故尔当人之心智应接纷繁外物之时,则会形成好恶之欲念——即“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因其好恶之欲念而人则随物变化,为物所役使不能自拔。从这一认识水平出发,《乐记》作者认为就应该特别关注为人所接触的外物——“先王慎所以感之者”[1],极力使那些符合情性之正的“物”为人所接触,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天性之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乐记》从伦理和政治标准上来谈论音乐,“乐者通伦理者也”,“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并且认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即追求符合情性之正的、合于礼之规范的音乐。乐乃人之真情之自然发抒,有和同的作用,但也有放纵情感的倾向,从而发生悖离,最终消解了“和同”;而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却可以制约“乐”之放纵情感的倾向,使之合于“度”,而发挥乐“合同”作用,从而使得“反人道之正”。所以,重视礼之节制则成为必然,而“知乐则几于礼矣”[1],这种礼乐一体的观念,则是对于礼乐相反相成作用的深刻认识。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礼乐的作用,达到大治大化,“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1]可见,《乐记》着重探讨如何以“礼”防止“人化物”之发生,保持“人道之正”,以达于大治大化。
当然,仅仅有礼乐还是不够的,为保障礼乐之施行,还必须有强力支持。《乐记》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礼乐刑政之并用,能够保持长治久安。基于这样的思想,《乐记》“人化物”的命题,其伦理和政治的意义就比较突出。
虽然在《乐记》中,“人化物”所关注的是以礼来节制人的欲望,是从礼乐的相反相成来立论的,但这一命题却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人化物”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人与物发生联系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在“天人合一”、前“互主体性”的观念下来论述“物——人”关系的。因此,“人化物”命题之提出、礼乐之相反相成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辩证法这一名称源自西方,但这一思维理论在东西方是现实存在,而且中国的辩证法思想出现更早。高清海为金景芳先生《〈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一书所作的《序》称:
“辩证法”作为人类的哲学思想理论,反映的是事物内在的发展本性,表现的则是对待事物的属人价值态度。……科学的规律属于事物的自在客观本性,辩证法的规律虽然也根源于事物的本性,但它同人的认识和活动的实践本性又是密切相关的。所说“普遍”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含义,就其实质来说乃指“贯穿、沟通、融会、结合”的意思,并非指自然、社会、思维共性的简单抽象。因为人性与物性不同,所以才需要理论去沟通,以便在人的实践行为中达到二者的一致和融合,即所谓“弥纶天地之道”。这是人的行为宗旨,同时也是辩证法理论的根本意义……
所以“辩证法”问题主要不是个科学知识问题,而是一种理论思想问题,有无辩证法不在于辩证法的名称,应该主要看人如何对待自己和世界的思想关系和行为态度。辩证法可以说本质上是人作为“人”自觉了的本能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着人已意识到自己为人,并试图要用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对待世界,开始追求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之时,不论东方或西方,都会产生出辩证法理论来。[2]
应该说,这一认识能够探源抉本,把握了辩证法这一哲学范畴的本质,是深刻、通脱、全面的。“辩证法表达的是人性与物性在相互作用中深层的对立统一关系”[2],在这一关系中,探讨人与物之间的贯穿、沟通、融会、结合,是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探索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金景芳先生论定,《周易》乃公元前十一世纪时周文王所作,“《周易》一书是用辩证法的理论写成的,它所体现的是事物深层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本性;《易》与天地准,讲三才,讲天地人,实际目的在人身上。”[2]作为中国思想的源头,《周易》对后世哲学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以文化传承者自居,整理文献,传承文化,厥功甚伟。儒家服膺文王、周公,赞赏“郁郁乎文哉”之大周,对创自周文王之《周易》多有青睐,创有“十翼”以作说解,故尔受《周易》所蕴含的丰富辩证法思想之潜移默化影响极深。儒学先师孔子亦学《周易》,有韦编三绝之传说,《论语》有孔子“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之喟叹,《史记·孔子世家》亦有“孔子晚而喜《易》”之记载,故尔冯友兰说:“孔丘是学过《周易》,不过他学《周易》,不仅学占筮的方法,而且要对于卦词、爻辞有所引申,有所发挥,有所理解,有所体会。这是他在学《易》中学而兼思的收获。”[3]那么,这种“学而兼思”,融会贯通了《周易》深刻的思想的。也就是说,《周易》之辩证法思想应该是渗透于儒学思想之中,而且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易》之强调统一而不强调对立,亦深深地影响了儒学思想。集先秦以来儒家礼乐思想之大成的《礼记》,也承袭了儒学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在建构上层建筑的同时,注意于对立统一,强调统一而非对立,因此《乐记》论述礼之“别异”和乐之“合同”,在对立统一中,注重统一,强调其相反相成。正因为如此,本文对“人化物”命题之说解、阐释,有其内在合理性,而非强作解人。
如上文所述,“人化物”在《乐记》中的意蕴乃人的心志受外物诱使,随物变化,而有“善”“恶”两种欲念,因此,为使得保其“天性”而不“灭天理而穷人欲”,则要节制欲念,不使其向极端发展。而保“天性”之关键在于“反躬”——即内省其心,以良知节制其冲动。更为重要的是,《乐记》认识到,无论是“善”抑或“恶”之欲念都会诱使人走向极端,而走向极端的欲念则会有贪得无厌的需求,最终为外物所役使、所控制,从而使人灭其“天理”、伤其“天性”——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溺于“物”而为“物”所拘滞,从而丧失了人之“自觉”与“自由”,人不得为人,人与其本质相疏离。可见,这一命题辩证法思想的丰富性。
而孔颖达的解释却恰恰抽去了其“合理内核”。孔颖达认为“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如此则应该规避“恶”物,使人接触“善”物,潜移默化,从而形成人的自觉的善良品性以及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那么,孔氏所说的“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欲也”,仅仅指的是“恶”物对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已。从教化目的而言,孔氏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不过,孔颖达这样的理解,虽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比较机械,偏执一隅,而缺乏辩证法的思想。孔颖达没有认识到,物与人皆处于一个“互主体”的和谐世界中,对物之欲求一旦不可控制,则会破坏这一“互主体”的和谐关系,走向人的对立面。就其根本而言,欲念无论“善”“恶”、物无论“善”“恶”,都会诱使人,发展至极端则人受物欲的支配,物最终成为人的对立面,人最终亦会疏离其本质而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成为异己化的力量——人为物所役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化物”的命题蕴含了“异化”的辩证思想,所论诚乃“人生至道也”。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探讨了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异化有“自我异化”和“物的异化”[4],所谓自我异化指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疏远;物的异化则指劳动所创造的物成为劳动者的对立面,役使、控制了劳动者。异化劳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4]
“物的异化”导致了“自我异化”。马克思在此论述的不是自然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人之存在的本体论,已经彻底超越了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体对立模式,在“人—物”的互主体结构中来论述人与物(世界)的关系。认为人与物应和谐共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一旦人将物作为彻底征服、改造的对象,物则处于人的的对立面,成为役使、控制人的异己力量,而且最终人违离其本身。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广泛而深刻的。所谓异化则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包括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性的思想文化活动,同人自身相违离,成为人的对立面、异己力量,从而形成控制、统治、残害人的这种关系。而劳动异化是产生其他异化的根本原因。那么,《乐记》“人化物”所讲述的正是人与自然界(外物)相处过程中,由于人为其贪欲所支配,力图全面支配、控制外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为外物所役使,从而使人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即人外化为物,与人自身相对立,成为人之类本质的对立面,也就是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相疏远。立足于“天人合一”观念的中国传统思想,注重人与物的和谐共处,人与物的平等地位,比较接近于近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互主体”思想,可以称之为“前互主体性”,《乐记》“人化物”命题所揭示的就是对“万物一体”和谐关系、和谐世界破坏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化物”与“异化”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当然,马克思异化命题是深刻的,是从“异化劳动”这一生产关系之根本入手,以探讨“异化”问题。“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4]从而昭示了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疏离这一深刻认识。而“人化物”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探讨,着眼于人的主观欲求与客观外物的关系,未能从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生产活动这一根本入手,故尔认知是比较浮浅的。但“人化物”毕竟认识到了“人”(主体)与“物”(客体)的关系,要求正确处理,以保持“人”之本性——人之所以为人,不要为“物”所役使,使“人”与“物”永远处于互惠互利的和谐世界中,是其深刻之处。
要之,“人化物”的合理内核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蕴含有“异化”的思想,启示人应该葆有其自身的“自觉”与“自由”,是其丰富深刻处,但是,毕竟与“异化”立足点不同,不可等量齐观。但发掘“人化物”等这一类元命题的深刻意蕴,以马克思主义、近现代哲学来分析、探讨,古为今用,融古今于一体,促进思想的活跃,充实丰富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参考文献】
[1]孔颖达.礼记正义·乐记[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3]金景芳.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M]. 沈阳: 辽海出版社,1998.
[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5]胡乔木.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雷恩海,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