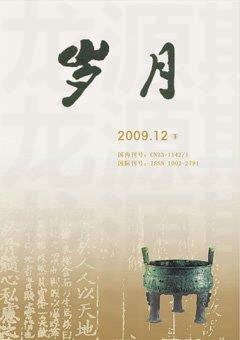颂诗读书 知人论世
何 荣
唐宪宗元和时期是唐王朝的中兴期,而所谓中兴,非仅指其政治与经济而言,亦指其文学创作。白居易在其《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提及宪宗元和诗坛云:“诗到元和体变新”[1],正是指出了是时诗坛的变化。而白氏所谓的“体变新”正是其本人与挚友元稹等人共同努力倡导之结果。元、白诗歌创作重写实、尚通俗,清人赵翼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2]。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3]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他们都对白诗之特点予以中肯评价,指出其诗歌创作“尚实”、“浅易”之特点。白氏著有《白氏长庆集》,现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值得注意之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及其对通俗性、写实性创作的突出强调与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白诗于唐代诗坛之特殊地位及其诗歌之特点,历来研究白诗之人为数众多,研究成果中亦不乏优秀之作。但不可否认,成就虽有,却不免宥于一隅,少有突破与创新之见解。今得蹇长春老师《白居易论稿》一书,如卞孝萱先生为其作书序中所言,此书乃是蹇老师“以数十年的精力,专心致志于白居易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今自选二十余篇,编成一集”[4]而得之,故此书为蹇老师数十载之研究成果,乃其心血之作。捧书细读,于书中对于白居易之研究成果慎思之,其中不乏精细独道的见解,使人大悟,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白居易论稿》一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白之生平与思想,其中包括对白氏之生平、思想以及其创作道路的论述、探讨了白居易思想之分界、白居易的江州之贬与王涯的落井下石、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以及《三教论衡》简析。中篇乃对于白之诗论与创作之研究,其中对于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及其诗歌创作有诸多论述,就其篇章而言有: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白居易讽谕诗的人生道理、《长恨歌》主题平议、以声写情的千古绝唱《琵琶行》、试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白居易诗论的美学意义及从“有所作而为”的主张到“为人生的艺术观”。下篇则是白集杂论,此部分论述内容乃是独立于白诗创作之外的白文创作,其中论及了历来研究白氏不被重视之内容,为历来研究之薄弱之处。其研究有:《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关于《白氏六帖事类集》、从《不致仕》看白居易的廉退思想、白居易《失婢》诗考辨及也说“青衫”与“江州司马”。本书三篇内容虽为各自独立之部分,但实为有机整体,环环相扣,互为表里。其中以上篇白居易之生平与思想为全书之主导,中、下篇的论述乃是在此篇基础上得以展开。
蹇老师之《白居易论稿》在研究白氏著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人物与时代紧密结合,力求做到“知人论世”,将人物的思想与活动放置
于历史的原点当中加以考察。
对于文学的创作主体而言,时代之安宁与纷扰、国家之繁盛与衰歇、个人之荣辱与浮沉,自然感之于心,形之于文。于其文便可见出其人之情,缘其情便可寻求其生活遭际,进而窥及色彩斑斓之社会一角。故而研究文学,不可限于文学本身,而应将其视野扩大到诸多领域,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社会大文化背景中诠释文学之真谛。此乃蹇老师于本书之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于书中不乏其例。如论及白之生平、思想以及其创作道路时,著者将白氏之创作与其生平、思想紧密结合,提出白氏倡导之“为民”而作之诗歌理论,乃其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之“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这一论点。又如其在论及白居易对于三教持调和平衡的中庸主义立场时,著者以人为历史之人、社会之人为研究出发点,认为白氏之所以持中庸主义立场,除了与其个人遭际相关联的主观因素之外,还应认识到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再如论及白居易的江州之贬与王涯的落井下石时,著者提出全新见解,认为分析此原因不仅仅要从王涯的性格和人品的层面去探究缘由,更应联系到王涯同永贞内禅的密切关系,从而结合元和初期新旧两派势力尖锐对立的错综复杂之政局中去深入探讨。任何一场革命与革新之于研究,都应立足于文学、历史、政治三个基本层面之综合研究。而对于唐代永贞革新之研究,学术界历来仅是顾其一而忘其余,迄今尚乏立足于文学而将三者加以有机整合之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之《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从揭示唐代宫廷斗争之秘出发,从而澄清唐代顺宗、宪宗时的一些历史悬案。著者于书中利用陈先生之研究成果,将宪宗之立与阉寺之扶持紧密结合,从而联系白之被贬江州与王涯之落井下石,历来牵绊学术研究之问题迎刃而解。由此,著者提出了古代文史研究中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之课题——如何结合时代背景,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古代作家的心路历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作品和思想文化遗产,力求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歪曲和误解。
二、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为出发点,将白居易之思想与其诗论、创作紧密
结合,以顾全人、顾全篇为精神要旨,
以此来探讨白之创作。
陈寅恪先生之《元白诗笺证稿》是其以诗文证史的代表著作。著者于陈先生之研究方法获得非常启示,而此便是于本书之中,值得注意之一大特点。著者于此书中始终不遗余力地学习陈寅恪先生之学术研究观点,形成其“以史征诗”之研究方法,实为陈寅恪先生之思维逆向运用。论文学须有史之佐证,只有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方可真正做到不为凿空蹈虚之论。著者在研究白氏诗论与创作时,大量援引历史文献,力求从第一手文献着手,还原诗人之历史原貌,突破前人研究之局限从而获取全新研究成果。如书中将白氏之对于永贞革新之态度与其大力倡导之新乐府运动紧密结合,于此著者援引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成果,认为白氏之所以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与其所处时代密不可分。从而指出时代特征导致白氏思想特征之形成,进而形成白氏诗歌理论。白氏在其《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其作诗标准:“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4],其目的即在于起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讽谕效果,并希望得以“泄导人情”。
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
我国历来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评都建立于单一主题说之桎梏中,从而导致对作品不同程度地误解与歪曲。在《白居易论稿》一书中,不难看出著者对于陈寅恪先生以史为据之研究要旨的学习与贯彻,但其亦不囿于陈先生之研究成果。其《<长恨歌>主题平议》一文中,著者既不局限于前人言论亦不限于一家之言,对《长恨歌》主题说提出质疑,建立新观点。应当指出,著者于此所提出的新观点并非虚妄之说,而是有正确之文艺观指导。书中,著者援引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一文中对于主题概念的界定,从而大胆提出打破单一主题说之桎梏,建立分层次的多重主题统一并存体系。在此基础上,著者指出历来探讨《长恨歌》之所以有多种理解原因,指出了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之局限这一问题,从而使得对于《长恨歌》的研究取得又一新进展。由其文之探讨研究亦可指出,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仅可以用于像《长恨歌》这样题材特殊、表现手法独特、创作主体思想矛盾这类作品之解读,亦可用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品评与理解。
四、大胆假设、守正出新
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诗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生,庐山之欣赏角度不同,其风貌自然又别具一格,而如若跳于庐山之外,其欣赏会更接近真实与完整。山水揽胜,可随视角变化而赏玩殊异之景象,而这于我们研究文学,亦是一不可或缺之方法。本书在研究白氏著作中便敢于跳出前人窠臼,提出不少大胆假设。在此需指出一点,即著者所提之假设亦是建立于大量历史材料的筛选基础之上。以丰富的史实考订和细致的文本分析为研究基础,故而著者时有所获,或得前人所未言,或秉承前人略言而后细入之,或据前人之言论而予以辩证。如著者在《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一文中,不仅继承了陈寅恪先生之观点,亦于文中加以大胆假设,即将《为人上宰相书》中“主上践祚未及十日而宠命加于相公者,惜国家之时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献于执事者,惜相公之时也。”著者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记载中援引大量历史文献,提出假设即将白文中“践祚”一词不仅仅理解为“登基”之意,而应按历史事实将其理解为“临朝视事”,由此历来研究停滞不前之问题得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蹇长春老师之《白居易论稿》一书之精细独创之处,亦可看到他在学术研究中所一再秉持之精神。其研究方法、态度及精神值得广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学习。
诚然,此书中亦有不足之处,如其《从“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到“为人生的艺术观”——白居易诗论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著者虽指出两者之关系,提及白居易诗论中的“为民”、“为事”的“有为而作”。但是对于现代文坛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的论述却很少,二者的联系与对比不够鲜明。再者,本书下篇白集杂论中,著者有《<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兼论白居易早期思想》一文及《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一文,二文都提及到判词写作在唐代科举考试中之重要性。而前者论及白氏在其前期文学创作中重视判词创作,实为寄希望与科举考试,以便进入仕途,从而兼论白氏早期之思想。由此可见,后者对于唐人于判词的重视之论述实为前者之基础,二者实可合为一篇,不宜于一本书中反复论说。
【参考文献】
[1]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赵翼著,胡主佑,霍松林校注.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蹇长春.白居易论稿 [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何荣,文学硕士,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