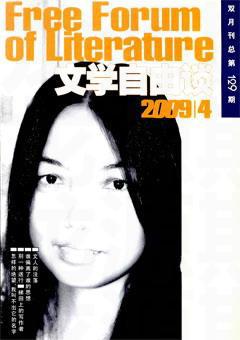忆方平先生的“愤怒”
仵从巨
2008年确是事多。不说搅动了国家的那几件大事,仅是在上海文化界,王元化、贾植芳、谢晋、方平这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先后谢世,也令人有伤怀、怅然的感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大约已属绝版了。若再望远一点,境外仙逝者亦有法国“新小说”主将罗伯-格里耶、俄罗斯与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与哈罗德·品特,以及因“文明冲突论”搅动了东西方思想界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是在“平安夜”西行的。
杰出、优秀的人物离去是时代与人类的损失与痛,而我所以有特别的触动并想写几句话,是因了莎士比亚专家、翻译家方平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上海师大度过了近两年的学习生活。上海师大中文系对我们这些来自全国高校的外国文学助教们,确是用了不少心力。主要操持此事的王秋荣先生、杨国华先生不仅动员了中文系最优秀的老师登台授课,而且还聘请了文学研究所的朱雯、朱乃长等著名学者。此外,他们还尽可能利用上海滩“藏龙卧虎”之优势,从校外请了一批学者、理论家、翻译家、批评家为我们授课或作专题报告(其中也有不少出入沪上的中外学者)。这其中包括草婴、李欧梵(芝大)、福斯特(美国)、包文棣、关口安义(日本)、王道乾、陈伯海、王纪人、任仲伦、余匡复、钱春绮、王忠祥、王智量、郑克鲁等。如果说我们后来多少有些进步、发展,实在都与上海师大与这些老师们有关。
所以特别记得方平先生,是因为他为我们授课较多。在桂林路上的上海师大、在华山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101室)等处,方平先生多次为我们讲莎士比亚,自然也少不了讲他钟情也深解的《十日谈》。在谈及《十日谈》在中国命运坎坷、屡屡遭禁、遭删时,方平先生动了感情。他谈到:关于《十日谈》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出全本还是出选本,曾请示中宣部,负责人同意出,但只能出选本,怕全本“贻误青年”。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序言”还提了一个意见:已删去的故事在“序言”中不应出现,所以“序言”中也删去了关于第三天第十个故事的评述内容。对此,方平有保留意见。“对《十日谈》,我相信,我比中央领导同志高明。”讲台上的方平渐渐激动起来,“有领导人说,‘《十日谈》不是一本好书,我说,‘搞政治,我不懂;搞《十日谈》,你不懂!”清晰记得,方平先生此言一出,教室内一片寂然,但每个人心鼓咚咚,都忽然蒸腾起对一位刚直的读书人、学者、知识分子的一片敬意。文人之言、布衣之怒,虽似惟此而已,但其精神之感召与思想之影响,却在下一代人心中留存,不然,24年之后我何故有话成文——那是1985年10月11日的上午。
虽然如今我已是老教师甚至资深老教师了,但曾经做过十几年学生,深知一位老师在学生心中留下长久以至不灭印象的,甚至主要不是学问,而是思想与人格。方平先生的莎士比亚论我确已记忆模糊了,但24年前的那一刻、那几句话、那“愤怒”的形象却刻在我心中。此后,每当我在讲台上讲薄伽丘的《十日谈》时,一定要讲方平,一定要谈他著名的“序言”——《幸福在人间》,一定要谈这位气质儒雅、谈吐谦和的学者鲜见的“1985年10月11日的愤怒”。
后来还与方平先生有过一次信交:我受某杂志之邀,并以“特约编辑”的名义,向外国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约散文稿,此事得到了卞之琳、贺祥麟、柳呜九、郑克鲁等先生的呼应与支持,内心也一直深怀感激。我也向心仪的方平先生约稿,不想其时他还在病中,但仍抱病作复并致“歉意”—那工整、秀雅的字和字后严谨、认真的人都使我迄今难以忘怀。
人有终老,乃天律。对优秀杰出的人物,我们庸常者总诚挚由衷地希望他们长寿。但天律难违,人有竞时。如今方平先生走了。可我挂怀他的“愤怒”,以为今日仍可惊听回视,因为人文知识分子之节义由此“愤怒”可一叶知著。
当追念方平先生的“愤怒”时,张目环视,只见千士之诺诺,曲学阿世作小伏低自荐枕席者众,鲜见一士之谔谔,士之病乎世之病乎,拟或二者皆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