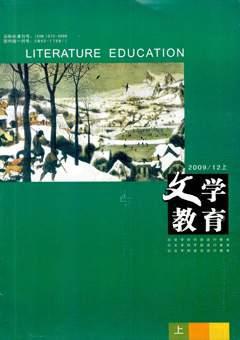略论《麦芽糖》中的乡村女性
如果我们对现代中国的乡土题材小说谱系进行简要的梳理,把自鲁迅肇始,许钦文、鲁彦、蹇先艾等参与的“只揭病苦,不开药方”第一代乡土题材小说称为启蒙形态的乡土小说,命赵树理为代表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村小说为革命形态乡土小说,把沈从文代表的游离于政治边缘的乡土小说称之为浪漫形态的乡土小说,称刘绍堂笔下的乡土小说为古典形态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湖北作家晓苏的乡土题材小说集《麦芽糖》冠名为“新乡土”小说。之所以这样称谓,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以自己独特的叙述形式,写出了他独特的乡村情、乡土味和乡土情怀。而其小说中塑造的“乡村女性”形象则丰富了晓苏的乡村情怀。
一.乡村女性折射出晓苏的乡村情怀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以他独特的小说内行式写出了农村的乡土事、乡土味和乡土情。《麦芽糖》正是这样的代表作,评论家李遇春说:“晓苏的《麦芽糖》讲述着油菜坡的故事,讲述着油菜坡的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晓苏把他对故乡的深情,都凝结在关于油菜坡的底层叙事艺术追求中了。”①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晓苏对故乡的底层叙事中,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生活在油菜坡里的一群乡村女性。在她们中,有勤劳孝顺的甘草,有善良而富有爱心的帅珍,有无私心疼孙子的土妈,有纯洁而美丽的“姐姐”胡秀,有执拗而能干的“姨妹”胡霜,有贤惠大度的西红柿,有内外兼美的徐瓜,有开放泼辣的麦嫂,等等。从这些性格各异的乡村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晓苏对她们的深情,可以看出晓苏寄寓其中的乡村情怀。
其一,晓苏一一将西红柿、 甘草、豌豆、胡霜、徐瓜、麦嫂、唐水、土妈等称谓赋予给他笔下的乡村女性。当这些典型的、与乡村人生活紧密联系的瓜果菜蔬等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称谓时,文章的乡土气息自然就弥漫开来了。而我们也会被作者对故土,对乡村的深情所打动,被小说浓郁的乡土味所感染。例如甘草,她自己这样介绍自己名字的来历:“爹特别爱嚼甘草,每次抓药回来总要从药袋里找一片甘草塞进嘴里,嚼得腮帮子鼓起来,嘴角往上翘,像吃鸦片。”这种生活场景显然是属于乡村的,所以也极富乡村韵味。对土妈的叙述,则能把晓苏对乡土的热爱和挚恋挥洒得淋漓尽致:“土妈刚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命中缺土,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土。还是娃娃时,人们都叫她土丫。当姑娘的年代,人们又叫她土姑;结婚生孩子了,人们就叫她土婶;后来老了,油菜坡人都叫她土妈了。怎么说呢?土妈真是土了一辈子。”“土妈喜欢住在老家这个土屋里,地是土垫的,墙是土打的,砖是土烧的。土妈说,她这一辈子是一刻也离不开土了。”土妈还把她对孙子的厚爱寄予在她自己通过汗水辛苦载种的土黄瓜中。与其说这些都是土妈自己的乡土情结,还不如说是晓苏本人浓厚的乡土情怀的体现,是晓苏对故土、对油菜坡、对乡村深切的念念不忘。对豌豆,虽然只是三言两语:“豌豆不是吃的那种豆子,她是杨聪表弟的媳妇。”但是荡漾在文字中的乡土气息依稀可闻。
其二,这群女性是晓苏心中传统乡村精神的象征。对于故乡,对于油菜坡,晓苏是充满了深情的,尽管这种感情中,有对故乡人苦难生活的同情,也有另外一种情形,正如李遇春所说:“晓苏对油菜坡充满了原乡人般的挚爱,但这种挚爱并不能阻止他从理性上对油菜坡底层民众做精神上的批判性审视。”②晓苏对油菜坡底层民众所要作的批判性审视,也就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为标志的“后改革”时代的到来,农村所呈现的从物质到精神的荒漠化景象。《侄儿请客》中有这样场景:在油菜坡,一辆小车翻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司机央求众人帮忙把车子给他抬出来,并且提出要给每人发一包烟以表谢意。众人却说不要烟,只要钱。而且提出钱不能太少。这种景象使得“我”的心像是被狗子咬了一口。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油菜坡的乡亲总是无私的去帮助不认识的人们。晓苏借助“我”的口,痛心疾首于油菜坡民风的衰落:“我简直怀疑他们是油菜坡的后代,他们真是把油菜坡的脸丢尽了。”
在《农家饭》中,晓苏又借助于我的“口”,痛心于人们的“见利忘义”:“我不想把每一个人都看透,我还是希望保留一些美好的东西,哪怕这些美好的东西仅仅只有一层美好的外表,里面都是丑恶,那我也不愿意将这层美好的外衣撕破。因为我们还要活着,如果把每一个人都看透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
如果说,乡村原有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意境在“后改革”时代逐渐淡化,原生态般的淳朴善良,重义轻利的乡村精神也在逐渐荒芜,那么,这一切恰恰又是晓苏的忧思所在。换言之,晓苏所念念不忘的,倒是故乡油菜坡原有的真实美好的淳朴温情。正如《侄儿请客》中所描述的那样的画面:“我陡然想到我年轻时候的一件事情,一天,一架外地马车从我们村门口经过,一不小心陷进了一个泥坑,乡亲们看见后马上跑上去帮忙推车,泥巴溅了乡亲们一身一脸,乡亲们却半句怨言也没有。”
无独有偶,活跃在晓苏笔下的这群乡村女性却是淳朴善良,有情有义地活跃在新世纪巨变中的乡村。对待自己的亲人,她们孝顺关心。如《甘草》中的甘草,每天起早贪黑卖菜,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可是当爹一有了困难,身心蒙受伤痛之时,立即放下手头上的一切,毫无怨言的去照料抚慰爹,成为爹的“顶梁柱”。对待帮助过自己的人,她们以礼相待,决不让别人吃亏,如《麦子黄了》中的徐瓜,在丈夫姬得宝得了“癌症”后,独自操持着家里里里外外,一个弱小女子,割麦子,捆麦子。当怀着各种目的的男人自发来给她帮忙时,她坚决不听信丈夫的话去利用别人,反而好酒好肉招待人家,还要给人家工钱。对于和自己无关的人,充满爱心和关怀,如《油渣飘香》中的“干妈”帅珍,因为心疼“我”吃不到猪油渣,并且挨了爹妈的责打时,在自己家庭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冒着被丈夫拳打脚踢的风险把家里最后一块猪油炼了油渣给“我”吃;《我们应该感谢谁》中的“钱春早老婆”,长期照料和她毫无关系的“我父亲”,弄得双手都冻破了,却没有一丝的怨言;甚至《坦白书》中的唐水,拒绝油菜坡有钱有势之人的诱惑,而对勤劳善良的光棍汉给予性关怀。甚至对于伤害自己的人,她们也待之以善心和好意,如《前夫开着轿车来》中的西红柿,被前夫无情抛弃后,却依然能在他“人困马乏”之时,为他倒茶端饭;还有《侄儿请客》中笔墨甚少的“表妹”,面对多年前背叛自己的“表哥”,也是不计前嫌,以温情和关怀待之。
对于这样一群有情有义的乡村女性,晓苏显然是倾注了肯定,乃至深情。比如甘草爹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感叹:“我想嚼一片甘草!”我们不能否认这是干草爹在近乎陷入绝境时对甘草的念念不忘,但它又何尝没有倾注晓苏对甘草的肯定呢?前夫“胡萝卜”在受到西红柿善待后,发自肺腑的赞美西红柿漂亮、贤惠、能干,这是不是也可以说倾注了晓苏本人对这位农村女性的赞许之情呢?那位内外兼美的徐瓜,晓苏借助了虚实相生的写法来美化其形象;“她穿着一件红背心,披着黑头发,睁着亮亮的眼睛望着我,像是一个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虽然睁着眼,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梦。这天晚上的月亮真的很好,麦草跺在明亮的月光下金光闪闪,就像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的景物。”这样虚虚实实的意境,显然是晓苏有意在升华徐瓜的形象,当然也带着晓苏对这个人物的深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精神家园的荒芜,重利轻义逐渐蔓延着曾经温馨的油菜坡,另一方面,是这群不为人所关注的乡村女性的淳朴善良,以她们的真性情演绎着温暖人心的故事;一方面,是晓苏对油菜坡精神荒漠化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是他对这群重情重义的乡村女性倾注肯定之情,甚至深情。这种截然相反的对比,应该说不会是偶然。恰恰相反,它似乎是晓苏有意在呼唤着、渴望着传统的乡村精神。换言之,是这群乡村女性,寄托和象征了晓苏心中永不失落的传统乡村精神,这正如李遇春所说:“晓苏似乎习惯了用黑色的眼睛看生活,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此责备作者心理的阴暗,我相信他的心中一样渴望光明。”③显然,这群女性可以算作是他心中的“光明”了。
二.乡村女性的不幸命运丰富了晓苏的苦难叙述
在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中,对女性的关注似乎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乡村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不仅承受着生存的压力,还承载着数千年来所形成的男权文化所赋予她们的某种道德文化和社会内容,她们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在《麦芽糖》中,苦难叙述可谓是全书的一个重点。用评论家李遇春的话说就是:晓苏书写油菜坡人们的悲喜歌哭,解密他们的心里波澜,直陈底层的苦难。需要注意的是,这群有着人性美人情美的乡村女性,她们的命运,却不如她们的形象那样美好了,其中有很多人却是一生坎坷曲折,她们的悲喜歌哭,同样被晓苏深深地看在眼里,成为他的底层叙事的另一个亮点。这些女性,她们有的遭受男方的抛弃,如《前夫开着轿车来》中的西红柿和《怀旧之旅》中的一直未出场的“田小苗”;有的被贫穷的生活摧残掉,如《寡妇年》中的“姐姐”胡秀;有的遭受丈夫或者儿孙的冷落甚至欺侮,如《油渣飘香》中的“帅珍”和《土妈的黄瓜》中的土妈;有的则是忍受精神上的苦闷,如《寡妇年》中的董玉芹和罗高枝。若仔细挖掘出这些女性的生存境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也应算作是晓苏的苦难叙述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一,以女性被抛弃的命运反思农村每况愈下的世风。《麦芽糖》中,女性遭受抛弃的命运似乎是晓苏隐隐关注的重点,在《侄儿请客》中,“我”进城后不久,就对青梅竹马的“表妹”变了心;《前夫开着轿车来》中,丈夫进城致富后,不久就抛弃了曾经同甘共苦的妻子“西红柿”;《怀旧之旅》中从头至终都没露面的田小苗,也是被初恋情人雷总抛弃,一直过着不尽人意的日子。
其二,对乡村女性精神苦闷的关注和人性关怀。在晓苏笔下,性的苦闷是他苦难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大多数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以男性的视角来叙述的。《寡妇年》则是以女性的心理视角来叙写这一点的,其中的女主人公董玉芹和罗高枝,一个是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很久都不归家;一个是死了男人,公公又不让带走小孙子,所以一直也就没有改嫁。两个女人因为精神上的苦闷,不得已一个有了婚外恋,一个和公公偷情,最后的结局是死的死,残的残。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性”对于女性来说,它的意义不再单一的意味着传宗接代,而是精神享受和愉悦。对于这一点,作者给予了难得的人性关怀:一方面,作者赋予了“我”对这几个孤单女性作“性的救助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我”对她们的救助失败并且她们自救也失败后,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借助“我”的口这样说道:“我发现我已经无法忘记那几个不幸的女性,并且非常非常地想念她们。”《麦芽糖》中这种对乡村女性的“性苦闷”的关注,虽然在篇幅上没有占很大的份量,但是,无论如何,它大大丰富了晓苏所要突出的“苦难叙述”。
其三,对农村女性在丈夫或者儿孙的冷落下的生存境遇的忧思。在《麦芽糖》中,关注农村老年女性的生存境遇的主要有两篇:《土妈的土黄瓜》和《油渣飘香》。土妈和“干妈”帅珍均是勤劳善良的母亲,前者为了使孙子能吃上自己种的土黄瓜,费尽万般辛苦。结果却是自己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儿子,儿媳的冷落乃至嘲笑。后者则以自己的辛劳支撑着整个家,却遭受丈夫和儿子的双重折磨,“虽然才五十出头,但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头发全部花白,脸上瘦得皮包骨。”如果说土妈遭受的是精神创伤,那么,帅珍则遭受的则是来自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折磨。对于她们的这种生存境遇,我想晓苏还是浸润了深深的同情的。在《油渣飘香》中,晓苏给遭受生活磨难的帅珍安排了“救助者”姚学本,是他,给予了干妈从精神到物质上的无限安慰,让干妈还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在《土妈的土黄瓜》中,晓苏有意让土妈没有看到被孙子扔掉的土黄瓜被叫花子捡跑了这多少有些残酷的一幕,反而让其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土妈对剃头铺老板说,我孙子总算吃到奶奶亲手种的土黄瓜了!土妈这么说着,脸上就露出了一层淡淡的笑意。”其实,这种安排也可看作是对土妈的精神安慰,在经受了儿子和儿媳的再三打击后。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晓苏的良苦用心:对这两位在精神或者物质上遭受苦难的乡村女性的忧思和同情。而这,恰恰又是晓苏的苦难叙述所在。
诚然,晓苏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还有更多的光彩有待我们去挖掘,晓苏的乡村情怀也应当有更多角度的体现。但是,有一点确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乡村女性形象从一个独特的层面折射出了晓苏的乡村情怀,她们以自身的人性魅力构筑了晓苏心中传统的乡村。
注释:
①李遇春:《麦芽糖·序》,载《麦芽糖》,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1页。
②李遇春:《麦芽糖·序》,载《麦芽糖》,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5页。
③李遇春:《麦芽糖·序》,载《麦芽糖》,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第5页。
张向辉,女,湖北黄冈人,新疆师范大学文艺学2007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