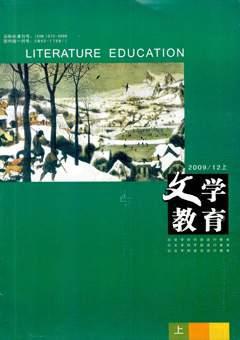雪泥鸿爪 人生况味
读谢伦的散文,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好说得清楚,如果你试图说出点什么来,则难以捕捉想说的东西。这种散文,跟许多流行的一本正经的散文很不一样。
你就看这两个短小的篇什吧,它写了什么呢?琐琐细细,娓娓而谈,没有中心,笔触游移,飘动,散漫,随意。第一篇《这边那边》,写一路回乡上坟的过程,先写朋友送“我”到吴店镇后那些絮絮的话,写家乡清明节上坟的规矩,再写天气,去年的和今年的天气之不同,由天气再说到身上的衣服,以及妻子给“我”加衣,再说吴店镇上的热闹,关于冥钱的时代变迁,再写山坡上的野花,写坟上挂的“花”,于是上坟,回家。——完了。这么琐碎散漫,然而它始终吸引着人,饱含着生活的真切滋味,淡而不薄,散而不杂,实而不滞,一如生活本身的模样。你觉得有味,但绝不轻松,你一定会感觉到什么,有点沉重?不太像,因为作者的笔端流露着大自然的明丽与人间的温情;那么,奇妙就在这里了,正象植物的养分渗透在植株茎叶中一样,这一点并不轻松的滋味就在这明丽与温情之中流淌。看看最后这段关于坟上假花的话吧:“这样也好,热闹些,好看些,益于视觉的愉悦,以免给自己留下过多伤感的机会。——毕竟,活着的人也都活得孤独沉重不容易,不在外在的形式上寄托一下,冲淡一下,麻木一下,一旦勾起早已深埋的凝血亲情,怕是支撑不住。”作者的心绪在这里一下子显豁了,原来,前面那些絮絮的叙说,都像源泉一样是这种心绪的来路呢。心绪,或者心情,现在叫心态,这样的叫法不知道是否科学含量更高些。那么,这篇作品就是写心态了。散文不写宏大,不写深刻,单写一点点心态,这样行吗?
这种写法的特别在它融化了主题,取消了鲜明,抛弃了强烈,也不要集中。这有点像写中国的传统的诗,这散文就有点古诗的味了。杨朔说过他是把散文当诗来写的,然而他的散文还是有“集中”的感觉和鲜明的“主题”。谢伦不是这样的。如果打个比喻,谢伦的散文有点像李商隐的无题诗——不过,李商隐太秾艳了,而谢伦是淡的,也不那么诡异。
《桃之夭夭》似乎有所变化,由于写的是桃花和美丽的女人,题材的关系,色彩就比前一篇浓烈了许多,近乎李商隐了。不过,整体的调子仍然保持着淡淡的忧伤与隐隐的哀愁,仍然在结撰上保持着散漫随意的风格。这一篇写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具体的故事,既不曲折,也不离奇。对于故事本身,作者也写得轻淡。作者所着力的,仍然是情绪,是心态。这从起笔上可以看得清楚。起笔有两大段,远远离开了故事,纯属闲笔,作者不急不躁,不写故事发生地周家湾,而写镇上;不写故事主人,而写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写与故事有关的人事,而写吃饭,写下岗,其间甚至由午饭的菜肴引出木心的话,再引出晋人张翰的“莼鲈之思”,感叹一番再写回来,写下岗引出的后果——今年不给父亲立碑了。第二段写午饭后“坐在小院儿里晒太阳,喝茶,说往事”,也是散散淡淡,发着人生的感叹。最后,话题才渐渐说到故事发生地周家湾。这些散淡的文字,流动着一种意绪,一种心态,透露着人生的淡淡况味。对于故事本身作者也写得少,重在氛围的铺叙上,写女知青老师的美丽,写她对学生的“我”的影响,把气氛,把桃园,把美艳的桃花,写得唯美极了。至于女知青老师的悲剧,只从侧面交代。通篇观之,前面人生况味的铺叙正好暗合着后面的人物故事,在时光流逝的伤感之中,浮现着凄美的回忆的轮廓。读者被感动着,既因为那故事,也由于那满纸的情绪。但是,如果单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而已。
小说家的散文展开故事,散文家的散文淡化故事。散文家的兴趣和本领,在于展开内心深处的意绪,表达人生的复杂况味——却能把它写得单纯明澈,一如春梦。
回到前面:这种写法行吗?其实以散文写心绪正是五四时期散文家们的特长,无论是郁达夫,朱自清,丽尼,还是庐隐女士,都是擅长此道的。更不用说鲁迅的《野草》,如《秋夜》《好的故事》《雪》等等。奇怪的是五四之后,这个传统渐渐消隐,读到谢伦这样的散文反而转成新鲜了。
席星荃,散文家,现居湖北襄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