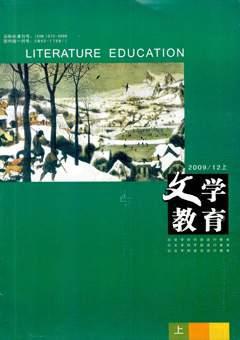白描背后的黑色幽默
这是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时代。置身都市的现代人在现代格式化生活中幡然醒悟,他们把眼光投向民间,投向野地,投向所谓的原生态,寄望于在民间野地中寻找到安妥现代人疲惫灵魂的憩息地。于是每逢所谓黄金周,城市人便像蝗虫一般涌向乡村,涌向那些所谓刚刚开发或者尚未完全开发出来的所谓新兴旅游热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到来不仅污染了当地人的纯朴心灵,而且对当地的自然生态也是严重的破坏和吞噬。现代人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破坏者,尽管现代人时常以世界的拯救者自居。这是现代人生存荒诞的一种表征,也是现代人无法解脱的生存悖论之一。
但仅仅写出这样的荒诞还不够,田耳的《到峡谷去》在现代旅游的时髦题材中开掘到了更深层次的荒诞意识。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两个城市妇女带着孩子去一个偏僻山乡旅游的尴尬经历,但作者的用意显然并不在于对这两个城市妇女受到当地人的欺骗抱以廉价的同情,甚至也不在于对当地民风受到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熏染而表达文化的批判,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就是一篇蹩脚而俗气的趋风之作了。田耳的这篇小说自有他独到的地方。作者的构思带有整体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按说,题目曰《到峡谷去》,很容易唤起读者的常规阅读期待,比如小说中将叙述某种穿越峡谷的惊险经历,或者穿插某种浪漫情感故事,严肃者类似艾芜的名篇《山峡中》,低俗者就是那种司空见惯的拍案惊奇的通俗小说了。然而,田耳没有这样做,他的构思蹊径独辟,他仿佛一个怀着恶意的导游,引领着读者作了一番没有结果的旅行。一般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读者也许会生气,因为这太不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了,甚至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小说中那两位城市妇女的感觉如出一辙。但我要说的是,这正是作者高明的地方。田耳是狡黠的,他不是那种“向导”型的作家,他是另一种“误导”型的作家。传统的作家乐于充当读者的“向导”,而现代派和后现代的作家往往做着“误导”的事业。在我看来,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卡夫卡的《城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作品,就是二十世纪文学中充满“误导”精神的杰作。戈多永远也不会来,城堡永远也无法走进,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如此等等,证明了“误导”的魔力。显然,田耳深谙“误导”三昧,一方面,他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人酷爱旅游的病态冲动,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挖掘出了这种病态冲动背后的生存荒诞。可以说,田耳写出了一条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峡谷,真正的峡谷只存在现代人的心理幻象中,现实中的峡谷不过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山沟罢了。当旅游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时尚的生存习惯,其中所隐藏的生存荒诞就日益凸现,旅游已经成了一种随波逐流的从众行为,旅游的目的已经不再重要,旅游的过程甚至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旅游这个概念的空壳。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那两个城市妇女后来并没有把所谓上当受骗放在心上,对于她们来说,旅途中喋喋不休的妇女闲聊录成了她们此次旅行真正的中心,至于那个莫须有的峡谷,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读这篇小说时常会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十分明显,田耳是玩弄幽默的高手,这是一篇幽默感十足的小说。但这篇小说的幽默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幽默,比如鲁迅先生所推崇的幽默是那种“含泪的微笑”,按照他的思路,幽默的产生大抵与无价值的东西被揭露有关,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幽默源自性本能的无意识伪装;前一种幽默常使读者笑中带泪,可谓“白色幽默”;后一种大抵属于黄色幽默,如黄色笑话之类。这两种幽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在现代中国文学里又从域外引进了新的幽默形态,这就是黑色幽默。田耳的这篇小说就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一般而言,白色幽默和黄色幽默虽然也有消解的功能,但还是内在地预设了可靠的价值观作为参照系。而黑色幽默不同,荒诞感是黑色幽默的表征,虚无感则是黑色幽默的核心。这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幽默,是一种欲哭无泪的幽默。前两种幽默在消解的同时还期待着建构,或者消解得并不彻底,而这种幽默抽空了所有的信仰或者念想。在《到峡谷去》这篇小说中,幽默与价值无关,与本能无关,文本中隐隐地散发出一种虚无的气息。这和作品表层的调侃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语言和行为等细节上的夸张式的白描是作者的强项,但这种表面的幽默不过是作者用来装饰文本深处的生存荒诞意识的绚丽外衣罢了。
李遇春,著名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