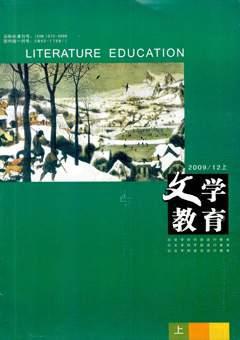文学作品批评的模式与方法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写作》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作品是文学创造的基本物化形态。作为人工创造物,有作者的劳动凝结其间,作为既按照“物种的尺度”又按照“内在的尺度”进行的创造,它又要显现外部世界的某种“意义”和文学创造者的内在需求,这种既合乎目的性又合乎规律性的创造物同时还要对读者公众发生影响,并通过读者公众影响文明或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凡此种种,说明文学作品既是文学创造的归宿,又是文学影响社会的起点,一切所谓“文学的”活动,只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才显示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作品因而也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对象,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也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类型。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萌芽状态的文学批评就主要是以谈论文学作品为特征的。古希腊例如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要谈论的是史诗和悲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批评原则和理论。中国自先秦至汉主要是谈论《诗经》和《楚辞》,以后才逐渐涉及时人作品。批评在进入近代以后,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构架日趋明显,人们于是根据批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谈论作品的不同方式,进一步把作品批评区分为更具操作意义的理论范型。例如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构造的以作品为中心,“由艺术家、作品、世界和听众组成的”批评的结构或图式就是:
“居中是艺术作品,即有待于我们予以解释的东西”,而解释作品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其中三类主要通过作品同世界、听众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艺术作品。第四类在解释作品时孤立地考虑作品本身”。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在归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时,也表示了类似于艾布拉姆斯的看法,即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是“文学的文本”、“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现实”、“文本与语言”,中心仍然是“文本”这个文学创造的基本物化形态。以下,我们将就这种区分,扼要介绍文学批评史上几种主要的作品批评形式。
首先是从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这种作品批评在欧洲文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其理论基础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及其派生理论,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基础,使得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虽然经由诸如浪漫主义的表现说和二十世纪以来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冲击,但仍然在批评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把文学作品理解为对外部世界的“摹仿”或“反映”,因而在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是十分注重从自然和社会诸因素中寻找造成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原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及其后派生的理论中,这个终极原因是广义的“自然”,即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世间事物。能否真实地摹仿“自然”事物即是判定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主要标准。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柏拉图否定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认为诗只能摹仿“自然”,但“自然”都是“理式”的摹仿,只有超出“自然”之外的“理式”才是真实的,因而诗不过是对“理式”的摹仿的摹仿,是不可能从中求得真理和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说法,他同样是从摹仿说出发,他认为诗所摹写的不是“已发生的事”,而是“可能发生的事”,诗中摹写的“自然”要比“自然”原有的样子更合情理,更带“普遍性”意义,因而实际上也就更加接近真实的“理式”。正因为摹仿说的理论十分强调艺术作品对于“自然”的摹仿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因而真实性和普遍性就成为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的一个重要判断尺度。这个判断尺度在现实主义那里被作了新的解释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尺度所取代,而且把前者作为决定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因其用“编年史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被巴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称道。相反,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则因为未能达到现实主义对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而被认为在体现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方面是不“充分的”。这种尺度有时候甚至被用来判断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纯粹形式问题,例如,新古典主义在恪守戏剧艺术的“三一律”方面,所持的根据就是不如此在观众看来就是不“真实”的和不合乎情理的。十七世纪法国戏剧批评家奥比尼亚克就认为:“同一形象(舞台)保持在同一情况下无法表现两件不同的事。”观众身在雅典,倘若把行动的地点从雅典移至斯巴达,那教可怜的观众怎么办?难道要他们像巫师一样腾空飞去?或是设想自己在同一时刻身处两地?这显然是把容纳戏剧情节的虚幻的文学时空与容纳生活事件的真实的物理时空混为一谈。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生活细节、活动环境,甚至人物语言的评判方面,古典主义的作品批评力求使这一切都逼肖“自然”或合乎“自然”的可能有的规律,现实主义的作品批评则要求在真实地再现现实的基础上将这一切升华到“典型化”的高度,亦即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中所特别强调的“本质的真实”。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形成的终极原因在注重社会学和实证分析的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在法国批评家丹纳那里,被分解为种族、时代、环境等三大要素,丹纳认为“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出悲剧,一座雕像,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这个“总体”,他认为第一是艺术家的“全部作品”,第二是与该艺术家“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第三是在这个“艺术家庭”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由此,他定下了一条作品批评的规则,即“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他对古希腊、罗马、中古时代、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分析就是运用这种理论观念和方法,并因此而奠定了社会历史学派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影响所及,以至于十九世纪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和二十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都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历史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在丹纳的三要素之外,把“生活方式”作为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文学的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这一方面补充了丹纳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又常常因为忽视决定与被决定的中介因素而陷入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的窠臼。由于上述形式的作品批评皆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外部寻找其意义和价值形成的原因,因而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又可称之为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
另一种也可称作“外部研究”的作品批评是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的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由于以抒情文学为主的中国古典文学十分重视对作家的心志研究,因而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观念在中国古代较早就开始萌芽滋生。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即是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成因归结为作家的心志的抒发。虽然后来有诸如“物感说”之类的理论进一步追寻作家心志形成的外在原因,但从创作主体出发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始终是中国古代作品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尤其是在魏晋南此朝以后,钟嵘的“缘情说”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诗言志”过于道德化的正统解释,使诗所抒发的感情更趋向于接近世俗的物事,曹丕又在总结和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进一步把作家的个性气质对文学作品的决定作用由诗推及更广泛的文学对象,使得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在理论观念和基本的概念范畴等方面日渐趋向成熟。例如在这个时期,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已经比较集中地谈论文学作品的风格问题,曹丕不但以“气”为标准区分不同作家的创作的风格特征,所谓“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等等,而且还指出决定文学作品风格的“文气”“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指出文学作品的风格是由作家的“才”、“气”“学”、“习”四种因素决定的。所谓“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影响到文学作品,则“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乘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而且在他所区分的八体风格之上,独标“风骨”,把一种肇自“骏爽”之气,“清峻”之风,“端直”之骨的风格作为对文学作品风格的最高要求。这种理论一直影响到皎然、习空图等人的诗论,成为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作品批评的主要课题。宋以后的作品批评由于引进了禅学理论,以禅喻诗,讲究“妙悟”,无形中就把作家对前人诗歌,尤其是汉魏、盛唐诗歌作品的“广见”、“熟参”当作了诗歌创作的主要源头,由于强调学诗的“妙悟”,故而要求于创作就十分注重作品对读者的暗示性,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这些理论和唐人类似的说法一起经过后人的不断创造,便铸就了“意境说”这个自宋以降迄于明清各代诗歌作品批评的中心观念。“意境”虽然有“情”、“景”之别,即后者写“客观”的“自然及人生事实”,前者写对此种事实之“主观”的“精神态度”,但一切“客观”的“景”又只有被“主观”的“情”所浸染,才能造就艺术的意境,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即是这个意思,故而以“意境说”及其相关理论为中心的作品批评自然属于从作家的主观情志出发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之列。与此同时,明清两代的文学批评又有人标举“性灵”,即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或言“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钟惺)“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袁枚)等等,都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论及文学作品的。此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常把作家的“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清代刘熙载“诗品出于人品”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言论,所谓“英雄出语多本色”,“壮士之赋,无一语随人笑谈”等,也都把作家的道德性情作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形成的终极原因。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作家与文学的关系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不但是中国古代作品批评的一个悠久传统,而且在批评实践中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概念网络和理论范畴,这对于理解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的实质是极有意义的。
在欧洲文学史上,从作家与文学的关系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虽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创作的天才和灵感的论述中就有萌芽,尤其是郎加纳斯,更加强调诗人的天才和德行与诗歌作品的密切关系,按照他的说法,“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把整个生活浪费在琐屑的、狭窄的思想和习惯中的人是决不能产生什么值得人类永久尊敬的作品的”。但这种形式的作品批评见之于比较自觉的实践则基本上是在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时代。由于浪漫主义文学注重抒发作家的主观情感,因而作家的心志就成了作品的题材和渊源。例如华兹华斯就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穆勒沿用华兹华斯的说法,也说诗是“情感的表达或倾诉”,“诗歌是感情在孤独时刻向自身所作的表白”,“一切诗歌都具有一种独白的性质”等等。他并且根据上述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对于诗歌作品的新的批评标准。例如他一反新古典主义对于不同种类的诗歌作品的评价和区分,把抒情诗提高到远比史诗和悲剧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认为史诗就其作为叙事诗而言,根本就不是诗,而抒情诗则“比之其他类的诗更富有诗意,更具有诗歌独特的气质”。与此相联系的是,他把诗人区分为“具有天赋的”诗人和“陶冶而成的”诗人,认为前者写出的诗“就是感情本身”,后者写出的诗则有“明确的目的”(即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所以前者“是远比其他诗歌优秀得多的诗歌”。这些关于诗和非诗,以及诗的不同价值的理论,显然都是以创作主体是否“有情”和这种“情”流露在诗歌作品的自然真切程度作为评判标准的。对于诗中描写的“客观”景物,他也表示了类似于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的某些看法,例如他说诗人“写景”的能力不是“写作那种通常叫做描写性诗歌的枯燥作品的能力”,“而是伴随着人的某种感情状态而创造景色的能力;情景是那样交融,以至景成了情的具体象征” 。这和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凡此种种,说明在中外文学史上,从作家与文学的关系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与以“摹仿说”和现实主义的“再现”理论为基础的作品批评确实是存在着根本区别的。而且,一般说来,前一种作品批评的重点是抒情性的文学作品,后一种作品批评则基本上是以叙事性作品为对象的。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批评中,以弗洛伊德的心理——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分支例如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为背景的作品批评,应当属于从作家出发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范围。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欲望和下意识活动作为文学的原动力和创造的渊源,是阐释和理解文学作品的主要依据。因此,心理——精神分析学的作品批评往往十分注重作家在儿童时代的经历和个体心灵成长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可能引起心理变态和压抑性爱欲望的生活事实,把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一种下意识的作用,作为解开文学作品奥秘的一把钥匙。例如达·芬奇笔下的圣母像被解释为作者对早年离别的母亲的依恋和思念的下意识活动的升华,莎士比亚和惠特曼的诗,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和普鲁斯特的小说等,都被解释为被压抑的性的渴望的冲动和外化的产物。当这种解释和分析作品的方法被运用于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生活事件时,甚至连人物形象和生活事件等文学创造的产物也被充分地“主体化”了。例如用著名的“俄狄普斯情节”的理论分析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即是把哈姆雷特当作类似于作家那样的真实的生活主体的。这也无异于是说莎士比亚是借哈姆雷特“再现”了潜藏于他的下意识深处的“恋母情结”,从而构造了这部作品和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格的。总之,心理——精神分析的作品批评是把作家的下意识活动,尤其是被压抑的性心理作为文学作品的意义的终极成因,同时又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分析来印证被这一派理论所预先认定的那些心理事实的。正如美国学者魏伯·司各特所说:“这类批评认为,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本质联系,类似于病人和梦境之间的联系”,“作家在作品中‘掩藏了他的病态,批评家于是成了分析家,以作品为症状,通过分析这种症状,发现作家的无意识趋向和受到的压抑。”正因为如此,这一派的作品批评通常是不对作品的优劣高下作出价值判断和评价的。神话——原型派的作品批评因为与心理——精神分析理论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关系而未从根本上脱出心理——精神分析的作品批评范围。不同的是,神话——原型理论不把作家在创造文学作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无意识事实看作纯粹个体的东西,即所谓个体无意识,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整个种族从原始时代遗传积淀下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无意识心理特征,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同于心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也就越不成其为艺术。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这实际上是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再现和记录。作家个人在艺术创造中的意义既属无关紧要,对作品的批评就主要是发掘和认识人类集体无意识借文学作品所获得的不同表现形式,从中找出那些能够使读者的心灵产生认同和共鸣的心理因素。例如荣格就认为歌德的《浮土德》中的浮土德博士和尼采的《查拉图拉斯如是说》中的主人公就是一种“智者”和“救世主”的原始意象(原型)。这种原始意象自文明之初,就已经潜藏蛰伏在人的无意识之中;“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有一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诗人和作家则把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出来,使之成为读者的心灵和精神上的真正的“导师”和“向导”。如同心理——精神分析的作品批评一样,神话——原型一派的作品批评也是把文学作品作为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实证对象和范例,二者一般都不涉及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较之以“摹仿说”和“表现说”为理论基础的作品批评,这两种以心理学为背景的作品批评都带有比较浓重的科学主义倾向。
“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的作品批评被韦勒克、沃伦称之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在欧洲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作品批评形式。其中又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和风靡欧洲的结构主义批评为代表。因为这些学派的作品批评把目标集中于关注作品的形式分析,因而通常又被人们称之为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按照美国学者佛朗·霍尔的说法,“对于诗和散文作品的文词结构本身的精密剖析的方法原来是源远流长的,由古希腊罗马人,经过古代典籍的伟大经师和法国的经典评注家而传之于近代的精读派读者”。后者即是运用“细读”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新批评派的批评家。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十分重视对文学作品自身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于诗歌作品的音韵、格律、造境、用事等方面的形式技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在古代批评实践中,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南朝齐梁时代周顒、沈约等人在总结前人研究汉语语音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首创汉语“四声”说,并以此检视时人创作,指出众多的诗歌作品在运用“四声”方面存在八种病犯(“八病”),要求诗歌作品的声律要做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玄黄律吕,各适物宜”,“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并且具体指出,在一首诗中,“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等等,即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理论。这种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格律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格律诗形成之后,又成为我国古代作品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尤其是在宋以后的“诗话”、“词话”中,有大量篇幅即是对诗歌的音韵、格律的批评和考究。元、明、清各代,伴随着戏剧、小说创作的繁荣,对戏剧、小说作品形式技巧的批评与探讨,也日渐发展起来。其中尤其是在金圣叹对戏剧(例如《西厢记》)、小说(例如《水浒传》)作品的“点评”式的批评和李渔的戏典理论论著中,包含了对于戏剧、小说作品的形式批评的极为重要的经验和见解。由此可见,无论中外,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作品批评模式。
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无疑是前人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经验的一个合乎情理的继承和发展。但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显然又不可与古代的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同日而语。区别在于,前者是基于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而且把内容看作是形式的决定因素,要求文学作品做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例如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和白居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理论等等。后者则认为,“在一部成功的作品里,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形式就是意义”,就是内容。“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读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内容即经验与完成了的内容即艺术之间的差别,就在技巧”。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各种模式和派别的形式主义作品批评一般都倾向于割断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的联系,以便把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进行各自的批评和研究。英美新批评就把从作者方面追寻作品的创作意图的批评称之为“意图的迷误”,把注重作品对读者产生的心理效应的批评称之为“感受的迷误”,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特的可以认识的对象”,具有“特别的本体论的地位”,是“一个为某种特点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因此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和研究只应当是诗的“本体即诗的存在的现实”(兰索姆)。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新批评所全神贯注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整一”性问题,即“文学作品是形成了还是没有形成为一个整体,以及在建立这一整体方面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他们通过“细读”的方法,在字、词、句之间寻找可能出现的暗示、联想和言外之意,以及词句与词句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这种相互关联中确定字、词、句的意义和含义。同时也把诸如词语的选择和搭配、句型、句法、语气、语调、声韵、格律的运用以及比喻、意象的组织等等技巧问题巧妙地联系起来,通过这种“细读”,使文学作品最终显示出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的价值和意义。为此,新批评派对描述和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构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较有代表性的如韦勒克、沃伦把文学作品的形式区分为“不同层面”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层面”是:①声音层面,谐音、节奏和格律;②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③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④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⑤有关形式与技巧的特殊问题等。这些“分析个别艺术品”的理论和方法对具体作品批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作品批评中,新批评是一种既有整体观念又具备精细分析手段的形式主义作品批评模式。
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关注重点略有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这种使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既不是作品的内容也不是作品某种固有的性质,而是文学作品在组织和结构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习惯的语言方式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此,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十分重视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技巧的“陌生化”问题的研究。施克洛夫斯基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他们把这种理论应用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着力从语音、韵律、语意等方面发掘诗歌由于“对普遍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雅各布森)所造成的“文学性”。在叙事文学方面,他们致力于区分“故事”(obadyra)和“情节”(cromem),即“作为素材的一连串事件”和写进小说的“情节”之间的差别,从造成这种差别的“陌生化”手段和技巧中,寻找作品的“文学性”的种种存在形式和表现。例如他们认为果戈理的《外套》的“故事结构中的能动原则不在所述的事件中,而在它们的表现方法中,而这一表现方法本身,与其说是取决于故事叙述者的推定的性格,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双关谐语和其他词语的语音作用”,因此,这篇小说的“文学性”便是“某一纯粹语言手段的产物”。较之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更加显明地使作品批评从属于语言学研究,并努力使这种语言学研究式的作品批评获得更高程度的科学性。
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结构主义的作品批评,一方面不同于英美新批评把分析和研究的重点放在个别作品的形式本身,而是强调超出于个别作品之上的文学系统对个别作品的决定作用,研究那些带普遍性的东西对个别作品的决定意义,另一方面又比俄国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更为直接地移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使作品批评带有更为浓重的科学的语言学研究的色彩。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所探寻的是文学语言这种特殊语言的属性。一切作品都只能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结构的体现,是各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因此,这门科学所关注的不再是真实的文学,而只是可能的文学,换言之,是构成文学特殊性的那种抽象的属性:文学性。这种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去确定对某部具体作品的评述或合理的概括,而是要提出关于文学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提出能够提供各种可能的文学图像的理论”。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结构主义的作品批评的主要特征,即“不以对个别作品本文作出解释为目的,而是通过与个别作品本文的接触作为研究文学语言活动方式和阅读过程本身的一种方法”,从中探究那些对个别作品起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文学的普遍规律和特性。为此,他们基本上摒弃了传统的作品批评常用的经验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如同现代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结构那样,用演绎模式的方法——即“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巴尔特)——对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在对具体的叙事文学的作品结构的分析中,这种模式化的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巴尔特构造的关于文学作品的描述层次的模式即把叙事作品的结构模式分为三个“描述层”:(1)“功能”层,主要研究作品中的基本叙述单位及其相互关系;(2)“行动”层(亦称“人物”层),着重研究人物分类及其结构原则;(3)“叙述”层,研究叙述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托多罗夫则把叙事作品当作“话语”来研究,具体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和“叙事语式”三个方面探讨了“话语”表现故事的模式。热奈特也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为三个“层次”,即(1)“故事”,表示所指或叙述内容;(2)“叙事”,表示能指、文字、话语或叙述文本本身;(3)“叙述”,表示创造性的叙述动作,等等,通过这些模式,他们逐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于叙事作品的语言结构分析的规则体系,为深入把握叙事作品的“无信息的编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图式。与此同时,他们受普洛普对童话故事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体裁所作的模式分析的启示,也对叙事作品的体裁进行了系统的模式分析,企图从中找出那些对每一具体个别的叙事作品起决定性作用的文体构成因素。例如弗莱从“主人公的行动力量”与“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构筑的小说体裁的五种模式:(1)神话:主人公的力量绝对地超过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力量;(2)传奇:主人公的力量相对地超过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力量;(3)高级模仿小说(现实主义):主人公的力量相对地超过其他人物的力量,但超不过环境的力量;(4)低级模仿小说(自然主义):主人公的力量不超过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力量;(5)讽刺性小说:主人公的力量弱于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力量。罗伯特·史柯尔斯则从虚构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构造小说体裁的三种模式:(1)浪漫小说:虚构世界胜于经验世界;(2)历史小说:虚构世界相当于经验世界;(3)讽刺小说:虚构世界不如经验世界等。这些研究虽然更加远离具体个别的文学作品,但却是具有宏观意义的一种结构主义的作品批评形式。在所有形式主义的作品批评中,结构主义的作品批评是一种高度抽象、高度模式化的作品批评,它的对象既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亦非文学作品的个别形式,而是整个文学,是使文学产生意义的各种方法和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的作品批评又是一种“反作品”的作品批评形式。
上述形式的作品批评都可以称之为从读者与文学的关系的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因为无论是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作社会历史的解释和评价,抑或是从创作主体和作品本文找原因,都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解释和评价。从这一点上说,前述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图式中有关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理论维度是指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作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以文学作品作为直接的解释和评价对象的作品批评。虽然“对读者的影响”也包含有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但关于这种影响的艺术成因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上述形式的作品批评的一般原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美学虽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和富于创造性的从读者与文学的关系的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作品批评,但上述形式的作品批评的一般原则,同样也可以容纳接受美学关于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最新观念。无论从哪方面说,作品批评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以“摹仿”理论、表现理论和本体理论为基础的各种不同表现的作品批评。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则有以单个作品为对象的作品批评,着重解释和评价个别作品,具有比较典型的微观批评的特征,而从纵向或横向集合一群作品或以它们的某一侧面作为阐发对象的作品批评,则大都带有宏观批评的性质。无论“微观”、“宏观”,都可能成为上述形式的作品批评的一些基本的实践方式。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批评理论的方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6至7页。
[2]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0至13页。
[3]转引自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页。
[4]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4至7页。
[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8至159页。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505页。
[7]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125至126页。
[8]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36页。
[9]魏伯·司各特编著:《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6页。
[10]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140页。
[1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143页。
[12]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1页。
[13]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1779年。
[14]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2页。
[15]马克·肖荣尔:《作为发现的技巧》,转引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第1版,第43页。
[1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版,第164页,第147页。
[17]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2页。
[18]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版,第165页。
[19]转引自张降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版,第75至76页。
[20]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此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3至24页。
[21]张秉真、黄晋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5至56页。
[22]张秉真、黄晋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