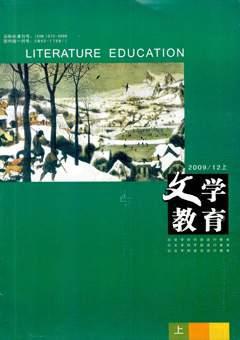人生滋味
谢 伦
这边那边
今天起一个大早,走高速,还不到九点,朋友吴露就用他的越野车给我送到了吴店镇。大哥和弟弟正站在街口等我。回乡上坟,这是一年一次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5日,我们家乡的乡俗是不能在清明的当天上山,要么前三天,要么后三天。村人们一般是选在前三天。这类事我们兄弟都不懂,不懂,就从众。
吴露还要赶回市里忙他的事情。临走时他问晚上了要不要再来接我,我说不用。车发动了,他又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说,那你就在老家多住几天吧,难得今年的天气好!他没说今天,说今年,是指没有以往按惯例前来造访的“雨纷纷”。我向他挥了挥手。想前些日手机里还反复预报有雨,还一直担心乡下的泥路不好走呢,好在只阴冷了几天,说晴也就晴了,一晴气温迅即转暖且呈直线上升。昨天终于把捂了一冬的毛衣脱了,怕上山路热,临走时又减去一件秋裤。妻说你这岁数了不行,不能减太猛,要感冒的,叫我再穿上。可穿上了还是觉得多,就又脱了。看来脱了还是对的,一路上春气徐徐清而不冷,旷野路边绿树芳草鸟语花香,到了吴店镇上,姑娘们都穿起裙子来了。吴店是枣阳市的一个大镇,它是枣南往沙洋、荆州、宜昌等地的交通要道,平时就人多,逢节就更热闹了。我和哥、弟挤进人堆里买了黄草纸、鞭炮、坟飘儿和柳枝,又挤出来在路边用百元大票在草纸上一一捶打——把草纸打成冥钱。这还是传统的老做法。时下新派的儿孙们早不买草纸了,买现成仿真的人民币,有百元万元乃至十万元一张的超大票儿,三五块钱就可以买上千万,甚至是几个亿——买冥钱论的是“张”数,不论“元”数,想给地下的老子送多少就买多少,免去了在黄草纸上拍拍打打的麻烦。
待打完纸钱,一叠一叠地在挑篮里码好了,我心里反而不安起来,算算我们兄弟挑一担的纸钱还不及别人一张的冥票多,由此及彼,父母亲在那边岂不又要受穷?真是穷怕了,遂转过去也买了冥票儿两个亿。大哥、弟弟都笑,我也感到好笑,可是,钱多好办事,谁又能保准这边看起来的假票儿,到了那边就不会成为真票子了呢?
父母、二哥的坟墓都在镇子前面的山腰上。山上多松柏,多樟槐,更多野花。每年一到三四月,便杂花生树,漫山的灿烂。开得最多的要算一种叫晕头花的花(不知学名),茎细叶小,花成串儿,色淡紫,都半尺或一尺来高,一束一束的摇曳在路边坡下。为什么叫晕头花啊?弟弟说,听说是闻着头脑发晕呢。我采一把放到鼻前嗅嗅,没晕,倒是有一种甜甜的清香味;再就是那些白繁繁的野荆花及贴地的像星星一样的是碎米花了。蒲公英花也不少。偶尔在背阴的陡峭处还可见飘飘拂拂的迎春花,奇怪,怎么四月了还有迎春花?当然,最抢眼、最热闹的还是坟头上“盛开”如灯笼似的大红大绿的锈球花、牡丹花——这些花都是“开”在柳枝上的——小时候记得乡人们上坟用的剪彩花都是白色的,而且小,是取一种淡淡的静哀;现在不同了,现在什么都讲究热闹好看。这样也好,热闹些,好看些,益于视觉的愉悦,以免给自己留下过多伤感的机会。——毕竟,活着的人也都活得孤独沉重不容易,不在外在的形式上寄托一下,冲淡一下,麻木一下,一旦勾起早已深埋的凝血亲情,怕是支撑不住。
半晌时起风了,不算大,松树的枝叶呜呜吹起鸽哨。还好,已叩过了头,手边的火焰渐息,风急急的在地上打旋,灰烬如黑色的蝴蝶飘飘飞升,消逝。物质的转化,会觉得肉眼看到的一切都不真实,很容易想它们就是先人的魂魄。
桃之夭夭
中午去镇上弟弟家吃饭。弟媳妇做菜的手艺真是好,春韭、水芹、茼蒿、不起豆油的白豆腐、青菜苔,皆清香馥郁,鲜嫩可口。木心说,中国的瓜果蔬菜,无不有品性,有韵味,有格调,是天赋的清鲜。这话看来不假。口腹之欲,让我想起“莼鲈之思”。可晋时张翰的潇洒,现代如我辈是绝不敢做,也做不到了。饭间聊起了妹妹下岗的事,弟弟、弟媳所在的造纸厂因为污染被上级强制叫停的事,怎么办呢?打工去?都是几十岁的人了哇!日子得继续,一时又没有什么好主意。原定今年给父亲立碑,大哥大嫂都说再等一等。长子如父长嫂如母,我们都是听大哥大嫂的。
午后坐小院里喝茶,晒太阳,身上就有了暖哄哄的太阳的气味。“还乡”的恬静,有如在地边青草丛里听小虫子们叽叽鸣叫。其实说“还乡”谈不上,一是没有“锦衣”,二是吴店镇严格说还不是我的“乡”,我的“乡”在镇子以东三里之外滚河北岸的周家湾。我出生在那儿,并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哥说,伦保(我二哥)过世时湾里人帮忙大,为答谢乡亲们他去年回过一趟老家。大哥说老家湾子变完了,快认不得了,过去的房子包括我们家的老屋都被人推倒重新盖起二层楼了。我问大哥,我们家从湾里搬到镇上有多少年了?大哥说八五年搬的嘛,那时你还在学校读书呢,现今有二十多年了。看,又一个二十多年!人间祸福,辗转周旋,一百年也就五个二十年,眨眨眼就过去了。此时我们坐在小院儿里晒太阳,喝茶,说往事。——太阳若梦,往事若梦,人若梦。
忆及老湾子,最早入梦的应该是那条被折的桃花枝。在村西头,在三通间的牛屋里,中间用两根松木杆子隔开,一边是吃草的牛,一边就是村里读书的娃娃们。我们老师是来自县城的女知青,一对齐腰大辫子的美人儿,人面如花,美而惆怅。惆怅,大概就是因为牛屋外的那片桃园吧。桃园是生产队的桃园,有百十多棵。春头上,老师用鸟儿一样翠的声调教我们唱:“春天来了,青草发了,窗外的桃花开了……”我们亦鸟儿样地跟着唱:春天来了,青草发了,窗外的桃花开了……
第二天一早背着书包上学来,天还冻得脸红鼻涕流,可那桃园的桃花就真格开了——桃花一夜雪如堆——红雪,如云。那时候我们才发毛(启蒙),没有书本,书包里除了一支铅笔和用纸烟盒自订的作业本外没有其它。所谓教唱的课文,我估摸是她编的。她把自编的课文一笔一划地写在黑板上,然后转过身来,用根细细的柳棍儿指着教我们。可我们哪有心事去看黑板上的字啊,都在看她桃花儿一样的脸,她那双清澈如晨露的大眼睛。老师好漂亮!
那老师姓什么呢?想过,一直没想起来。现在能记得的只是她的俊模样儿了。再记得的就是在桃花盛开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从外队(后来听说是第十一生产队)来了一个男知青和她相拥在繁花如锦的桃园里。可万没想到被队上喂牛的黑老戈(人黑,姓戈)发现了。黑老戈是个老光棍儿,不过这并不主要,主要他是老党员,还是村队委会的成员,自然是有资格教育她:自身不正哩,还不把娃娃们教歪了?一愤怒,告到支书那儿,最直接的证据,除了他亲眼所见的“亲了嘴儿”,就有一条被她折断的桃花枝。
记忆的春天,其桃花开也忽焉,落也忽焉,如雪片一样,缓缓而下,幽若芳魂——比喻,有如蔡琴的歌声:温情款款,隐隐忧伤。桃花毕竟是太美艳,美而易折,刚一转身就觉出它别样凄凉的意蕴了——老师走了,有两说:先说是和那男知青结婚去了,这故然好;可后一说就不好了,说是死了,并且得到了某些村人的证实。为何而死?这就不该是小孩子知道的事情了。我辍学了,好玩儿得很,二十几个孩子坐在有牛吃草有牛屙屎的教室里空等了一个上午,之后,队长来了,队长来了说各人把自家的小板凳搬回去吧!在我读书生涯中共有两次辍学,那是第一次,是集体辍学。
巧的是,没过几年(可能是三五年吧),黑老戈也死了。而且同是在春天。在生长过那片桃树林的土地上(桃园已废),队里办起了养猪场,盖了豆腐铺,喂牛的黑老戈和养猪的菊姑娘就在豆腐铺的柴禾窝里亲了嘴儿,过了皮。呜呼!桃园虽废,曾经盛开的桃花却依旧温暖着乡人的粗粝生活。只不过,黑老戈的年龄已快能做那菊姑娘的爷了。但古话说得好,春天里枯树也想开花,何况人心?要命的不是他的年龄,是他的觉悟——头上有一顶共产党员的红帽子,他在遗书里写到: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时光如烟。大哥说,那片桃园他已是很恍惚了。又问:你还辍过学?……我终于明白,童年经历的事情大多是靠不住的,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旦枯萎零落她就不再是花了,是泥。
——人世不过如此,一回首,皆成往昔。
(选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