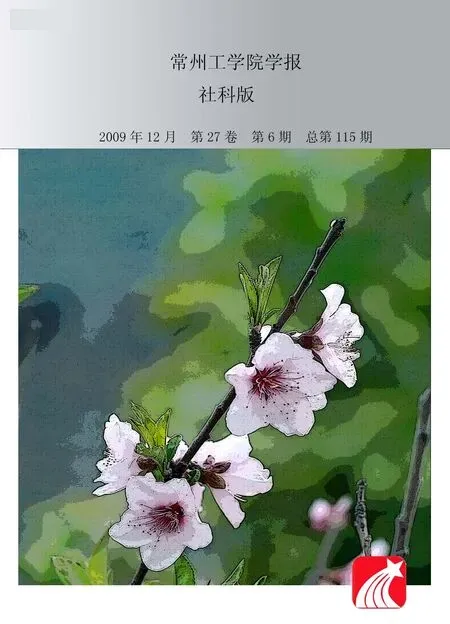失衡的社会 扭曲的心灵
——《最蓝的眼睛》之生态学解读
吴文权
(宿州学院外语系,安徽 宿州 234000)
“生态学”最早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但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生态危机的警钟频频敲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学批评相继直面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追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从20世纪90年代起,“生态学”从单纯的自然环境研究不断渗入到其他学科,产生了诸如“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新型交叉学科。按照鲁枢元的划分,生态学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以相对对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1]。学者刘文良也指出,生态危机绝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自然生态危机,还有社会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批评也不单只是关注自然生态这一层面,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样是生态批评所必须关注的对象”[2]。
文章借助生态学批评相关理论,从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两个层面对《最蓝的眼睛》进行文本解读。在这部作品里,莫里森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故事,探索了黑人的历史与命运、种族与家庭,并将笔触深入到黑人的灵魂深处,从而构建了一个个在社会和精神失衡生态系统中苦苦挣扎着的美国黑人形象。主人公佩科拉在双重失衡的生态环境里成长,祈求能得到一双最蓝的眼睛,从而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然而,处在社会生态系统最低端的黑人社区,她会有救赎的希望吗?佩科拉苦苦追寻无果后最终发疯了,莫里森由此告诉人们:美国现存的社会生态系统往往导致年轻一代黑人心灵扭曲、精神世界失衡,美国黑人民族彻底救赎的希望十分渺茫。
一、社会生态的失衡
“社会生态是就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及文化生态而言,是人类生态系统的基础性存在结构。社会生态以人与社会、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生态平衡表现并延伸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3]抛开与自然生态的联系,社会生态实际上强调的是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自然界的生态危机。《最蓝的眼睛》就展示了黑人社会中种族歧视严重、经济条件低下、家庭关系冷漠等。
美国社会存在着白人、黑人以及其他来自亚洲、南美洲等地的有色人种,但黑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因为黑人的祖先最早是被当作奴隶从非洲贩卖过来的,因此,种族歧视在美国一度盛行,即使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后黑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小说主人公佩科拉的母亲分娩住院时,白人医生这样描述黑人产妇:“这些女人接生不会有麻烦,她们生起来很快,也不感到疼痛,就像下马驹儿一样。”[4]99佩科拉尽管只有11岁,也处处遭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她去买糖果时,店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移民,连看都不愿意看她一眼,“感觉没有必要浪费他的眼神”,目光里“没有一丝对人类的认同”,“在下眼帘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的是厌恶之感”[4]42。在学校里,老师瞧不起她,所有的老师“总是避免看她”,也从来不喊她回答问题。没有任何同学愿意和她同桌,“她是班上唯一单独使用双人课桌的人”,她被一些同学当作侮辱某个男孩子的工具,因为只需说某个男孩喜欢佩科拉就会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以及被嘲弄者的咒骂声。
黑人社会生态恶化还体现在黑人的经济状况十分低下。小说开篇就展示了一个贫穷困苦的黑人社会:故事的叙述者每天晚上跟大人一道,沿着铁路线拾火车经过时散落在铁道旁未燃尽的小煤块,她家的房子“又旧又冷,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4]12。佩科拉家更是一贫如洗,连住房都没有,一家人挤在废弃的库房里,用胶合板隔成一间间小屋,阴暗、寒冷、家徒四壁。她所属的整个黑人社区死气沉沉,充满穷苦、衰败、暴力、酒精与卖淫女。而离黑人社区不远的白人社区,则是另一番模样:到处是玫瑰花、喷泉、绿草坪、野餐桌椅、漂亮的房子,院子里点缀着被修剪成锥形、球形的灌木丛。这天壤之别,曾使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不无悲哀地谈到:“黑人,只因肤色与众不同,过去,被人看作奴隶,现在成了贫困的象征。”[5]
家庭也是黑人社会生态失衡的重灾区,其悲剧色彩在于:笼罩在黑人家庭的不是爱与和谐,黑人家庭中父母缺乏对孩子的关爱,夫妻关系异常。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出生时就被父母抛弃,成了孤儿,后来虽然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却被无情地赶走。他本是黑人社会生态的受害者,但“亲生父亲的拒认对乔利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极度无依无靠,也无需对任何人负责和承担义务。这样,乔利缺乏家庭亲情的关爱,也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可避免地导致后来对他人的伤害事件”[6]。佩科拉的母亲感到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白人的家庭工作中。她把主人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对自己的家没有丝毫兴趣。她对主人家的女儿疼爱有加,却舍不得给佩科拉半点母爱。另一位肤色较浅的黑人杰萝丹家庭经济条件要好一点,但她同样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感情,从不和孩子谈笑逗乐,也不亲吻溺爱,她对儿子的爱远远不及自己养的一只小猫。在夫妻关系上,黑人家庭也是缺乏关爱的。佩科拉的母亲之所以和乔利生活在一起,是把自己扮演成殉道者的角色,她认为自己受丈夫拖累,甚至诅咒自己的丈夫,祈求上帝惩罚他。无休止的争吵成了他们夫妻生活的必备内容,莫里森辛辣地写到:“布里德洛夫太太平淡无味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界定、来组合的。这些争吵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内涵,否则,生活暗淡无光,不留任何痕迹。争吵能消除贫困带来的烦恼,也使死气沉沉的屋子有些生气。”[4]36-37另外,莫里森有意安排杰萝丹的丈夫缺场,表明在杰萝丹的意识里丈夫可有可无。她对自己的丈夫既没有情爱的举动,也没有正常的性爱,而是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在一只猫身上,从抚摸猫的行为中获得极大的性满足。
二、精神生态的失衡
生态学对人类精神的关注是伴随工业化产生的,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消费社会以来,生态学者发现,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出现生态危机,人类自身的精神,诸如人的信仰、信念、追求等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精神生态学应运而生。按照鲁枢元的观点,“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7]。精神生态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着与自然生态相似的危机。与社会生态失衡相比,美国黑人社区存在一种更深层的精神生态的失衡。
就全书主题来看,《最蓝的眼睛》实际上是莫里森对非裔新一代黑人精神状态的一次诊断,黑人的种种困惑、迷茫、失落和痛苦意味着黑人精神已经全面扭曲。这首先体现在黑人认可“白人至上、黑人卑下”这一奴化思想。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年轻时,遇到黑人女孩达琳,他们在树林里发生初次性关系时恰巧被两名白人猎人撞见,这两名白人用长枪指着乔利,命令他当他们的面继续做爱。乔利屈辱地按照他们的要求表演,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愤怒。可悲的是,“白人至上”的观念已经内化为黑人屈辱的精神信念,乔利不仅不敢反抗,他甚至不敢对白人有丝毫不满,却将愤怒发泄在同为黑人的女伴身上:“他看了一眼达琳。他恨她……他对她恨得要命”;事后第二天,他还沉浸在这种愤怒中,“他绷着脸,烦躁不堪,把怨恨都撒向达琳。他一次也未想过要怨恨那两个猎人。这种想法会毁了他。他们是高大带枪的白人,而他是弱小无助的黑人。他下意识地明白仇恨白人会让他自取灭亡,会让他像煤球一样燃烧,只剩下灰烬以及团团的青烟”[4]117-118。
其次,黑人精神生态的失衡体现在黑人审美观的扭曲上。小说笼罩着深深的蓝调:在黑人意识里,他们是丑陋的,这在佩科拉一家人身上得到了体现。父亲乔利不仅觉得自己丑陋,还把这种丑陋表现在行为上:他不断用酒精麻醉自己,又通过打骂妻子、赶走家人、纵火烧屋发泄自己的愤怒,变成了如同“老狗、毒蛇、耗子一样的‘黑鬼’”。佩科拉的母亲波利“像演员对待道具那样对付丑陋,为的是塑造性格”,她对女儿不闻不问,即使是在女儿被父亲强奸后。“当波利用自己已被白人文化价值观扭曲的视线看不到自己女儿的可爱时,她的情感变得贫乏,责任、道德及亲情可悲地缺席——她的精神被污染了。”[8]佩科拉本人则是这种扭曲的审美观受害最深者,她幼小的心灵是不懂得种族歧视的,她只相信:在学校受冷落、回家途中受欺侮、在商店受歧视、在家里父母不爱她全是因为自己长得丑。为了能得到社会的接受和父母的爱,她沉浸在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中,她幻想使用印有白人童星的杯子喝牛奶、吃有蓝眼睛图像包装纸的糖果就会拥有蓝色的眼睛。但这并未给她带来所期盼的蓝眼睛,她在精神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后来试图寻求上帝赐予她一双蓝眼睛,但作为佩科拉精神寄托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助纣为虐,反成了导致佩科拉精神绝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帝的代言人——皂头牧师不是进行精神疏导以帮助佩科拉走出精神危机的阴影,而是利用佩科拉去毒死一只厌恶已久的老狗。佩科拉苦苦追寻一双蓝色的眼睛最终发疯,直接原因是佩科拉的审美观扭曲,但社会和家庭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次,黑人精神生态的失衡还体现为黑人自身文化的失落。“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9]细读作品不难发现,在铺天盖地的白人文化席卷下,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自身的文化遭到践踏,其黑人文化身份渐趋丧失。黑人的幼儿读物渲染的是白人之家的幸福模式,日常生活用品都印上蓝眼睛白人明星的图像,电影讲述的是“那个混血女孩儿恨她妈妈,因为她是黑人,而且长得很丑”[4]57,甚至高等教育灌输的也是精神奴化思想,黑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如何尽善尽美地替白人干活:家政课学习如何为他们做饭,学教育用来教育黑孩子顺从听话,学习音乐好安抚劳累的主人和他那颗迟钝的心灵。……总之,要学会抛弃纯真简朴的本色、可怕的纯真情感。自然大方,以及一切人类感情都该抛弃”[4]68。
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摧残下,黑人与本土文化渐趋疏离,白人的文化代替了其自身文化的根基,黑人找不到精神的皈依和拯救。于是,暴力、酗酒、卖淫、疯癫,甚至强奸自己的女儿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丑陋的,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莫里森借助小说叙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似乎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疑问便接受下来。主子说:‘你们都是丑陋的人。’他们四下里瞧瞧,找不到反驳此话的证据;相反,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目光都为此话提供了证据。”[4]34
三、结语
莫里森通过《最蓝的眼睛》展示了美国黑人社区的生态图谱,这是一幅失衡的社会生态图。自然界的和谐来自于自然的生态平衡,而社会的不和谐,恰恰也源自社会生态的失衡。这种失衡是与黑人社区的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交织在一起的,源自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以及白人文化价值观。由此可见,佩科拉的悲剧绝不是偶然现象,她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种族歧视与黑人文化身份沦陷的必然产物。佩科拉是莫里森塑造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在黑人社区失衡的生态环境下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她的最终疯狂无不暗示着黑人救赎的无望。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刘文良.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维度[J].理论与改革,2009(2):95-98.
[3]盖光.社会生态平衡与共生性的生存“合力”[J].江汉论坛,2009(6):20-24.
[4]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2.
[5](美)查尔斯·鲁亚斯.美国作家访谈录[M].粟旺,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26.
[6]Carmen Gillespie.Critical Companion to Toni Morrison[M].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2008:51.
[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48.
[8]焦小婷.寻找精神的栖息地[J].山东外语教学,2004(1):102-105.
[9]孙文娟.迷失与探索——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4):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