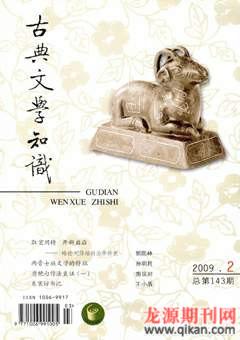《文选》赋类序说
王德华
作为现存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文选》不仅为后世留存了先秦至齐梁间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文选》作为有选择性的“选本”,业已成为编选者考察特定文学体裁、表达文学观念的重要载体,并在文体分类上起到垂范后世的重要作用。《文选》首立赋类,赋体在《文选》各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不容忽视。
李善注《文选》本共60卷,赋类19卷,约占三分之一。19卷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门类,共56篇作品。很明显,15门类的分类标准主要是根据标题与题材,据此我们很难总结出《文选》赋体作品的主要内容。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进行“原本以表末”发展梳理时,涉及赋体功能与体制分类,既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也有“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虽然刘勰把“述行写志”也归入“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畛域有其不当的一面,应该独立开来,可作为“情志”一类,但是他初步提出的大赋与小赋的分类方法,对我们进一步概括《文选》分门较细的15门类赋体作品并进步了解赋类作品的主要内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我们看看《文选》赋体15类中所载大赋。赋称大者,约有两端。从主题上说,刘勰所说的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征,这“体”与“经”为动词,而“国”与“野”相对照。也就是说,大赋的基本功能即全面描述整个社会的风貌,关涉一国体制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因而表现出体现劝百讽一、光明正大的的文化特点。因而,我认为,刘勰用这八个字是很能概括出大赋的政治文化的指向的。从外在体式上看,表现出长篇铺陈的特征。《文选》赋类有关体国经野的大赋约包括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等门类,如京都类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及左思《三都赋》,郊祀类扬雄《甘泉赋》,耕籍类潘岳《藉田赋》,畋猎类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长杨赋》等。这些赋作,借助对京都、帝王重农耕藉、重嗣郊祀、讲武畋猎等方面的描写,或颂或讽,主要表现了对有关国家政治文化及制度的看法,是大赋中的代表作。其次,《文选》中的小赋作品。赋称为小者,义有如下两端:一是相对于大赋之篇制而言,篇幅短小,没有宏阔的结构与大量的铺陈;二是托物写志上不是关乎重大的政治与思想问题,不像大赋那样“体国经野”,只是涉及道德政教诸多琐细之处,或者仅为帝王的娱乐而托以道德说教,故其所托之物也多为禽兽鸟木花草日用物品之类的“小物”,或其所咏对象亦为音乐或舞蹈之类。这种小赋创作源于荀卿赋,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均有继作,成为赋体创作中重要的一类。清代王芑孙《读赋卮言》说:“赋者,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聊以小言,犹云短制,在汉则刘安、枚乘、邹阳、严忌、桓谭、赵壹、孔臧、路乔如、黄香、蔡邕、李尤、杜笃、公孙诡、闵鸿、侯瑾之徒,碎金屑玉,慭遗选外。”(王芑孙《读赋卮言·小赋》,《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见《赋话广聚》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从《汉书·艺文志》及《西京杂记》所存小赋看,其数量还相当可观。《文选》赋类中小赋有物色类如宋玉《风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鸟兽类如颜延之《赭白马赋》,音乐类王褒《洞萧赋》、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嵇康《琴赋》、潘岳《笙赋》、成公绥《啸赋》等。这些赋通过特定对象诸如风、雪、月、白马、洞箫、舞、长笛、琴、笙、啸等的描写,最终表现或颂或讽的作赋目的。最后,我们看看《文选》赋体“情志”类的作品。此类作品相当于刘勰《诠赋》中提到的“纪行述志”类赋作,在《文选》赋类中相当于纪行、游览、志、哀伤、情等几类,志、哀伤、情类较明显,可以归为情志一类,而纪行、游览类,往往通过纪行、游览方式或述怀古之幽情,或发抑郁不平之气,都是创作主体一己之情志的发抒,标题虽异,实与“志”类等同。这类作品,创作主体往往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抒情言志,与大赋、小赋托物言志、以讽喻为旨归的创作目的不同,且表现方法上也有异,更与屈原创作的骚体相类。因而,从文体功能角度而言,我们不妨把刘勰提到的“纪行述志”及《文选》赋类中“纪行、游览、志、哀伤、情”等几类一起归入“情志”类,似更妥贴。《文选》情志类赋作有纪游类如班彪《北征赋》、曹大家《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王粲《登楼赋》、支遁《游天台山赋》、鲍照《芜城赋》,物色类如潘岳《秋兴赋》,鸟兽赋如贾谊《鵩鸟赋》、祢衡《鹦鹉赋》、张华《鹪鹩赋》、鲍照《舞鹤赋》,志类如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张衡《归田赋》、潘岳《闲居赋》,哀伤类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向秀《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潘岳《寡妇赋》、江淹《恨赋》、江淹《别赋》,情类如曹植《洛神赋》等。这些作品或通过一段旅程的纪行如班彪《北征赋》,或通过特定地点的登高兴怀如王粲《登楼赋》,表达自身漂泊之感及所经之地的历史兴亡之叹;一些作品或临秋兴悲如潘岳《秋兴赋》,或托物寄寓如祢衡《鹦鹉赋》,或谈玄抒志如张衡《思玄赋》,或感叹人生易逝如陆机《叹逝赋》,或发生离死别之痛如江淹《别赋》、《恨赋》等,无不表现出作者面对社会动荡、人生挫折、生命迁逝时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具有很强的自我抒情的特色。与以讽颂为旨归的大赋与小赋有着不同的创作基调。
从以上对《文选》15门类所作的三大类的概括,我们不难体会到《文选》赋类分类标准,这些标准既构成《文选》赋类分类的特征,同时也呈现出既分难明的分类矛盾,体现了编选者的历史局限。
首先,《文选》赋类选文是以赋名篇的作品,这既是赋体作品汇聚一类的条件,也呈现出以篇名定体的局限。《文选》赋15类56篇作品,全部都有“赋”名,这不仅是赋类定体选文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文选》一部书其它体类共同遵循的选文标准。但是正如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的“古之诗者,今全以赋名”,作为古诗之流的“赋”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创作与发展,它不仅成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体,以致西方很难找到一种确切的文体与之对应,同时以赋名篇下的作品也呈现出体类芜杂的现象。以篇名定体是简单易行的,但是在文体意识尚处于萌生、发展与成熟的阶段,这样一种方法,会造成一定的混乱,在《文选》赋类中主要体现在骚、赋不分。稍早于萧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辟《辨骚》、《诠赋》专篇,在强调骚体作为“文之枢纽”重要性的同时,也限制了骚体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屈原及其追拟者的作品。而起自荀卿、宋玉的两汉以赋名篇的作品统统归入赋体范围。萧统编《文选》也依据这样的观念,分立赋、骚。骚类完全依汉代《楚辞》选择作品,除《离骚》等骚体作品外,还收入《卜居》、《渔父》等文赋,显然也未着意思考“骚”作为文体的外在体式特征的统一。赋类下“纪行”、“志”、“哀伤”等类一些作品,体式上又完全等同于骚体,实是以赋名篇的骚体。因而,《文选》的骚、赋分类一方面是以篇名定体,突显了屈原骚体的地位,这一点在他的《文选序》也有说明;另一方面,萧统与刘勰一样,表现出以篇名定体的局限。
其次,具体分类以题材为标准,虽简便易行,但又过于简单,反而遮蔽了具体作品的主要内容、创作意义及文体功能。如同一标题之下未必表现相似的主题,因而,细读各类文本会发现所次欠当。如卷一二“江海”类收入木华《海赋》和郭璞《江赋》,单从标题上看,归入一类,非常妥帖,但是《海赋》只是描绘了海的壮观,对大海进行歌颂性的描写,而郭璞《江赋》则托赋长江,有着为东晋王朝建都建康寻求一种地缘政治因素的创作动向。郭璞在东晋建立之际,不仅以他占卜特长为司马睿政权营造君权神授的合法地位,而且运用散体大赋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积极颂扬东晋王朝。《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如果徒以描写江海视之,就遮蔽了郭璞此赋托物言志的创作目的,而这一点是赋体最为主要的文体功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宫殿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何晏《景福殿赋》两篇,从描写上看具备大赋的特征,也具备颂讽的功能,却次于纪行、游览类之下,所次欠当。
第三,注重赋体颂美政教功能。萧统《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和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虽然萧统注意到赋体创作的时间先后,即时次的重要,但时次从属于类次,因而,能否在类次中反映赋体兴衰变迁,这是一个繁难的问题,也关涉到编选者能否从赋体客观发展出发考虑编排。《文选》赋前四类京都、郊祀、耕藉、畋猎,均与帝王政治文化相关,显然,萧统过于推崇体国经野的大赋,而又局限于标题分类,因而,使得赋类编排上未能反映出赋体的历史变化。如大赋按照“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的顺序排列,突出具有颂美意义的班固京都赋作的地位,而司马相如的大赋则在“畋猎”类中才出现,很显然没有注意到类次中时次重要。再如对宋玉赋的处理上,宋玉赋共选了4篇,一是物色类的《风赋》,二是最后一类情类中《高唐赋》、《神女赋》及《登徒子好色赋》。荀子、宋玉赋在赋体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刘勰《诠赋》已给予充分肯定。但一是由于篇名定体而使《文选》荀赋失收,二是对宋玉四篇赋未能充分认识到其托言讽谕的重要赋体功能,简单将之归于物色与情,其赋体特色及在赋体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另,在“情”类中未选曹植以下有关作品,未能重视南朝的小赋的新变。以上三个方面既是《文选》赋体分类标准,从其与《文心雕龙》的相似性来看,又体现出梁代分体方面特有的历史局限。
《文选》作为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其首立“赋”类,说明赋体在萧统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从赋学理论上看,萧统首立赋体,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学观念的认同以及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赋体创作与赋体批评并不是同步的,赋体创自荀、宋,赋体批评始自汉初。赋体托物言志的功能,要求赋体创作在描写与构思上有一定的虚构与夸饰,但又必须为讽颂创作目的服务,用扬雄的话说就是达到“丽以则”的完美效果。扬雄本着“丽以则”的批评准则,对大赋创作进行了“劝百讽一”的批判。东汉前期由于儒学地位的进步提升及统治者对作赋颂美的提倡,班固在不否定讽谏的前提下,着重建立赋体颂美的创作标准,强调“润色鸿业”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创作和批评上实现了大赋创作主旨从讽谏向颂美的转向。虽然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亦言“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只言片语中突出对赋体辞藻之“丽”与“体物”特征的推重。但是西晋赋论,尤其皇甫谧、挚虞与左思的赋论,却继承了班固观点,表现出推重颂美、反对浮词而取向征实的倾向,与曹丕为代表的辞丽派有别。南朝刘勰继承了皇甫谧等人的观点,如其《诠赋》把赋体的“丽词雅义”看作是“立赋之大体”,可以说,大赋有关“丽”与“则”对立统一关系的探讨与创作实践,是与赋体讽颂文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又一重要理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虽然萧统没有直接的针对赋体发表的言论,但是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言:“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对文辞文质彬彬的审美追求,颇与班固以来赋体创作与理论相吻合。萧统存赋七篇,即《殿赋》、《铜山博山香炉赋》、《扇赋》、《芙蓉赋》、《鹦鹉赋》、《蝉赋》,虽是残文,但也主要还是观物咏德,承继了荀子以来小赋创作的风格。周勋初先生在《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中指出,梁代文论存在着以萧纲等为代表的新变派、以裴子野等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以刘勰与萧统为代表的折中派(参见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赋体“丽”与“则”对立统一正是折中派最为欣赏的一种体类。可以说,既有文采同时又能兼顾儒学政教的社会功能,莫过于赋。这不仅是萧统,同时也是自班固始至南朝萧梁时代对赋体文学的主流看法,即赋体无疑既是一种美丽之文,同时又具有儒家所推崇的颂美讽谏的政教功能,是在辞与义上能够完美结合的一种文学体类。因而,萧统首立赋体,是由赋体特殊的文学与文化功能决定的,也体现了萧统对儒家诗学观的推崇。其次,我们应当看到,从编排体例上来看,萧统首立赋类受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同时也是唐前赋体创作的实际成就及时人对赋体的关注所决定的。最早对赋体进行分类的是班固,他依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编定《汉书?艺文志》,其中“诗赋略”,先赋后诗,赋类分“屈原赋类”、“荀卿赋类”、“陆贾赋类”及“杂赋类”四类,四类后列“歌诗类”。班固先赋后诗,一是由于“六艺略”中已有“诗经”一类,二是《诗经》之后,班固作“诗赋略”时,其所看到的文献只是“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都是汉代采集的乐府歌谣。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创作数量方面,赋体创作都远远超过歌诗。因此,班固先赋后诗,是战国秦汉诗赋创作的现状与成就决定的。两汉四百余年,许多大家染指辞赋,这种文体遂成一代之胜,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这一风尚在南朝虽有衰减而未断。且赋体有关帝王经国大业诸如京都、畋猎、郊祀、藉田等活动,史书多有载录。《史记》、《汉书》对司马相如、扬雄大赋的载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对班固《两都赋》等作品的载录。从《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著录可以看出,时至南朝,对赋体辑录越来越关注,如刘宋谢灵运辑《赋集》29卷,梁武帝有《历代赋》10卷,梁时还有《皇德瑞应赋颂》16卷、《杂赋》16卷等,这些都说明时至南朝,虽然文坛发生数次新变,但赋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可动摇,这也应是萧统《文选》首立赋类的重要原因。
萧统赋类以标题题材分类的方法,对后世赋类专集以及文集的编排都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部分所分屈原赋、荀卿赋、陆贾赋及杂赋四类,主要以人物归类,因大多篇什已佚及各类赋下所属人物较杂,所以很难判定班固归类的标准。萧统在赋体分类上首创以标题题材分类,虽然判诸实际,有历史局限已如上述,但是就文集编排方式上看,仍有其操作简易的特点,故为后世总集、赋集所取。如宋代《文苑英华》、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都是在《文选》赋体15门类基础之上,踵事增华,愈加繁复,但都基本上沿用以标题题材分类的格局而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可见《文选》赋体分类方法影响之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