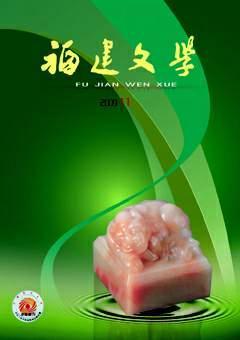丧失
黑 丰
终于,杨村长的儿子的岳父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2点50分撇下了他的独生女儿杨村长的儿媳妇,撇下了好不容易熬来的好日子便匆匆地踏上黄泉之路作寂寞远行了。杨村长儿子的岳父的仙逝,起初并没怎么引人注意,没有感到这世界少了或多了点什么。因为这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守恒的。要说多嘛,顶多只是感到本村某处的田野又多出了一个坟包。
这天早晨,太阳在8点20分以同样的强度和能见度穿过细叶水杉林的空间照在葫芦村小学校园那个菱形的花坛上。此刻老师们正在位于学校东北角的一间简陋的厨房里进餐,用以下咽的佐料仍然是一盘发黑的萝卜干,此外,灶台上摆满了的瓶瓶罐罐,像六月河花水涨上防汛堤站哨的民工。菜都是老师们从自家里带来的,不过菜的品种并不多。有腌萝卜烩萝卜炒萝卜,除了萝卜仍然是萝卜。有时也有带咸盐菜带鲊辣椒罐辣椒的,偶尔也有带咸鸭蛋的。但少。虽然这样大家并不感到生活艰苦,也没有感到生活的异样。只顾赶紧吃了饭好去上课。期中考试马上临近,老师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这场考试不仅可以掌握这半期的学习状况,同时也可预测期末可能的考试成绩。它既是学校把握教学状况的晴雨表,又是老师和学生中途的一个加油站。虽然是期中,镇教育组不组织统一考试、不排名次,但学校还是设了奖,自己跟自己以前对照是进步还是退步了。据说村领导也要这个结果做教师工资预算的参数。所以,教师们都忙,没有时间来想其他问题,没有时间来琢磨这村上死的人会与他们有什么瓜葛。人到了该放寿的天年,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有时也皱眉头,那是因为米饭里有大量的没有淘干净的沙子硌着了牙齿,或者看到了某某老师的小孩在厨房当门大便什么的。
不多一会,早课的铃声响了,人们像往常一样踩着同样的节奏去课堂上发挥萝卜干的干劲。
但是这一天,小豆老师的左眼总是跳个不停,无缘无故地跳了一下,又跳一下,他便感到了某种莫名的不安。一会,他看见一个人影晃进了学校,闪进了校长的办公室。接着,孙校长就急急忙忙夹着课本走了进来。整整一个上午,小豆都看见孙校长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晃荡……
大约13时45分,下午的第一节课上了不到一半,孙校长便当当当当当当当拉响了放学铃。放学铃与下课铃不同,很好听,放学铃是连续地敲击,下课铃是敲两下为一拍节。孙校长的铃敲得很嘹亮,嘹亮得听不出铃里的湿气与阴郁。许多老师精彩的讲解与发挥一下便被这嘹亮的铃声给葬送了。学生们似乎很振奋,尤其那些厌学的学生。教室里立即出现了一片小幅的动荡与响声。那些想上课的学生和老师情绪也马上出现震跌与不安。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今天的铃怎么这么打?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司铃的今天大脑注水了?一半的老师满腹狐疑或异外惊奇。有人在私下里猜测,这下有好戏看了:看!连铃都打不好,还不被校长骂得狗血喷头!也有一部分老师在惋惜这两节课,眼看期中考试就要来临,校长多次开会,几次三番地催促、强调,要抓紧一切有效时间上课,抓质量,要知道质量就是学校的生命,质量就是教师的立足之本,我们不是特级教师,我们的教学跟别人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只有靠时间和汗水,靠反复的对某些知识的强化和巩固来加深学生的印象和理解。在纪律上,我们更要高标准、严要求,谁也不得无故旷课,如果有谁置学校的名誉与个人的生存而不顾,随便缺勤无故旷课者,绝不饶恕!这话校长说得很严肃。在这里,在这距中心城市十分遥远的边陲民办学校,校长就像一个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是有威慑力的,谁也不敢不听。对于地位低下工作关系极不牢靠变动很大的民办教师来说,下课,就意味着到生产队像农民一样从事最苦的最脏的最没有尊严可言的体力劳动,意味着从地位本来就低下的民办教师沦落到更低下的境地。
说实在的,他们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并不一定认为教师就真有多么高尚,真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或发自内心有多么喜欢,完全出于一种无奈,四顾无门。因为当时社会并没有出台多少就业的岗位,四周到处还是一体化的集体经济。而且不准说不热爱,不准说不喜欢,说不热爱和不喜欢那与说反动话和写反动标语无本质上的区别。教书,虽然钱不多,但毕竟无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每年都可以从大队得到450—500的“飞拨工”。
不到放学放学铃就响了,几节课在嘹亮的铃声中无由地报销,对教师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未必一定感到特别可惜,尤其对于师资匮乏的民办学校,因为压在他们身上的课程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教师几乎可以包揽语数品自音体美劳等八门课程。几乎整整一天都泡在教室里,谈不上有一节课的喘息,谈不上有很充裕的备课时间,更谈不上进行教学研究活动。如果教师中有一人生病,有一人出差到镇上听公开课或有幸参加县里省里举办的教研课和观摩课,那么这个教师所任这个班的几节课就有可能无人上或改上“体育”。体育最好上,也最受学生欢迎。因为体育在生存和挣扎于底层的民校看来(非官方),有着特殊的味道,它就像一块冒油的肥肉。人们很愿意把无人经营或无法去上的课程变通为“肥肉”。一旦变成了肥肉,它的泡沫就大了,给人感觉也大异其趣。至于它为什么可以具有肥肉诱惑,它的最终解说和特殊的解释权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那个民校,在现在已然沉寂了的民师那里。
铃声很久地响着,响了一遍又响第二遍,一遍比一遍敲得急,一遍比一遍敲得狂,一遍比一遍敲得肆无忌惮,一遍比一遍敲得人心律不定……那铃声简直就像催命拿魂的无常。
人们开始由喜转忧,由喜转到一种深深的不安,由不安转而生出疑惧……人们也许预感了走出教室大门走到太阳底下会有一种难以料定的或阴谋的危险性的存在,颖悟到教室里可能是安宁的自足的……这样,那天下午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有点像灯泡,被铃声无辜地敲灭了,那些铆足了劲,备战初考的也被敲黯了。他们也许迟钝地感到了生活的荒诞或荒谬。
小豆老师由于有所准备所以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大惊小怪。在办公室里小豆有条不紊地干他的日常工作,但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孙校长脸上有一种神情(也许是某物)在晃荡。办公室里老师们才忽然记起了在整整一个上午教室的一侧(也即学校的北边),不绝如缕响起的成群的杂沓的脚步声和一晃而过的花圈。距学校不到100米远的北面就是一片坟场,那里已成了大队的一块不成文的村民公墓,几乎所有的死人都葬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丧事仪仗都要穿过学校的这条主路,绕田或干脆从主路下到学校操场然后从学校厨房与教室之狭缝穿过去。那时学校根本没有围墙,也没有建围墙的概念。当时中国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校还没有从广阔农村这所大学校的外延下,从人的意识领域到物质世界真正地脱离出来。所以,从教室里从寝室从操场从学校的任何一点望出去都可以望见生长着绿庄稼或丰收在望的田畴,可以望见农民在田里施肥、锄草、喷药、灌溉、收割的劳动场景。学校与外界四通八达,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或走近都无挂无碍。村里有一条主路就一直贯通学校直达东西,东边到达瓦河大堤,西边直抵暗寂的沉湖。所以红绿的花圈和嘹亮的唢呐没有不引人注意的,但由于死人的事情多了也就熟视无睹了,谁也没把这码事放在心上,人们都一心一意抓教学。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回这个死人是要与自己的经济、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关系的。这一次校长冒着组织的危险,冒着期中考试的炮火而不顾,牛劲十足地打铃,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然,那就白打了。
孙校长开始训话了。
孙校长说,这一次把大家召来是要到杨村长那里去一下。道理很简单,作为村里所管辖的一所学校,自己的父母官家中老了人,我们这些做子民的不去哀悼一下是不像话的。本来死者与我们毫不相干,可那是杨村长的亲家,丧事就是杨村长亲自操办的,那个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这个事我们就不能不管了。
大家开始叽叽喳喳……说去的有,说不去的有,沉寂着不发一言的也有。
小豆说,这个事我认为属于个人交往应在个人私事之列,老师说去,放了学就可以去。既不影响上课,也不影响吊唁,没有必要停课开会组织大家一起去的。再者,老师手头也紧张,你这么一组织一强调,老师们有压力……
没压力没压力,大家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的不勉强。我开个会没别的意思,一是告知大家一声,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二是体现了一个单位意思。孙校长说。
要体现单位意思很简单,学校买一个花圈一挂窝子鞭,你和刘出纳代表大家一起去,得了!小豆说。
大家如有不愿去的,我们不勉强……
我不想去!
……你不想去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勉强!孙校长说。
静寂!
办公室死一般的静寂!
……有一件事我必须严正地告诉大家,眼下正值期中,也是上半年给大家结算工资的有效时间,对各位的工作和工资的评定杨村长是要拿出主导性意见的……甚至包括在座的各位教师的岗位他也要拿出主导性的意见。大家都是明白人,希望不要在关键时刻犯糊涂,不要明白一世糊涂一刻……我宣布,今天下午的课就不上了,再忙也不在于这一刻。学校提供花圈和鞭炮,安排刘老师统一收资,集中上情,愿意去的可到刘老师那里登记,有困难的,跟刘老师……时间不早了!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孙校长说。
大家开始动了。
老师们心里还不明白,话都说到这步田地了?上情呗!……这情还能指望它回吗?这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老师们对杨村长领教还少吗?他常来学校,大家都知道杨村长的一个特别嗜好——就是有事没事喜欢往学校里钻。他说,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跑总能学到知识。他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向老师们学习!”所以他经常来学校“向老师们学习”。经常深入课堂,深入办公室,深入寝室,深入到老师们的备、教、辅、改,与老师们交心谈心。他比镇教育组负责教育教学工作指导的教研员和教育行政领导到来的次数还要频繁。所以,很多老师一听说他杨村长又“学习”来了,头就大了。他“学习”完之后还要吭哧吭哧地组织大家“交流心得”。有几个其实十分优秀的老师就是被他“交流”走的。他什么都不懂,不懂教育,所以“交流”一次,老师们就要起一身鸡皮疙瘩。可以想象作为一位学历不足高小的村长,成天呆在乡下,呆在庄稼地里,又没有到外地去走走、看看,又会“交流”出什么新的前卫的心得呢?平时,他还经常传个口信叫某某某某老师到他那里去一趟,他那里究竟是哪里?是教育机构教研室吗?不是。不过就是一个装了麦克风的空荡荡的村会议室。在那里他又能谈得出什么道道来呢?不过是把这些男男女女老师猥亵一顿罢了。他喜欢看一个老师在他面前像一只蝇或像一只蝉,他看着他们低吟或挣扎。
所以,在办公室里当孙校长一提起杨村长小豆便看见满屋的蝇嗡和蝉鸣。人们黑压压的头低垂着,没有人站出来说不的。
“好吧,大家都一言不发,想必没什么意见啦?刘老师,那就抓紧收了钱我们出发吧!”
奇怪得很,刚才大家还筛糠,刚才大家还气粗粗的有情绪,才几分钟就孩子一样兴高采烈起来;刚才还嘟嘟囔囔地叫穷的老师,仿佛一下得了宝物,顿时变得慷慨起来。小豆细致地看着人们这种微妙的变化,细致地感受着人情冷暖,结果他发现谁都比他富有,没有一个有困难的,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穷人……可是,怎么先前就一点迹象也看不见呢?仿佛他们本来就知道这个事儿,知道是杨村长的岳父,知道是杨村长料理后事,早就做了准备,其实他们在教室里本来也没有安心上课,一直心不在焉地在黑板上画着什么教着什么念着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做了些什么。他们甚至烦躁、焦虑直到铃声响了……铃声一遍又一遍地响了,人也到了办公室,可是谁也不愿先出头。装傻。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这时,孙校长也发了话,把钱拿出来吧!
这可苦了小豆!因为他基本长期过着书生生活,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一者他说了那样一番话,得罪了孙校长也间接地得罪了杨村长。他说了那样一番话杨村长会有不知情的吗?纵然孙校长从大局出发不说,个别老师也会说出去,这样一个有利于接近杨村长的好机会还不稍微利用下吗?刚才就已经看出来了,阵营一下子就清楚了,人们迅速地倒向了孙校长那边,自己马上被孤立起来,他似乎一下子与同事们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峙关系。二者他真是一个穷人。别人说没钱可能是假的,他说没钱就是真没钱,不像有些老师,口里说没钱,其实衣袋里有的是钱,只是不愿露富。小豆很多时候衣袋里是布贴布的,有的话也只是一些零票子……现在的格局已被小豆给弄僵了,就是别人肯借钱给他,他也不好意思去说了。因为他毕竟发表了“个人私事”的高论,所以他便坚定下来,做一回自己。
但在小豆回家的路上还是出现了一些低度的眩晕与低幅的恍惚。因为毕竟重量的绝大多数滑到天平的那一头,一种失衡感还是在内心里滋生了。不过还能把持住自己。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不站在绝大多数那一边是有害的,是要吃亏的,是另类,是要被驱逐或遭剪除的对象。人类的绝大多数并不喜欢对自己说不,不喜欢差异和叛逆……他知道老师们很圆滑很势利很见风使舵,没办法,环境造就出来的,不这样恐怕也无法生存。他知道老师们并不是真正的很有钱,兴高采烈或一言不发应该是有他们内心苦衷的,也许是一种假象。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从早餐他们呑咽黑萝卜干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状况。谁能想到一个很富有的职工愿意把浸了些酱汁的黑萝卜干吃得有滋有味、吃得香甜可口、吃得像在吃酱板鸭呢?他们的工资一年才450-500元,不足现代白领一次节假日所发的过节费呢!小豆后来终于奋斗出去,在广东一家文化艺术单位工作。他经常回顾这段艰难的日子,他能清楚地记起在厨屋进餐时吃黑萝卜干的情景。这些萝卜干是一个姓黎的女老师带来的,萝卜不大,盐腌制后用青篾穿了放在屋檐下风干,然后浸到辣酱里,待一定时日就可从坛中取出来吃。但是由于忙,放到檐下的萝卜干就像放入了记忆的深处,老是记不起收拾,风吹雨淋萝卜干就生出了一些黑霉斑。虽然几经刀刮,但斑迹依旧明显,主人舍不得扔,就储进了酱坛。带到学校,居然很受欢迎。小豆是吃过这些带黑霉斑的萝卜干的……他感到过去的日子就像一串串生满黑霉斑的萝卜干,满是皱纹地在眼前晃荡,一遍又一遍地像放幻灯片。当时的小豆就真切地感到了这晃荡的萝卜干的日子,这忧郁、沉闷、光照不足的日子,风雨一遍又一遍地涮在萝卜干上,黑霉斑在长黑霉斑在扩展,整个日子像萝卜一样生满了滑腻的涎水。可是这些吃黑萝卜干的穷教师,还得把自己再拧干一次,到杨村长那里交银子。一想到这小豆就恨!——那个死鬼算什么东西!他倒好,一了百了!现在正安安静静地躺在芦席上,躺在阴阳界上,享受着他的孝子贤孙送来的米酒、肉食和跪拜礼,交替出现在小豆眼前的还有孙校长与杨村长战友般会心的笑意与很响的咂酒声。小豆终于看清楚了一直没有看清的在孙校长脸上晃荡的东西,那可能是一种酒意或者酒的泡沫。从空中滴落下来的酒,从空中滴落下来的美意。酒杯已经盛满,但那美意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上面滴落,最后那美意与酒的泡沫涌溢到了孙校长的嘴角,然后又从嘴角滴落到孙的四口袋的中山服上。看来孙校长对于奔丧或吃丧户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倒像是做成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有必要庆贺庆贺!那时去一家作吊或吃喜酒,上一个人情一般是5-8元。看孙的样子,吃回这8元是不成什么问题的。领导一般可吃过几桌的连席,吃过三桌连席的都有。领导话多酒量大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三桌。领导在那里坐镇喝酒,主人还特别高兴,殷勤为客人斟酒加菜。小豆不行,小豆一不能喝酒,二不是领导,三不会说话。所以在世人的眼光中是一个没有特长的人。小豆的大姐就经常说小豆嘴笨,一句乖话都没有,死脑筋一个。小豆大姐还说你看人家×××老师,多会与领导处关系,把人家站着的说得坐着,坐着的说得站着……每每听得这话,小豆就一脸沮丧。对一个只读了三年级的大姐小豆又能说什么呢?小豆不仅不会说话,对于到丧户家吃饭从小就很有顾忌。想想餐桌就在丧棚的一旁,芦席上的尸体挺着胸脯,嘴里一阵阵冒着红色的泡沫与腐气,小豆就无法兴奋,怎么也举不起一双筷子去戳肉戳鱼的。再美的菜也吃不出味来。在他比较保守的观念里那夹着送到嘴里去反复咀嚼的鱼肉与嚼死人的腐尸无异。如那样的话,不仅小豆的8元钱,还有众多老师们的钱都无异于水上打漂漂了。如是水上打漂漂也倒好,因为打漂漂毕竟潇洒、美丽,倒也养眼。可是老师们拿了这8元人民币去打漂漂究竟能换来什么呢?村长是个痞子,校长是个老于世故的滑头。已历经三届校长的老出纳刘是个“雾满天”,是个永远把他看不懂看不透看不明白的经络纵横交错曲里拐弯的“雾满天”。这8元银子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交也白交。而且这吃不回来不仅有这8元人民币,还有这年终才能结算的工资550。至少有50近80元的现金要荒诞,要漆黑掉。每年年关也即大年三十都有教师在漆黑的夜里踩着沮丧的泥泞高一脚低一脚地到“雾满天”家里去,希望、侥幸与惶恐并存地喘着粗气心情复杂地敲开这个老出纳家的铁门,讨要那早已虚幻了缥缈了的工资余额,关系不错的,有村长杨的直接批条的或有校长孙的直接批条的可能要好办一些,或可兑现一部分了,但老出纳总是现银不足,他总是说:等到开春吧,你的这点钱不多,开了学第一个就把你的这点钱给兑了。这样你必须耐着性子等,等到初春,提上一些拜年物品……这事可望办成。所以,乖觉一点的老师当夜就提着礼品,当晚就兑现了余额。迟拜不如早拜。也有老师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以致卷铺盖走人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弄明白为什么单单就没有结清自己的那部分余额。最让人难堪的是到“雾满天”家与“雾满天”遭遇,“雾满天”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来看你,看你一路疲惫,看你一副穷酸,看你一身的落魄,看你一脸的无奈……他然后就把鄙夷一收,端出一副教训的架势,他的豆渣罐就开始了,他的那张婆婆嘴就咕嘟咕嘟滚开了。他指责你这件事过了,那件事犯糊涂……说得你恨不得去投江、钻地缝,说得你脑袋糨糊、心灰意冷……如是耳里灌满了他给你的糨糊给你的风,灌满了他给你的心灰意冷给你事业的诽谤,之后他再把余下银子给你全部兑现也不亏。问题是他把你教训完了,把你的精气神说没了,你还得怎么的来怎么的回去。他一点也没帮上什么没在你的经济上增添什么,反而削弱了你削弱了你活着的信心和力量,削弱了你的本来就很薄弱了的生存意志,进一步给你增加了思想负担,进一步给你本来就凉透了的身体吹来了一股更凉的凉风,他批评你不该花那么多冤枉钱买书,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你应该花一些时间跟老师们一起坐坐,跟领导搞好关系,你看你酒不喝烟不抽牌不打活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别人说话你也说不上一句,像一个呆子,典型的书呆子!人一生就那么回事,吃喝拉撒玩。你想当作家,当艺术家,当科学家……谁不想?你怕我不想?那是人人都能想得到的吗?你跟我一样,父母只给了你这么个天分,只给了你这么个条件,你家祖祖辈辈都是栽田的,你能一步登天?能保住民办教师这个饭碗就算烧高香了,你还想怎么着?指望坐飞机当总统啊?你只有那么个命,一切都是命,五庚八字命生存……你多大了?三十了,你以为你还小啊?有人说三十而立,立什么?立个鸡巴!那是你能立的吗?我跟你说,人到三十万事休,休是什么?休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人要知足,知足常乐,你像我就很知足,我跟你桂姐(“雾满天”媳妇)就培养这俩孩子,种几亩田喂几头母猪,经营好学校这个商店,每天早晨喝二两小酒长点酒膘,不像你们年轻人七想八想,脑壳都想破……不过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早点回头,找个媳妇,生个儿子好好地培养下一代,兴许下一代比你强……听了他那番话,你会格外伤感,你会感觉到书本与知识都一钱不值,他那种宿命的东西像一颗黑钉拴进你的脑子,叫你半天回不过气来。你就感到那最叫你骄傲,最叫你自豪,最叫你响亮,最叫你觉悟,最叫你活得自信与尊严的理论与价值观统统不值、狗屁不值……所以小豆每每看见“雾满天”,看见那张看起来很仁德看起来很厚道的猫脸就格外光火,看见“雾满天”猫脸上的那不长毛的阴弧碎嘴就会产生一个喷红而快活的愿望:痛痛快快地掌他几巴掌,再看他的反应怎么样……愈是资金紧缺愈是到了年关,愈是重返黑夜的泥泞地带,他的这个愿望就愈加强烈,像一粒跌落肥泥的古莲时刻等待着萌芽开花见红的那一刻……
然而,一直没有等到……老师们的作为让他很失望,尤其那天,他看见老师们乱云飞渡,本来对老师们就不存任何希望的他,当看到老师们作鸟兽散时竟然产生了一种虚茫的愤怒和仇恨,老师们在关键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一种奇特的一致、冷静与麻木让他感到寒冷感到可恨,比恨“雾满天”们更恨和愤懑。老师们的这种做派让他像踩在一团绵软的云气上一样,一下跌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他开始汗炸与孤独,他这才真正地体会到群众是什么,是一团乱污,一团秽气,一伙乌合之众,一群狗屁不值的东西,他们永远就那样,不可爱,不必对他们抱以过高的希望。
离开了他们,小豆推着自行车,慢慢,慢慢往回走,小豆老师永远也无法拭去他目光里浸染上的亘古的忧郁。毕竟他的那个本来就站在群众立场上的关于“个人私事”的讲话,没有感动在场的任何一个听众,包括黎老师等那些平素与他最要好的几个,没有赢得他们的哪怕只是半掌的响动,或是用空衣袖很空很羞涩地招摇一下。没有!什么也没有!更不用说巴掌的噼啪了。他们也曾私下对他嘀咕,但是现在风静云息……他们也曾扯他的衣角,问他究竟去还是不去,他们可以借钱给他去?他不记得当时自己如何对他们说,去耶非耶?也许终是不置一辞,他轻轻地也许是在想象中摆了摆头。悲哀的是他的姿态相反加速了老师们营垒的分化,加快了老师们的行动,他们残酷地往“岸”上跳,他们把沉沦把深渊把危险留给了别人,他们迅速地从窘迫的两层布之间掏出那些攒了多时也舍不得一用的花花绿绿的零票子,近乎讨好、下贱地走到“雾满天”跟前交钱……小豆的姿态使小豆仿佛一下子从潜在从书页翻动的宁静从暗寂的房间走到了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的一种光里。他在这种令人眼盲的白光得以淬火,他反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刚硬,以致对她们几近畏葸的劝慰和好意极为反感极不耐烦。小豆最终一意孤行。在离开之前,小豆想象自己在他们的注视下傲然骗腿而去,无数哆哆嗦嗦疑神疑鬼的目光撞着小豆轻猿般光溜的背脊滑下摔落跌碎。于是人们战战兢兢的对他复杂化的一个宿命的评估像噩耗又像一只凶残的狼在小豆要去的十字路口殷切地守候着他。
事实上小豆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仿佛走到了别人的太阳下,自己不是自己,自己是另一个人,自己在替别人活着。太阳很苍白,没有一点力。他感到了自己同样的无力。像一个赌徒,刚刚走下赌场……这时就有一支歌在咿呀地忧郁地唱。人们逃也似的从小豆的身边走散,仿佛小豆身上携带着一种绝命的瘟疫。檐影里有耳语声嘀嘀咕咕像一群嘤嘤嗡嗡的牛虻。那些曾经任由他自在沐浴甚而自在游泳的目光此刻也使小豆感到疲惫和陌生,犹如流浪在异乡。小豆真的如想象中那样迅速一骗腿上了自行车,他不愿让这些人看见一个硬汉男人的泪水。
……在道路拐弯的地方小豆心情复杂地慢下来,把车子支在一棵柳阴里,他无限伤感地目送着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此刻,他们正蹦蹦跳跳,手拉着手,肩靠着背,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趣事儿呢。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