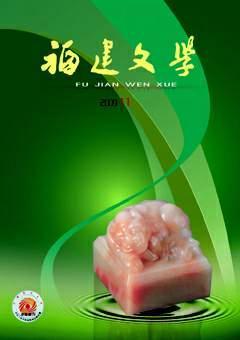我所遇见的一群人
黄金明
我没想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一踏进这个西南边陲的小餐馆,就看见了他。他望着我,目光炯炯。餐厅里空空荡荡,隔壁的一间小屋子挂着油腻的布帘,里面传出的鼻鼾声振动着门帘。他冲我招了招手,仿佛是我的老朋友,一直在等待我。我觉得他十分熟悉,但马上可以确定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感觉本身就是陌生而古怪的。他盯着我说:“我能理解你的想法。”我说:“我没有什么想法。”他说:“这儿的游客并不多,但我坚持认为开一间餐馆是必要的。”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他神情散漫,实在不像这个餐馆的老板,而像是一位内地的游客。他的目光锐利、清亮,仿佛穿透了我的心底,说:“我不算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我以前也喜欢在大地上漫游,像一朵云飘过旷野和天空。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主意。你先吃饭吧,如果你乐意,我可以跟你说说那件事。”
他挑起门帘走进去,将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拉出来。小伙子跟他面貌酷似,但年轻得多,看来是他的弟弟。小伙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趿着拖鞋走向伙房。
很快,小伙子就弄好了我要的两个菜。他又钻入厢房,一会儿就传出打雷般的鼻鼾声。老板看着我狼吞虎咽,蛮自信地说:“滋味还不错吧?”我点点头。老板开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给我,将另一瓶往嘴里倒。“我请你喝,”他说,“咱们聊聊吧。”
此刻,窗外阳光大盛,天空很高、很蓝。遥远的雪山像少女的乳尖,锐利、闪亮。而半山腰的岩石像一团灰云般混淆不清。我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停留在无垠而寂静的虚空之上,我依稀看见一只黑鸟飞快地掠过。但我不能肯定。
老板说:“在三十岁那年,我离开了娇妻和幼儿,踏上了通往远方的路途。我说不清离乡背井的原因,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寻找什么,但我确实听到了某种缥缈而真切的呼唤。尽管我不知道是谁在呼唤我,在哪儿呼唤我,要呼唤我到哪儿去。我搞不清这呼唤的确切意义,但我可以断定这个呼唤是真实的、有力的。总之,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我对在南方都市里过一个小职员的生活烦透了。即使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也无法阻止我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老板又开了一瓶啤酒,仰脖往喉咙里灌。他喝酒的速度,让我想起小时候用水去灌地下的蟋蟀。他望着我,诧异地问:“你不喝?”我歉然地摇了摇头。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
那只黑鸟又在天上出现了,像一支箭激射而出,又瞬间消失,我还没有看清它是一只乌鸦还是喜鹊,或者别的什么鸟。现在,我才留意到老板浑身漆黑,倒是衣襟上的一排白纽扣又大又亮,像闪光的银币。那身黑衣裳就像是黑鸟的羽毛,他垂下双手,仿佛鸟在合拢翅膀。我这个想法是毫无道理的,这让我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老板也看到了那只黑鸟,说:“太远了,你看不清楚。别看你瞧到的只是一个小黑点,其实它的翅膀伸展开来,怕有一两米。也许它就是大雕,或者传说中的鸿鹄,如果看清它的嘴脸,你会吓一跳的。”我说:“你说你改变了主意,那你是寻找到了想要的还是放弃了追寻?”
老板说:“不要着急。在一个细雨连绵的冬日,我来到东南的一个小城。我在街头遇见了一个潦倒的肖像画家。画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画好的几个样品,就放在他的脚下。画纸湿透了,但没泡烂,倒像白瓷一样闪光。画中的人像,仿佛全成了活人,表情栩栩如生。雨越下越密,街上没有什么人。雨水打湿了画家的脸庞,但他无动于衷。他啜下流入嘴角的雨水。他像一尾鱼。那些画像也像鱼头在水中摆动。
“我说,给我来一幅吧。那个画家的眼睛,就像火柴在磷纸上猛然擦亮。他目光单纯,又带着神秘,有点像鱼的目光。他说,你要寻找的是自由,但自由是难以描述的,更无法像抓小白鼠一样将它关入笼子。你离开你的家,就像鱼离开水域,登上了河岸。只有雨水,才会像镜面那样,映照出你愈来愈模糊的记忆。我摇头不答。这只是他的想法,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画家抽出一张白纸,那张纸马上被越来越密集的雨水覆盖了。他手上的炭笔在挥动,我的画像在水面上迅速而神奇地完成了。我的肖像,像一碗水中的倒影,或一面镜子里的虚像,清晰、逼真。我吃惊的倒不是这个,而是该画像尽管出自画家的手笔,但赫然是他的自画像,或干脆说就是他的映像。我惊诧之下,还没有领悟到其中的深意。我付了十元酬金,我拒绝将那幅湿淋淋却没有毁坏的画像带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看出了什么问题?至少我当时无动于衷。”
“你编的这个故事很不错,”我说,“但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
老板嘿嘿地笑了,继续说下去:“在一个云朵被落日烧红的夏日傍晚,我来到江南的一个小镇。我之前没来过这儿,但小镇的一切事物,都让我感到异常亲切而熟悉。那种熟悉的程度,就像一只在花香中迷失的黄蜂,又回到了枝叶掩映中的蜂巢。我在小镇的旧旅馆上遇到一个人,他清癯、健谈,却让人没有陌生之感。我觉得那个人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来。我一直怀疑他的黄色葛衣下面,隐藏着一对半透明的翅膀。它们单薄、轻巧,就像折骨伞的绸布。那对翅膀并不大,但足够使他飞上天空。我紧张地注视着他,唯恐他突然张开翅膀飞走。我担心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那种翅膀不像飞鸟的,也不像天使或神人的,倒有点类似昆虫的羽翼,譬如蝴蝶或黄蜂。我精神恍惚,觉得自己正陷身于一个骇异而逼真的梦境中。越来越浓的暮色,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我几乎忍不住要掀开他的衣服,察看他的两肋。在跟那个人喝光了两坛黄酒之后,一股强烈的睡意像洪水将我淹没了。
“我一直睡到翌日中午才醒过来,那个人充满怜悯地望着我,转身走了。我走到镇上去,我突然发现,街上没有汽车,室内没有电灯,整座小镇没有一件现代文明的产物。我所行走的分明是一座古镇。青砖灰墙的房屋一间挨着一间,密密匝匝,鱼鳞似的红瓦上,茅草在晃动。
“我走进一座院子,一个美妇人迎了出来。该妇人风姿绰约、白皙丰满,如果要用古代的美人来形容,显然非杨贵妃莫属。至少,那也得是唐朝的美人。妇人说,相公远道归来,历尽风尘之苦,待奴家好生服侍相公。我一愣,她显然是误会了,但这样的误会,傻瓜才会说穿呢。我随即想到,这不过是小姐扮成古代美人招徕生意的招数。我点点头,随她步入庭院。院中栽着几丛修竹,一束虞美人像火炬一样怒放,墙角的白玉兰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妇人端来一只盛满热水的铜盆。她将我的鞋袜脱掉,那双在我脚上移动的手,细嫩、滑腻,让我舒服极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男人,通过这样的一双手,可以推测妇人的好处。果然,夜晚里妇人的温存无与伦比。
“我枕在妇人的双乳间沉沉睡去,进入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在梦里,我成了一个巨人,就睡在两座椎体状的白色山峰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山峰不是真正的山峰,我也不是真正的巨人。我离醒来还远着呢。说是梦吧,但那种空气稀薄、近乎窒息的感觉是无比真切的。我变成了一只黄蜂,不幸的是,一个孩子把我抓住了,并捏住我的翅膀。我就像一个被警察反剪双手、拧向背部的犯人,动弹不得。
“一种极度的恐惧攫住了我。我终于惊醒过来。窗外晨曦柔和,红霞正在被无数道白光驱散。我居然睡了一宿。我抚着妇人白嫩滑溜的背部说,但愿你真是我娘子。你的老板很有创意。妇人拭着我额角的汗滴,答非所问地说,你太疲倦了,那只是一个噩梦,醒过来就好了。我说,我得走啦,埋单吧。妇人笑着说,你回到家里,就出不去了。我不理她,扔下两百元,抬腿就走。然而,门口外面的小径,通向的是另外一座庭院。与其说我是走出这一座院子,毋宁说是迈入到另一座院子。我不禁汗毛倒竖。我飞快地一连穿过七座彼此相似的庭院,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口,也看不到一个人。
“我陷入了一个由无数座庭院组成的巨大迷宫之中,精疲力竭地停下来。我双腿发软,冷汗涔涔。那个妇人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说,你注定要陪我一辈子的,你走不了。我感到天旋地转,那些院子仿佛也跟着我的脚步在转动。我被这些房子囚禁了。我意识到我像一匹小马陷入了梦幻般的泥沼之中,而我再也无法醒过来。此刻我十分清醒,我知道。我完全脱离了睡眠,阳光刺痛了我的复眼。那个梦境十分荒唐,按理说,一只黄蜂是无法做梦的,在梦中,我是一个来自现代的年轻人,并在一座古代小镇或仿古建筑群中寻欢作乐,碰上了销魂而恐怖的艳遇。在那个匪夷所思的梦境里,被一座座庭院组成的迷宫困住了,无法逃生。而在现实中,我不过是一只工蜂,每天清晨,在六角形的蜂房中振翅飞出,在山坡上的野花丛和桉树杈上的大蜂巢之间来回奔波。我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一个孩子捏住翅膀把我塞入玻璃瓶中,并正在旋紧塑料瓶盖。
“我终于完全清醒过来,我将那个缠绕在身上的梦境像蝉蜕一样抛掉。那些重重叠叠的梦境,就像那无数座庭院一样,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黄昏的夕光,像一只灰鹤啄上我的鼻子。那个人笑眯眯地望着我,桌子上倾倒着盛装黄酒的坛子。他手里拿着一只玻璃圆球,但光滑透明的球体表面,却从内部呈现出无数个拼接在一起的六角形的、蜂窝状的图案。我有理由认为,那个圆球正是使我饱受折磨的罪魁祸首。但他说,不是的,这完全是你喝多了。你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我不知道,我到底从梦境中脱身了没有。我凝望着他,一股寒意像蛇窜上脊背。借助圆球的反射,我发现我的面目跟他何其相似。只是他垂垂老矣,额头上的皱纹像水波在荡漾,而我则年轻力壮。”
我没有吱声。老板说:“你好像不信我说的。”我说:“你的确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老板苦笑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说的全是事实,我发誓我并无半句虚言。”我说:“你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老板说:“在开餐馆之前,我跟你干的是同一个行当。”我问道:“你老婆是不是也很像杨贵妃?”老板咧嘴笑了,说:“我老婆更像巩俐。”我说:“她还在家乡吗?”老板说:“也许吧。我后来没有见过她。”我又问:“那你孩子呢?几岁了?”老板说:“快七岁了,后来也没见过。”我默然不语。老板说:“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孩子,他很像我的儿子。他当然不是。”
忽然,一只黑鸟扑过来,像一颗石头投掷在碗盘狼藉的餐桌上。它伸着嘴喙去啜饮盘上的残汤,看来一点也不怕人。我终于看清了,它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只黑鸟,确凿无疑是一只乌鸦。我冲着老板笑了笑。老板尴尬地挥手去驱赶它,它才振翅飞走。
老板说:“多年以来,我在各地游荡而一无所获,我麻木了。我几乎忘记了我出门远行的目的,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听到什么该死的召唤或启示,而实质上是在逃避那些让我厌烦或恐惧的东西,譬如女人,譬如家庭等等。我心底有一个声音愈来愈清晰:你要寻找的东西不存在,而你要逃避的却如影随形。这个声音占据了我的头脑,在我的身体里盘旋。它是一只鸟。我成了一个鸟巢。我携带着这只鸟,烦躁不安。它似乎要伴我到天涯海角,一直到地老天荒。直到前年,我遇到了那个渔夫的孩子,才知道我错了。那只鸟是不存在的,连一根羽毛也没有。我的漫游一无所获,但并非全无意义。
“我是在深秋踏上那个南方之南的海岛的。岛上仍炎热如盛夏,微风中吹送着海水的气息和菠萝蜜的浓香。那些穿着长裙露出美腿的年轻女子,像色彩斑斓的大蝴蝶在海滩或椰林间飘然而过。我在海滩上闲逛,远眺着洁白的沙滩和深蓝的海面,这几年来的往事,就像波涛在不停地涌动,或者水面上的海鸥在盘旋。我深感人渺小如水滴,但一个人的命运依然像大海那样深邃和神秘。水的自由在于流动,所有水滴都渴望汇聚在一起并触及那深刻的源泉,即使冷漠的沙子也紧抱成一团。而人呢?我几乎说服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奔波劳碌,只是为了知道我是谁。
“我凝望着起伏如丝绸的波涛,几乎有了写诗的冲动。忽然,我感到脸上很不自在,那是一种被人盯视的感觉。那目光是如此炽烈,像火焰在吹拂。我低下头,看到了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和他抱着的大鱼干。那具鱼干长逾一米,就像一具沉重的飞机模型。刚才盯着我的有两对眼睛。一对是孩子的,另一对是鱼的。我明白那两对眼睛背后的渴望,但我不需要这具鱼干。我从不做饭,也没有朋友可以相赠。我奇怪的是,那具鱼干分明没有了水分,却仍能发出海水般深蓝、让人心颤的目光。孩子不说话,执拗地望着我。
“我快步离开,孩子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不耐烦了,说,你跟着我也没用,我不会要它的。孩子开腔了,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但你似乎忘了。我当时惊诧于他说话的腔调如此老成,而对其话语的深意没有察觉。我怒恼地嚷道,我不会买下这尾鱼的,我一见到鱼干就反胃。我童年时吃过太多鱼干了,现在看到鱼干,就像看到噩梦中的鬼怪。我在前面走,孩子在后头跟。孩子忽然说‘到了。
“我如梦初醒,看到海边的土坡上有一座茅寮。好像不是孩子跟着我走,而是他巧妙又不易察觉地将我带到了茅寮门前。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将一群鹅赶回家的。我不由自主地跟他走进去。孩子充满热忱地望着我,说,先生,我们需要三百元看病,你能帮这个忙。而我们唯一值钱的就是这尾鱼。房子里一片漆黑,透过墙缝中射入的光线,我看见木床上睡着一个老人,他神色憔悴,脸孔苍白,在不断地喘气。我伸手去摸他的额头,烫如火炭。我朝孩子说,他是你爸爸?孩子说,不是的。我说,你们看上去很像。孩子说,我们在等钱看病呢。我掏出三百元,还帮孩子叫了大夫。折腾到傍晚,老人才有所好转。
“我端着那具大鱼干,跑到海滩上叫卖。我有非要卖掉它不可的冲动。孩子跟着我。我们坐在一棵弯垂如弓的椰树上,落日像烧红的圆铁盘,眼看着就要急速地沉入大海。有个女人牵着一只卷毛狗走过来,说,那孩子长得跟爸真像。她像在跟那只狗说话,但狗不理她。孩子说,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就是父子俩,其实不是的。那只狗也不是狗,至少在那女人的眼里不是。我瞧了瞧他的眼睛,又望了望鱼干的眼睛,孩子的眼睛像海水一样幽深而湛蓝,而鱼眼的火花早已熄灭。我想起了出门远行的初衷以及这几年来的遭遇,无数件往事,就像白色的浪花在波涛上盛开和破碎。金色的霞光映照着孩子的脸,他目光炯炯,脸蛋儿像天使一样美,仿佛被晚霞镶上了金边。我握着孩子的手,说,谢谢你。
“今天我才晓得,我既不是要追求所谓的幸福,也不是要避免痛苦,而是对多年来的一成不变心生厌倦。我到处游荡,不需要任何回报和好处。同理,我也无惧于利诱和恫吓。我不指望一个老大罩着我,哪怕他是上帝,我也没想过做别人的救世主。我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人无法代理。事实上,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天堂和地狱——”
我打断他说:“用不着长篇大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认为你的生活死水一潭,你要的是打破预先设定的秩序,而不管其是好是坏。”老板说:“不是的。我曾经有过你这样的想法,但如今我发现命运的链条,自有其不可揣测并不容打破的法则。我曾无意中听到神秘源泉的呼唤,我花了无数光阴去追寻它。它来自整体。我的愿望就是触及这个神秘,别无他求。”我高声说:“你这种悲观的论调,不配使用‘追寻这个词。”老板坚持说:“除了对神秘本身的肯定,我对一切持怀疑论的态度。”我说:“你的怀疑论不足道。那个孩子后来呢?”老板说:“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
忽然,一个巨形物体从天上飞过,穿过云端,老板惊喜地大叫:“大雕,我说就是大雕嘛。”我没看清楚,惶恐地说:“那是飞机吧?”老板说:“你有没有见过黑色的飞机?”我摇了摇头。老板得意地说:“你刚才听见飞机的轰鸣了吗?如果是飞机,飞得这么低,肯定有响声的。”我说:“就是呀,我听见飞机引擎发动的轰响。”老板生气地说:“哪有的事!”
我懒得跟他争论。他想了想,说:“你似乎一直没有看出问题的症结。看来,我讲得口干舌燥,全是白搭了。”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又端起酒瓶子往喉咙里灌,这已经是第三瓶了。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他说:“我只好将我遇到一群人的事情讲出来了。就是这件事使我厌倦了多年来固执的、盲目的漫游。你一定要耐心听我说完这件事——”他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像兴奋又像恐惧。他的声音有点喑哑,我注意到他拿着啤酒瓶的手在颤抖——
那一个夏天,某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我去了一生中去过的最远的北方。一阵大风吹起,我在恍惚之中,跟一群人在草叶吹拂的辽阔旷野上相遇,猝不及防。那些人或惊诧或麻木地望着我。他们高矮不一,但脸孔彼此相似。为首者骑着高头大马。前面是马夫,后面是侍从。他衣冠华美,腰挎宝剑,看来是一个大人物。他盯着我,似笑非笑。我目瞪口呆,跟他就像两面虚空的镜子,从对方的脸上窥见了自己。
在刹那间,我脑海里飞快地掠过那个潦倒的画师、手捧圆球的老者和卖鱼干的孩子,他们是同一个人。我知道我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神秘。我撞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无法解释的。但我很快就从惊惶中镇定下来。我知道,越是容易犯迷糊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清醒。我思忖:“他是梦想中的我,还是主体的我?而那些随从,不过是一些较为次要的我。”大人物仿佛猜出我的心思,微微一笑,说:“我是某个时刻的你,你也不是你自己。你自己大于我们的总和,如果这个变幻莫测的背景可以忽略不计的话。”我瞅着四周,这巨大的背景,由天空、大地及草木构成,也许还有看不见的风及空气。蒲公英像缩微的云絮,在草叶上飘飞,几根鸟的羽毛从云中掉落。
大人物的坐骑凝望着我。他说:“这匹马也曾经是你,但只限于局部。去年春天,我在不周山遭遇一头半人半马怪。他使用尧时代的语言,说他是某个时刻的我。我见过女娲修补之前的天空,也见过大禹治理之前的黄河,但我还是被吓了一跳。”我忽然发现,队伍之中,有两个人推着一辆囚车,推车的人跟被囚禁的人,具有同样的脸庞,而神情迥然不同。大人物看到了我的疑虑,说:“他是一个反叛者。他妄图逃离作为整体的我们,然而他身体的另一半灵魂出卖了他。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他的拯救。”囚徒比我年轻,他凝视着我,嘴角带着轻微的嘲讽,他的目光蕴藏着无限深邃的波涛,又仿佛什么也没有透露。
我望着这一群人,一声不吭。他们分享着我的姓名和灵魂,却具有不同的身体和影子。我看到一个孩子,他脸色苍白,像一株羸弱的雏菊,死神的巨翅曾多次掠过他的身躯。大人物说:“他是我们的童年,他为了通向我或你,走过了每一条道路。而每一条道路,都会将他塑造成另一个人。幸好,尽管他多次误入歧途,但并没有迷失。”孩子忽然大声说:“我不想成为你,我还没有停滞,也没有被固定。我可以到达的那个人,仍在我的身躯中孕育和生长。”
一个中年人走出来,满脸欣慰:“我虽然头脑迟钝,大腹便便,但总算在最微小的地方,摆脱了最高意志的控制。”一个老人懊恼地说:“都是你不争气,我才落到这般田地。我依然没有完成自己,而我已油尽灯枯。”我好奇地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在年轻时代,我在大地上漫游,我做过水手、小贩和捕快。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想成为诗人。现在,墨水只剩下一滴,而我还没有写下时光的奥秘——”
大人物粗暴地打断他:“狗日的,快闭嘴——”他扭头对我说:“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只有专注和持恒,才可能实现理想。譬如一棵橡树,它要成为巨木,就只有抛弃细枝末节——像那种想入非非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家伙,他跟随我走过同样的道路,如今却妄想跟我分庭抗礼——”大人物扬起马鞭,狠狠地抽打着囚徒,鲜血像火花从囚徒的脸上溅起。大人物冷酷地说:“无论是哪一棵树,都不能有两株树干。否则只有一种下场。”
囚徒对着我微笑,仿佛在说:“你看到了吧。”我问:“他将要被押向何方?”大人物侃侃而谈:“对不觉悟的人,就去教育他,改造他。对不服从的人,就去压抑他,削弱他,必要时铲除他,消灭他。至于这个家伙么,他有麻烦了,我要把他押上京城,让皇帝看看他忤逆的嘴脸和卑贱的骨头,然后施以极刑。”我愈发惊诧:“谁是皇帝?”大人物回答:“皇帝就是我们的整体,是我们的最高意志。他是抽象意义上的每一个我,而又抛弃了那无关紧要的每一个人的个性。”
我凝神细看,只见队伍之中,有一辆马车运载着大堆白色或青色的巨石。车上有人持着锤子和刻刀在敲打。我看见一个人的五官和毛发,从石头上缓慢地长出,但更多的还没有成形。完成的石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从车上走下来,汇入越来越壮大的队伍。我几乎脱口而出:“我从何而来?我要到哪儿去?我是否来自一块石头?来自一把锋利的刻刀?”但我最终没有张口。
大人物说:“那些雕像不是真实的人,而是梦想的产物。尽管我们认为梦想不值一提,但我们并不排斥,更不禁锢。当然,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得经过检察机关的许可。”我疑惑地问:“你带着你的队伍,带着石头以及石头里的雕像,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你看上去鹤立鸡群,跟他们并不一样。”大人物笑了,说:“你很敏锐。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整体,但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总得有人去指挥,有人去干活……”
人群中有一个年纪与其相仿的人走出来,厉声说:“我早已厌倦了赶车和凿石。为什么你从不劳动,而我却拼死累活!”大人物勃然变色,用鞭梢一指,马上冲过来几条凶神恶煞的大汉,将他四脚攒起,捆成一团,掷入一辆囚车。大人物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总是随身带着囚车,以备不时之需,但有时囚车不够用,只好就地正法。”我惶惑地问:“这也是皇帝的旨意吗?”大人物举着剑说:“我的旨意,就是皇帝的旨意。”
天上,一朵灰云在扩大。它像一个碍眼的补丁,使晃动着蓝色丝绸和白色棉团的天空变得灰暗。更多的乌云在迅速地聚拢,像全世界的乌鸦集中在一起。年轻囚徒的眼中滚过一连串雷霆。大人物说:“我本来孤身一人。在漫长而艰辛的路途中,首先遇见了我的马,然后遇到了我的马夫。沿途之中,不断有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你不想加入吗?”
我绕着队伍走了一圈,我在人群中反复寻找我想成为的那个人而一无所获。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他们肯定不是。天空不断堆高的乌云,仿佛给天空穿上了一件威严的黑色大氅。在塌陷的乌云之中,显现出闪电纤小而耀眼的道路。我看到一个巨人,在闪电的钢丝绳上行走。他巨大的身影,几乎遮蔽了天空。他的脸仿佛从我们所有人的脸中跃出,但显然更加完美、神秘和冷峻。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我知道我穷尽毕生之力,也不可能成为他,甚至不能接近他。既然如此,成为什么样的人,已无足轻重。但眼前的这个人群,尤其是那个飞扬跋扈的大人物,却让我有一种又想哭又想笑的感觉。
我壮起胆子,坚定地对着大人物摇了摇头。大人物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你会后悔的。”他不再理我,扬起马鞭往前一指。这群人像轻烟在风中吹散,瞬间不见踪影,就像狂风卷走了尘埃和草屑。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坐在地上双眼发直,半天没有回过神。仿佛这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逐渐变得幽暗的天空、地上深刻的车辙以及路上撒落的碎石屑,让我在惊疑中不敢否定。
老板终于说完了那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汗如浆出,虚脱般瘫软在椅子上。他说:“就是这件事情,使我决定结束在大地上的漫游。”我说:“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开了这个餐馆?”老板望着我,笑了笑,一本正经地说:“就是为了你。”
他冲着厢房大喊了一声。那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睡意未消,但还是一骨碌就起床了。他用手端着一面大镜子,站在我的面前。他嘻嘻笑着说:“不用看也知道你跟老板是双胞胎,你看那个鼻子,那对眼睛,就像是克隆人一样!”老板不理他,把脸凑过来,冲着我说:“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什么?”我感到心烦意乱,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老板说:“看到了吧?这是两只大鸟的脑袋,一模一样的鸟。”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和惊恐,终于猛地张开了眼睛。镜中的画面好在还是人脸,而不是什么怪鸟的脑袋。那两张人脸的确有几分相像,我只觉得头脑“嗡”地一声轰响,仿佛有一架飞机或一只大鸟正在穿过我的脑海,消逝于脑海中无垠的天际。我头痛欲裂,精神恍惚。我宛若身处梦境,双臂张开来,身子轻飘飘的,眼看就要像鸟一样飞起来。
我狠狠地掐了一把大腿,使自己稍微清醒,又凝神去看那面镜子,老板一张瘦长的马脸咧嘴笑着,神经兮兮的,跟我肥大的圆脸风马牛不相及!世上哪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我笑了。这种想法本身就何其荒唐!我惊疑不定,不敢再看了。我一个箭步跑出餐馆,夺路而逃。我宁愿马上将这个餐馆、老板、伙计以及该死的一切遗忘!我跟自己大声说,老板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责任编辑 杨庆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