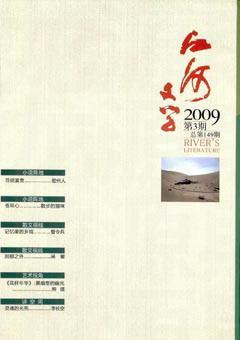雪祭
王小虎
一
其实他的造型的确雷人,枯黄色的头发上还有几根草把儿,象是刚从草地里钻出来的。穿着一件肮脏破旧的大衣,肩膀上露出暗黑色的棉絮。一双被劣质烟草熏得有些枯萎的眼神,偶尔转动一下,象是思考一个久远的人生命题。我不能想象,他竟是曾在北京混得人模狗样,曾经名声赫起的某电视台编导。
他在黑夜里拣起一只烟,在通红的炉火上点燃,抽一口吐一个。剧烈的咳嗽让他不时费劲的耸起肩膀,象扇动一双瘦弱的翅膀。
其实我很久没有给人讲故事了,雷人说,我觉得只有兄弟你可以帮我写。我望着空旷的庭院,再望望眼前这个一下子变得陌生而又曾经熟悉无比的雷人,心在无限地沉下去,象沉进一个永远也到达不了底部的井。
前不久刚落了场雪,我从南方匆匆赶回北方,似乎就为了和这场长夜行军的洁白约会。堆堆残雪到底使我有了倾听的勇气,于是更有了下面雷人的文字。
二
从审讯室出来,我调整了一下手铐的位置。抬起头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一个女犯正被管教押着走过来。她戴着笨重的脚镣,走起路来很吃力,哐铛的脚镣在那个初冬的黄昏动人心魄。她和我擦肩而过,粉红色毛衣上散发着肥皂的芬芳。我注视她的背影,若有所思。就在她走进审讯室的一刹那,她一直低着的头突然抬了起来,竟然下意识的回头一瞥。那是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流露着高雅忧伤的气质。额头上的刘海在风中如狂乱的垂柳。衬托着她的清秀与文静,一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闪烁着渴望与人倾诉的眼神。
我的心一动。屁股上随后挨了看守一脚。我乖乖地往回走,重新回到仅仅十几平米却容纳着三十几号人的监舍。
“喂,磁县,有景儿没有?”大烟刘呲着一嘴黄牙凑上来。他是贩毒进来的,对女人也象抽大烟一样有瘾。每当提审的出去,回来他总要盘根究底地问下有没有见到女人。如果有景儿。就垂涎着听,象一匹很久没有吃到肉的饿狼。
“你他妈的就知道泡妞。”号长大张不耐烦地骂大烟刘,“有一天把你扔进女号一晚上,让你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全号的人都大笑起来。
“货呢?”他把手朝我眼前一伸。
我从口袋里抠出几个烟屁给他,他把过滤嘴掐掉,把烟丝挤出来,开始卷他的烟。不一会。号里就缭绕起了呛人的烟味儿。
高高的小天窗镶着块苍茫的夜空,也镶进我的沉思。在没有女人的世界里,情感日渐稀释,只有等待命运裁决之前的那种恐惧和惶惑。天天推算自己可能被判几年,猜测1000次,又否定1000次。而审讯室前那女人的惊鸿一瞥,给原本简单枯燥的日子注入了一抹欣幸,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悲哀又把这一点欣幸挤兑走,那个温馨的情节稍纵即逝,残酷的世界不接受任何浪漫。
在雷人的叙述中,我看到那个初冬的夜晚落了一场雪,小小的天窗外雪花在凌空飞舞。一向喧闹的监号格外沉寂,三十个左右失去自由的人在兀自想着心事。
我还看见雷人蜷缩起身子,在号舍的转角处用长长的指甲划了第四十九道,这意味着他在看守所已经度过了一个半月的囚禁时光。我似乎还听到铁门的撞击,这样一次次的撞击让许多人都面如死灰。
三
兄弟,给我支烟抽吧。
我把从南方带过来走私的南洋兄弟出产的红双喜递给雷人。
雷人狠狠地抽了几口,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后。他开始重新叙述故事……
记得是周五,照例要放风,照例要经过女监号。经过女监号时,所有的男犯都显得躁动不安。眼神不安分地往女监舍溜,恨不得把所有的女犯一览无余。放不放风已经无所谓,只要能见一眼女人,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也能成为号房里最热烈的话题。
“嘿,那妞真靓,还一个劲的朝我瞅,感情也憋坏了。”马猴儿回味不已,他是因为酒后猥亵幼女进来的,对女人念念不忘。
“要是把我关进女号一天,枪毙我都值了。”“红歌星”咂咂嘴。这个有着歌唱天赋的小伙子,却鬼使神差迷恋上偷盗,此刻却浮想联翩。
这时,即使再丑陋的女人,也会给监舍带来沸腾的气氛。
又一天,我们出去放风。路过女号时正好清监,十几个女犯贴墙站着。监舍男犯人谁都不肯放过这天赐良机,用那仿佛能使女犯怀孕的目光贪婪地观赏着这难得的风景。女犯们或低眉顺眼,或迎接挑战。只有一个例外,旁若无人,美丽的脸庞上依然凝结着雷打不动的忧伤。我的心一动,是“红毛衣”。她戴着镣铐,刘海凌乱。乌黑的大眼睛有些呆滞,一缕阳光从窗外射人,映在她苍白的脸上。一股同情和怜悯使得我的脚步有些踉跄。我杜撰了许多和她有牵连的故事,但破落的心情都终使故事以悲剧谢幕。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位置,顾影自怜。兄弟,你知道吗?在放风场,我看到了雪,有限的空间被意念放大。我彷徨在厚厚的积雪上。却耽心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命运。我突然被这种愚蠢的想法苦恼不已,接下来就是渴望女友秦袭能来看我,哪怕是最后一次。
半个多小时的放风时间过去。我们重新要回到笼子里去。路过走廊,看见清监之后的女犯人正鱼贯而人。我心猿意马地望了“红毛衣”一眼,擦肩而过时。完全是潜意识的,我竟悄悄地说了一句话。“想开点。”我说,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她闪身而过,留下一阵熟悉的肥皂的芬芳。我突然有些后悔,为自己的莽撞和不合时宜的自我多情。但好在似乎她没有听到,因为她一直没有回头。然而,在她脚快迈进监舍的一瞬,她回了头,向我投过一个苍白却不失真诚的微笑,然后就消逝了。
我有些愕然。
四
兄弟,你永远不知道度日如年这样的感觉,感觉人的身体被抽空了,只有灵魂孤独的喘息着。
雷人苦笑下说,我在转角处划到100多道痕时,秦袭仍没有出现,我开始慢慢的绝望。我努力不再想高墙外的世界,每天只是把一些过了期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借以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并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那一天,监舍的门轰然洞开,管教人员和两名持枪的武警出现在门口。他们叫我的名字。我知道法院提审的时间到了。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其他犯人。上囚车时,管教把我和另一个人铐在一起。在初冬的严寒中我无精打采地抬起头,于是看见了那双熟悉的眼睛。她也正瞅着我,眼神里竟闪着些许亮色。我们都被着偶然邂逅感动着。
气氛是悲哀的,但默契蕴藏在空气里,多少给这次命运未明的判决带来了一线生机。
我们在窄窄的橡皮凳子上坐着,肥皂的芬芳一直朝我鼻子里钻。我能感受到她的心跳。
颠簸的囚车使我们的手碰到一起。她的手指冰凉。和白皙修长的手指毫不对称。我们彼此感受对方的体温。她一缕刘海甚至不经意划过我的脸,感觉电光火石般地交流着,让我心惊肉跳。旁边是持枪的武警,我们不敢交谈,于是心照不宣地把视野移向窗外。
城市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晨光静静地撒在楼群和人群当中。灯笼、花柱、十字路口巨大的宣传画,还残留着庆祝祖国五十五岁生
日的痕迹。车水马龙,让人们融在生活的河里,没有人理会一辆囚车正驶过身边,只是机械地在警笛声中放慢车速。
那时她收回目光,有些茫然。脚镣在车厢里咣地一下。我回过头,用无限同情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她是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的女孩,似乎一瞬间读懂了我的祈祷。同时腾出一只手,悄悄地捏去我肩膀上一个小小的线头。这个属于女人的细腻的动作让我温暖如春。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偷偷地在她的手心里写下了两个字“保重”。她看明白了,但随后摇摇头,然后在我的掌心用力写了一个字。看着那沉重的笔划我开始战栗。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这样的场合只能保持沉默。望着她的脚镣,我的心在一点点儿地往下沉。我抓住了她的手,两只戴手铐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慢慢地,我感到那只冰凉的手有了热度。
到了法院门口,下了车,管教给我们打开手铐时,我们才松了手。管教有些惊讶,但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一级台阶,回过头,我发现她美丽的大服睛里储满泪光。我的心一酸。掌心里的那个字烙着我的心。我不知道一个年轻鲜活美丽的女人会和这样一个字连在一起。
你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提审时,法警叫她的名字,没听清全名,我只知道最后一个字。叫雪儿。
五
兄弟,故事还没结束。
雷人又叼上了一根红双喜……
从同监舍的兄弟们得知,雪儿原是首师大的一名大学生。假期被人贩子骗到云南,受尽屈辱。最后终于逃脱,开始走上复仇之路。在茫茫京华她居然真的找到了仇人,并趁其不备杀了他,然后投案自首。然而她的血性却让她生命的华章从此灰黄。想起囚车上那只冰冷的手,想起那不设防的温暖一握。我竟有一种和那个叫雪儿的女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相逢竟是囹圄,这真是人生一种善意的嘲讽。
元旦马上就要到了,为稳定监舍犯人情绪,看守所发起了《一封家书》活动。优秀的家书将择优通过广播向所有在押犯人播送,从而激发这些人的改造热情。
号长极力怂恿我参加,因为他知道我喝过不少墨水,央视上一些稿件也出自我的手笔,理应首当其冲。我眼前一直晃动着一张美丽忧伤的脸庞,脚镣声在梦里彻夜哗响。我有了给她写信的冲动。于是我趴在潮湿的木板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飘起雪花,落在静悄悄的防风场上。那双涌满泪水的眼。此刻竟然如此让我眷恋生命。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某个角落偷偷地流泪,你忧伤的背影宣示着命运的悲哀和生命的无常。但是面对失落和厄运,一切的自卑都是那么的苍白,无济于事。在血色黄昏,你必须重新鼓起勇气走向黎明。……”
“……相信一切最痛苦的事情终会过去,生命的航道一旦用理性疏通,即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生活一样会掀起美丽的浪花。”
最后,我给这封信命题,名字就叫《一封发不出的信》,而收信人的名字就叫雪儿。洋洋洒洒几千字,全是真诚的劝慰,没有人知道我这封信是写给雪儿的。能否获奖已经是其次的了,心到,一切便豁然开朗。
后来呢?她看到这封信了吗?我有些迫切的问。
嗯。真的没想到着封信让管教挑出来了,而且表扬了我。并且让我通过广播把这封信朗读一下。我拿着麦克风,手竟然有些发抖。你知道我中学时播音还算可以。于是我很块站稳了阵脚,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这封信。一想到她将心领神会,我发现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深情的朗诵中,雪舞着,飞翔着。象冬天的精灵。
六
开春,我的判决结果终于下来了。酒后意外伤害,刑期三年,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你没事了?我问。
可以这么说,但我已经在里面呆了半年。真他娘的不是人呆的地方。结果比我想象的要好,但同时我依然惦记着另一个人的命运,感觉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最后那段时间,女监舍已经搬到楼上。让我望尘莫及。每当我走过女监舍,望着空荡荡的监舍,便有一种要命的留恋。我仿佛又看见她站在走廊上,一张美丽的脸庞刻画着忧伤,刘海在风中飘扬;我又希望在楼梯的出口和她邂逅,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一种宁静和安详。但是这样的机会似乎再也没有了。
三月,我被释放回家。离京时,桃花一片灿烂,而到老家,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自由世界使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但同时让我的怀念也不成样子。
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叫雪儿的女孩。当亲情和爱情都陌生甚至遥远的时候,雪儿竟如此在记忆的开阔地里畅通无阻,慰藉着我孤独又倔强的生命年轮。于是我便给看守所一位还算称得上谈得来的警察写了封信,在经过很长一段饮水思源的总结后,我侧面探听雪儿的下落。
很快得到了消息,警察朋友的回信里只字未留,只装着一份《新京报》,在《社会经纬》一栏,我看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美丽的囚徒含笑受刑》,才知道在我释放前,雪儿已经如一缕青烟飘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走上刑场的她为什么笑得那么灿烂,义无反顾。当生命行至末路时,一份真诚的关爱燃烧了她枯木般的心灵。尽管我无力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但相信在那个世界的她是幸福的,快乐的,来生一定还会活出流光溢彩的人生故事。
听到雷人讲到这里时,我听到了哽咽声。
我看到雷人的鼻翼努力控制其翕动,但仍有一溜黄色的鼻涕流到他稀疏的胡须上。
“故事,只是故事,别当真,谁当真谁就傻,呵呵。”雷人笑着走出屋门,他背影猥琐。但走路的姿势自信有力,每走一步就腾起一团大大的雪雾。
七
一年多后我才开始整理这个故事是我的疏忽,更是慵懒所至。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开始沉浸在南方炎热的夏季里。
隔着长长的岁月的距离,恍惚间我似乎看见那个积雪堆在门外的冬天,一双戴着手铐的紧握的双手。当生命的寒流不再,那张忧伤的脸庞绽放出了永恒的微笑。
一股熟悉的肥皂芬芳弥漫在空中。
我仿佛看见她文静地坐在大铺上,听着雷人如泣如诉的朗诵,热泪情不自禁滑过脸颊。她贪婪地仰望窗外飞舞的雪花,享受着生命最后的慷慨馈赠。
空调开得很低。光着膀子的我有些冷。
我关掉空调,踱到阳台上去。
一轮刚被雨清洗过的朦胧圆月,正悬吊在万家灯火上的茫茫夜空。
责任编辑: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