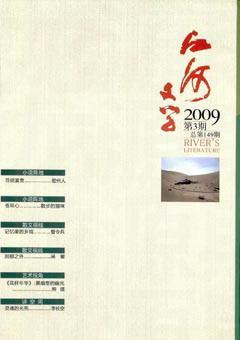汉族妹和布依哥
王宝玉
那年春天,他们偶尔相识,彼此间都留下良好的印象。
1973年初春,高原上的清晨,凛洌的寒风仍呼呼地刮着,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握着打狗棒,背着税务包的张锐,压抑着离别亲人的忧伤,走向大山深处征税。她正缩着脖子靠近城关税务所侧面那棵百年榕树,刚向河坎下了几步,布依老所长急促地在她身后喊道:“小张,你昨天刚探亲回来,休息几日再进山,要不等明后天小莫小姚从山里回来,你再同他们一道出发,山顶有一段路太荒凉。”望着老所长那副怜爱担心的表情,张锐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她答道:“你老放心吧,我要尽快将年前年后的这段税收上来,再往后就春耕农忙了,我会小心的。”
是啊,河坎边这根深叶茂的古榕树就是所长感叹的见证,今日,它仍然立在河边上向美丽的婀丽河伸着臂弯着腰,欢送着张锐走上渡船,又望着她随船横渡到对岸,然后在对岸那片田野上行走,直到看不见踪影。
走完那一段唯一空旷平坦的沃野,张锐眼前横亘着无边的崇山峻岭,她抖擞精神,拄着竹棍,时而在螺旋上升的盘山路上踩踏,时而又在公路边的小道上攀爬,终于浑身冒着热气登上了离县城最近也最高的山顶。她看了看手表自言道:“快走吧,还有二十里路呢。”是呀,这山顶就是新的起点,从这里还要爬一道坡又一道坡,绕一个弯又一个弯,随着陡峭的山路走向各个隐蔽在丛林中的山寨向村民收税,这就是读完五年大学,毕业后到部队受两年再教育,又下到基层的女大学生张锐的工作。
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转身向山里赶去,来到一片灌木地,听见背后发出“唰唰”的声响,她急忙回头,环顾四周,除了在风中不停晃动的草和树什么也没见,她惊吓地问了声:“谁?”无人回应,她的眼睛一下盯住了身后那一簇簇高大的芦苇,耳边顿时想起了小莫小姚路过此地时对自己说过“那芦苇里最藏老虎”。“老虎?”张锐背脊立刻掠过一股凉意。她一边后退一边四处恐慌地张望,然后使出全身力气,快步转弯奔跑,同时大声吼道:“我不怕。不怕,就是不怕……”不怕不怕的声音在四周的山峦中此起彼伏地回荡。
这时,正在附近山道行走的岑大权听到了喊声。这位六十年代的军人、七十年代的民兵。有一种本能的应战准备意识。他边跑边喊:“谁?你在哪里?快说啊,是谁?”听到有人接应。张锐心里一阵高兴,恐惧感顿时消散一半,她仍然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在这里,在这里,芦苇丛边!”说了两次,应声而来的岑大权快速向张锐奔来,远远地看见张锐手持着竹棍,惊恐地跑着,但并无险情,便松了一口气,大声问道:“你是哪个队的知青,为什么在这儿呼叫?”张锐喊道:“那,那个里面!有老虎!”“老虎?”听到此话,赤手空拳的岑大权先楞了一下,然后疑惑地问:“先别怕,你亲眼看见的吗?”张锐说:“没,没看见,但我正在走路,听见里面有唰唰的声音。”张锐说到此,全身仍感到毛骨悚然。听到此话,岑大权眼睛密切地凝视着芦围丛,并一步一步地向芦苇靠近,只见芦苇不停地摇动,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朝芦苇丛中扔去,吓得张锐一边往远处跑,一边喊:“你怎么扔石头,老虎出来怎么办?”岑大权道:“不弄个明白,万一过路的人真闯到怎么办?”张锐吓得加快速度跑起来,“扑通”一下,摔了个嘴啃泥。岑大权又朝芦苇里扔去几块石头,仍然未见老虎。于是,他拍拍手上的灰,回头朝着张锐喊:“别怕,没有老虎。”见张锐摔倒在地,赶紧跑了过去,一边扶起张锐,一边说:“你看,再往那边去一点,就是悬崖了,不小心滚下去,就真的没命了。”张锐哭丧着脸说:“完了,我的腿断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岑大权扶着她,凭着经验说:“你把腿踢一踢。”张锐踢了两下,岑大权松口气说道:“骨头没有断,是筋被扭伤了。”岑大权老练地在她腿上几推几拉,不一会儿,张锐感到疼痛感减轻了许多。他俩慢慢地走着,岑大权说:“还是解放初期,这里出现过老虎,但这几十年都没听说过老虎的踪迹了,倒是偶尔听说过有凶猛的野猪与人不期而遇,不过,遇上野猪,你不搭理它,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倒是野兔经常出现,刚才你听到的唰唰声,估计就是野兔,它见到人就会象箭一样从草丛中窜跑。”张锐仍心有余悸地说:“如果真有老虎,我今天就牺牲了。那我再也回不了湖北,见不到可爱的女儿了。”岑大权好奇地问:“你已经有孩子啦?我还当你是知青呢!穿着简朴,两只小辫,这么年青。嗓子又清脆、响亮,还真没想到哇!”张锐微微笑了一笑,说:“你真勇敢,今天遇到你真幸运。”岑大权问:“你在县里啥单位工作?是下乡来帮助修水利的?那可受人欢迎呢!”原本没有弄清对方的身份,张锐是不会告诉自己的真实情况的,但眼前这位看上去衣着整洁、相貌平平、中等个子、黝黑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对精明眼的壮年汉子,那庄重、成熟的表情,朴实、热情的举止,勇敢、无畏的行为足使她产生好感,出于信任和感激,张锐就直说了:“我是城关税务所的,下乡去收税。”听到此话,岑大权先愣了一下,急促地问:“你现在去唐牙队吗?唐牙大队那七个小队是你的责任区吗?你姓张?”张锐奇怪地问:“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岑大权兴奋地说:“知道,知道,几个月前,就听说过你了,你还去过茂乌队呢!”张锐说:“那是去帮助所里面的其他同志完成任务。”岑大权说:“对呀,提起你,村里人都夸奖呢!你比下乡搞农田水利的同志还受欢迎。都说你人长的好,心善良,是我们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到哪家就帮哪家干家务活、带小孩,还到田间地头参加劳动,说你是大学生,但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只要你开税务会,那些没有钱的村民借钱也要把税款交到你的手上。”张锐听了此话,心里热乎乎的,忍不住感慨地说:“是呀,想起这两年,这里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我十分感激,每当饿了,都有热腾腾的饭菜送上手,晚上,有头上擦满了青丝油的姑娘陪我说话,与我同枕共眠。我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走乡窜寨,挨家收税。”岑大权认真地问:“你在我们这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大山区,真不觉得苦吗?”张锐淡然一笑:“苦什么?贵州不是有个顺口溜:毕节、兴义苦乔巴,遵义、黔南一枝花。我工作在黔南这个花乡,还叫苦呀?”岑大权又笑着说:“你这每天翻山越岭几十里,也不觉得累么?”张锐道:“累什么?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也下乡来工作吗?”岑大权说:“可我们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男同志哦!我们少数民族的人个个都是登山能手。”张锐说:“那红军长征中的女兵,不也是一样,跟着毛主席走到了陕北吗?”听了此话,岑大权不住地惊叹道:“你背井离乡,来到我们大山中,吃苦受累,不但没有丝毫的埋怨、委屈,反而乐观向上,令人佩服!”张锐愤愤不平地说:“我就是要让人们改变对知识分子,对女人的偏见。这几年到处都在骂臭知识分子,我们简直被淹没在……”张锐的话还没讲完,岑大权微微皱着眉头,抢
着说:“这种漫骂是错误的,没有知识就没有人类的进步,知识本身就是力量,你工作这么出色,不就是因为你有知识,有能力吗?可惜我们这穷乡僻壤太缺少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幸好,我曾在部队学过不少知识,否则搞农村工作是很困难的……”张锐边走边听着岑大权滔滔不绝的讲述,心想:一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尚能人木三分,相形之下,那些咒骂知识分子,轻视知识的人是多么渺小、悲哀啊!无形中对这位曾经当过兵的民兵敬佩感更进了一层。
张锐和岑大权走着说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口,张锐指着右前方的公路说:“我该从这边去唐牙了。”岑大权热情地说:“从这里到唐牙有一小路,比走公路可节约近一大半时间的路程,你脚扭伤,行走不便,今日我给你带路,往后,你就从这里去唐牙吧。”他俩在蜿蜒曲折的山径上一前一后地走着,每到一转弯处,岑大权都提醒张锐注意路边的特点。不一会,到了一个斜坡上,岑大权用手一指:“你看,对面半山腰那个寨子,不是你今日要去的唐牙么?”顺着他的手尖望去,几个背着背蒌的妇女带着银铃般的笑声在山崖边割着秧青,她们脚下那片被青山环抱的木楼群在翠竹林的不断晃动中时隐时现,一群顽童在小溪边嬉闹,从寨子里延伸出来的青石板路直达大队办公的大木屋,它侧面的几棵树下栓着一大一小两头水牛,那头长着长弯角的大牛似乎看见她,朝着她“哞,哞”叫了两声。面对这熟悉、亲切而又充满生机的山寨,张锐高兴极了,她连连对岑大权说:“谢谢,谢谢你带我走这个捷径,以后,到唐牙来会更快更节约时间了,也谢谢你帮助我赶走了未见着的老虎,还谢谢你帮我治好了脚伤,更谢谢你的是,你正确评价了臭老九。”岑大权微笑着说:“该说谢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不辞劳苦在这里为我们少数民族作贡献。”两人挥手告别。未走几步,岑大权又急忙返回,对张锐说道:“如果你的脚还在疼,就到寨子里面用酒揉一揉。”张锐昕他这么一说,感激地朝他点点头。
张锐在唐牙几个队巡回奔走,一段时间后,经常感到浑身不适,这天她实在忍受不住病痛的折磨,决定回城里看医生。跨进税务所大门,同以往一样的是首先把税款交到所长手里,同以往不同的是没有急于烧开水烫洗让身上发痒的沾满虱子的内衣和毛衣,而是匆匆往医院跑去,医生给的诊断书使她更加忧心忡忡,她回到税务所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吃完药,便蒙头睡觉。毫不知情的老所长在门外喊道:“小张,小张,你休息一会儿到我家吃晚饭。”张锐有气没力回答:“不了,我有吃的。”老所长又接着说:“老孙病了,你明天不用急着进山,到城关五队帮老孙收一天税,刚好明天五队有人结婚,趁机把以前队里拖欠的税一起收上来。那个队有几个村民蛮不讲理,老孙就是被他们打了的,你看行么?”躺在床上的张锐心想,城关不用爬大山,且当日就可返回,就咬着牙说:“行。”“那你明天就下五队去了。”屋里张锐又答道:“好。”
第二天早上,张锐吃完老所长媳妇端来的面。又吃了药,背上税务包,提着打狗棒,用意志坚持着向城关五队走去,她穿过集贸市场那块黄土地,又经过两条小巷来到城郊,左边就是通向湖北去的那一圈比一圈高的盘山路,她停住脚望着左边想了一阵,便又毅然朝右边那条公路走去。经过一路打昕,终于看到大山脚下那依山傍水的五队,它被茂密的绿树重重环绕,进寨的那条路似幽深的古道,两边几棵古朴苍健的青松像卫士一样把守着进寨的路口。张锐正在路口张望。几条凶猛的大狗向她叫着扑来,她一边挥舞打狗棒,一边呼叫着。一位老太婆和一个背上背着幼儿的八九岁男孩赶走了群狗,张锐正向他们道谢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挑着水向这边走来,这不是那次在山里遇到的那位民兵吗?与此同时,岑大权也认出了张锐。当岑大权得知张锐的来由,赞叹道:“你真是税收及时雨啊。这位新郎是我内侄,也是退伍军人,走,进寨热闹热闹,我担保该交的税一分也不少。”张锐庆幸地对岑大权说:“哪里需要帮助,哪里就有你的身影。”
新郎门前的场坝上,一片喜庆气氛,穿着盛装、兴高采烈的村民们,随着锣鼓喇叭声,载歌载舞。身体不适的张锐随岑大权在人群中勉强欢笑一阵后,便和队长、新郎站在僻静处商讨税收问题。岑大权关切地走了过来,张锐委婉地对新郎说:“看这个热闹场面,你至少酿了三十缸酒。杀了两头猪吧?”新郎正想讨价还价,岑大权立马抢先说道:“小张同志不会给你多算的。你还是当过兵的人,应该支持国家税收嘛!”新郎嘟着嘴,用服从长辈的眼神看了看岑大权,然后笑着对张锐说:“等吃了饭,喝了酒再交吧!”岑大权又敢紧说:“早听说过。小张是宁可不吃饭,也要先收税的。”无奈之下,新郎只好如数交了税款。此时,听见有人大声喊:“闹席了!”队长、新郎和岑大权说:“走。上桌吃饭。”可张锐却指着花名册说:“这还有好些拖欠的税没交,尤其是那个动手打老孙的,去年就建了房子,至今不完税。”队长说:“没关系,喝完喜酒,我召全寨开税务会,会上收。”张锐着急地说:“那样天都黑了。我还要带着税款赶回所里。”队长指着岑大权说:“这位城关镇里面赫赫有名的民兵连长护送你回镇还不行吗?”
暮色已降临了,山寨一片幽暗,村民陆续从会场走散。张锐收拾好税务包,又吃了几颗药,在岑大哥的护送下,匆匆往镇里赶去,夜幕中,四面八方的山峰象顶天立地的巨人,温柔的月光照着河边那条直达镇上的蜿蜒曲折的公路。张锐和岑大权即便没有电筒,也能在满山不知名的昆虫的交响进行曲中借着星月光步行。“原来你是镇民兵连长,可所有的人都尊称你为岑大哥。”张锐敬佩地说道。岑大权说:“这还让我感到亲切些嘛!”张锐说:“今天没有岑大哥的帮助。我的税务包不会装得满满的。”岑大权说:“这都是因为你有知识,有能力,能说会道呀。刚才在会场上,那个有名的刘老大,一开头就冲着你吼道,‘我是贫下中农,命有一条,锅有一口,钱可没有。但你沉着冷静,几席话使他口声软了,愿意给你打欠条了,在你继续说服中,他再次退却,愿交税款的一半,可你仍然穷追不舍,层层逼进,最后,他只好全部交清。哈哈哈……换另一个简单粗暴的税务官,恐怕就没这个能耐了。开怀大笑的岑大权又接着说:“还有你在会上用城关镇集贸市场旁边那一口大井为例。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时期的税收相对比,使广大村民真切地明白了,共产党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深刻道理。所以那些长期拖欠税款的人。纷纷掏钱纳税。这一切都说明,你有知识有才干,我挺佩服你的,真的!”张锐却笑着说:“如果没有你这位有威望的民兵连长坐在我旁边。时不时地用表情、神态对群众作出警示,今日单凭我,效果也不一定这么好呀!我真正应该感谢你哟,真的!”
一阵冷风从山谷中袭来,张锐原本虚弱的身体不禁打了几个寒战,顺口说了句:“嗨,这夜风还有点冷嗖嗖的呢。”岑大权关
切地问:“你是否生病了。今天见你的脸色较前次差多了,也瘦了不少,精神也象不太好,十分憔悴。又看你在吃药,你可要注意保重身体呀!我看你胃口不好,不如明日上我家喝喝我家媳妇亲自磨的豆浆,吃点二面黄的豆腐,我媳妇是队里豆腐坊的能手。你上我家来,我还想请你帮我大女儿梅梅找找学习差的原因,你看行吗?”张锐十分乐意地答应了。
张锐看见前方一片闪闪烁烁的亮光,高兴地说:“你看,县城到了。”刚到集贸市场,远远地看见老所长站在税务所大门那微弱的灯光下,焦急地朝这边张望,也许是看见了两个人影。便试探地喊道:“是小张吗?”张锐急忙答道:“所长,是我!”所长喃喃自语道:“终于回来了。”
所长和张锐站在税务所大门前,感激地目送着岑大权渐渐远去的背影。
张锐回到税务所办公室,所长立刻歉意地对她说:“小张啊,今天你到五队以后,我才知道你的情况,你早没有告诉我呀,从现在起。你不用下队收税了,就在城关镇收,等生了孩子再说。”
第二天,张锐提着一瓶酒,一袋五香花生,寻着城南三队县中左侧一百五十二号找去,相隔大约十五米远的距离,她就看见象是刚从地头回家的岑大哥正在自家放着锄头的门边,用水冲洗着沾满黄泥的双脚,同时嘴里唱着:“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张锐暗想,岑大哥不仅大胆勇敢,正直热情,而且还乐观开朗。想到此,张锐便喊了声:“岑大权!”岑大哥回头看见张锐惊喜道:“小张来啦!我还以为你昨晚随便答应一句,没想到你还真看得起农村人哟。”岑大哥话刚落,随即从里屋走出一位穿着少数民族自织自染的蓝白相间的上衣、眉目清秀、俏丽苗条的妇女。她一面摸着自己乌黑闪亮的头发,一面笑眯眯地对着张锐问道:“你就是税务所的张同志吧,快进屋坐,快!”
张锐跨进高高的木门槛,眼前见着一个大天井,天井右侧是厨房、柴房、猪圈,左侧有两个一大一小的房间。岑大权把张锐领到一个小房间说:“那间大的让给我前年结婚的弟弟住,他还在部队未回。我家六口人住这间小屋。”屋里除一架破旧的宽木床、一个旧书桌和两口朱红色箱子,就只有屋中间地炉上的铁锅。张锐奇怪地问:“这屋子里能住下六口人吗?”岑大权笑呵呵地指着头顶:“晚上大女儿梅梅和二娃、三娃爬上去睡,四娃和我们就睡这里了。”张锐看到岑大权如此简陋清贫的居室,想到昨晚在五队税收会上。他从身上掏出钱来借给别人纳税;想到他宁愿自己一家六口挤成一团也要让弟弟住得宽敞舒适的长兄情怀;想到自认识他以来从他身上看到感到的各种优秀品质,张锐钦佩不已,她叹道:“岑大权真是难得的好人难得的好兄长,如果我有这样的大哥,该有多好!”岑大钱权欣喜地说:“如果,你不嫌我这布依族的农民又穷又少文化,你就把我们当你哥嫂吧!”一家七口人围坐在地炉。看着炉边木墩上的七碗八碟香喷喷的肉和菜,张锐举起一杯酒,对着岑大权真真切切地说:“我在贵州举目无亲,从此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大哥大嫂,请你们受我一拜,认了我这个小妹子吧!”
又是一个赶集日,张锐在水泄不通的市场上转来转去收税,突然发现十字路口围满了人,她急忙走过去,见一位七十来岁的驼背老太婆背对着一个约三十多岁高个男子哭丧着脸说道:“这是我赶夜工做刺绣的钱呀。”那男人吼道:“你再不拿出来我要搜身了。”说完他俩便拉扯起来。当张锐得知他们是母子俩,那男子名叫吴明,是贵阳大学毕业分到县中的教师时,心里充满愤怒。她冲着那教师呵叱道:“你像是老师吗?”此话一出口,围观者纷纷指责吴明,吴明将一双凶狠的眼睛转向张锐:“你收你的税,管闲事干嘛,不看你是个孕妇,老子今天对你不客气。”说完在众人蔑视的目光中灰溜溜地走了,那老太婆对着张锐千恩万谢,并一定要送一双精巧的小虎头鞋给张锐,说是给未出生的宝宝穿。此时,正巧岑大权给张锐送豆腐来,得知刚才发生的事,便对张锐说:“锐妹,你做得对,对这种缺乏道德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批。”张锐把大哥送来的豆腐分一半给老太婆,怀着连自己都理不清的心绪返回税务所。
转眼进人炎热的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焦了税务所门前集贸市场的泥土地。刚从街上收税回来的张锐气喘吁吁地走进自己房间,脱下发烫的球鞋,光着脚丫靠坐在床架上,扇着扇子歇息,一扭头看见窗外大嫂手里提着口袋向税务所走来。大嫂一进门就夺过张锐手上的扇子,坐到张锐床边说:“来。我们一起扇!”她边扇边说:“你大哥催着我给你带些糯米耙来,吃了可养人,你多吃点呀,你一个人吃的是两个人的饭啊!”扇了几下,大嫂站起来,“我今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你把床单、蚊帐拿到河里去洗,这是大哥的命令。…‘你大哥说夏天汗水出的多,你们城里人爱干净,你在这山沟里面,身体又不方便,爱人又不在身边,还要忙工作,真是够苦的,咱哥嫂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呀”。听到这朴实真挚的话语,张锐心里酸甜酸甜的。
张锐站在高高的河坎上,低头望着河边使劲捶着衣物的大嫂,心里感动地喊着:“我的大哥,我的大嫂,我在贵州的亲人!”
嫂子晾好了衣服,临走时,东张西望看看周围没人,便拉着张锐的手轻声说:“锐妹呀,我想给你说点事,你就不能够调到县中去教书吗?梅梅和二娃不是你,他们这学期考试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吗?连周围邻居的孩子都说你讲的课比学校的老师还好,你会讲语文,还会教物理、化学,而且当老师又有两个假期,到县中离我们家又很近,咱哥嫂也可以更好地照顾你和小宝宝,你总不能生了孩子以后又背孩子去大山收税吧。”
傍晚,张锐吃着嫂子送来的糯粑,独自坐在税务所侧面的河畔上乘凉。落日的余晖洒在河水中,照亮着她的思绪,左思右想后,张锐决定向县委组织部申请调动。
经过反复周折。税务局终于同意了张锐的调令,但谁也没有想到,进入县中的那几年竞成了张锐这一生中最凄苦最愤慨,也是最自豪的几年。
张锐到县中上班的第一天,中午时分,大嫂已做好了饭菜等她吃午饭,左等右等也没看她回来。大哥正准备叫梅梅到学校找姑姑,就见张锐满脸怒气地进了门,哥嫂急忙上前问究竟,张锐“哼”了一声说:“真是冤家路窄,大哥你记得那次在集市上被我当众指责的吴明老师吗?”大哥应道:“记得,他的妈常到店里买豆腐。每次赶场,她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她见人便说吴明对她不孝。”张锐轻蔑地一笑说道:“这种人竟然是我们综合教研室的主任”。大哥一家十分诧异。张锐接着说:“他想给我下马威,第一天就刁难,把学校给教研室批林批孔的讲座任务放到我头上,而且时间就在明天上午。就一个晚上的时间准备。我找办公室打听,除了几张报纸,什么参考都没有,我总不能凭空乱讲呀!”大哥大嫂听了也傻了,见大哥大嫂着急,张锐反倒安慰说:“怕什么,我就要他们知道巧媳妇能为无米之炊。大哥,你下午帮我到镇上借今年的红旗杂志,我手上借了几本历史书,再加上报纸上的观点,我今晚就
下,流出的滚热泪水;而面对假丑恶,张锐却呈现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形象,她愤怒呵斥,百折不挠,顽强抗争,谁在她脸上也看不到一滴泪水和屈辱的表情。这一天晚上,因为春儿生病。张锐便背着她去参加批判会,不料天空下起雨来,散会后,雨落得更大了,老师们打着家人送来的雨伞回家了,有的家人没送雨伞来也被有伞的老师一起带走了,可谁也不敢叫张锐同打一把伞,谁也不敢对她关心的问上一句话。她背着春儿孤零零地站在会议室的大门口,望着茫茫的雨地。突然,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线里。随即听见“锐妹”的喊声,“我的大嫂送伞来了”,她急忙上前接过大嫂给她撑开的雨伞,泪水长流。
一天傍晚。大嫂和张锐正在给哭得喘不过气来的春儿喂药。望着春儿那张苍白的小脸,想到这些日子饭没有给她喂饱,药却灌了满肚,张锐心如刀绞。这时大哥进来了,张锐欣喜道:“你回来了!”大哥说:“回来办点事,明天又要下工地。”说话间,他一眼看见床上的春儿,心疼地问:“怎么这几个月,春儿瘦成这个样了?”又回过头问大嫂:“你是怎么帮着照看她的哟?”大嫂不说话,只是撩起衣角擦眼睛。
当大哥得知情况后,气得把桌子一拍。说道:“真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几年学生经常开会劳动,学了些什么科学知识?已经这样了,还在鼓吹考试打零分的张铁生,大呼小叫教育形势大好特好,反而说实话的竟成了右倾翻案典型,太不象话了”。这时,梅梅突然进屋来,对着张锐说:“姑姑,吴明带几个学生来叫你去开批判会。”张锐对大嫂说:“嫂子,请帮我看一看春儿,我去开会了。”大哥一下站起来,说道:“不去,今天你就在家照料春儿。”然后走到大门口,目光如炬,冲着一群来者吼道:“谁来叫张老师开批判会?”吴明见学生吓得躲躲闪闪,不敢吭声,便大模大样走上前,答道:“学校领导!”又接着说:“学校领导也是奉教委的指示。”大哥说道:“什么领导,什么教委,明明是你想落井下石,以泄私愤,你们回去告诉学校,张老师根本就没有错,该受批判的应该是你们。”同时又指着那几个学生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凭什么去喊超英赶美。”
学校认为张锐态度太顽固,太放肆了,决定第二天在大操场召开邀请县教委领导参加的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对张锐的右倾思想进行公开批判,并宣布对张锐的处分意见。
张锐认真地对大哥说:“哥。你明天一定要参加大会后再去电站哦,我马上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去贴昨晚我写的几十张大字报。公布今日下午县中公开召开批判张锐的大会,敬请全县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尤其是学生家长,务必参加,因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呼吁全社会的人都来关心教育,评判教育,一定要把这个错误的批判大会变成激烈的辩论大会,把被审判的人变成审判者。”
果然,社会上的群众看了张锐的大字报和海报,有的怀着好奇心,有的凭着正义感。纷纷聚集到贴满大幅标语的批判现场。会上,张锐看着象铁塔一样站在人群里的大哥,心中又踏实又兴奋。她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摆实情,讲真理,用正义言辞把批判者们的发言驳得体无完肤。全场群情激愤。教委领导当场责令校长宣布散会。
这次批判和反批判大会惊动了县委,县委领导肯定了张锐的言行。从此在县中,谁也不敢再提张锐是右倾翻案典型的话语,也再没有谁敢说批判二字。
为了骨肉团集,张锐要带着春儿调回湖北了。
九月的夜空,满天星斗,大嫂坐在高高的木门槛上,抱着熟睡的春儿,张锐坐在大嫂身边,望着县中操场上开批判会时挂着大幅标语的白杨树和树后面那排她与春儿住过的平房,思绪万千。看着屋里忙着给张锐收拾行装的大哥,大嫂难过地说:“你们回湖北了,我和你大哥会很不习惯的,会很想念的。”张锐含着眼泪说:“我也一样。春儿长大了,定不会忘记是大舅妈的豆浆把她救活养大。”
夜深人静,张锐悄悄从床上坐起,从行李包拿出笔和纸,打着电筒写道:亲爱的大哥大嫂。我和春儿要回湖北了,但心里实在舍不得你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年,你们对我象亲人般的关怀体贴,忘不了你们在我最困惑的时候给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和幼小的春儿重获新生,分别之际,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块手表就留给大哥出门工作时用吧,愿大哥大嫂全家幸福快乐!张锐写完信后,就把手表从手上取下来,和信一起放进牛皮信封里。
长途车站的汽车顶上,大哥正在给张锐捆绑行李,大嫂带着离别的忧伤,不断抚摸着春儿那枯黄的头发。此时,听见司机大声喊道:“上车了,要开车了!”只见大哥从车顶上跳下,向张锐这边走过来,张锐想到与大哥大嫂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见,她使劲地盯着大哥大嫂,想要把两个亲人的面孔印在脑海里,盯着盯着,无法再锁住的泪水象大坝决堤一样冲了出来,她把那装着感恩的牛皮信封递到大哥手中,从大嫂怀里接过轻瘦的春儿,激动地喊道:“大哥大嫂,再见了!”
车徐徐开动了,张锐拉着春儿那细小枯瘦的手,向站在窗外的大哥大嫂喊道:“大舅舅,大舅妈再见!”这一瞬间,张锐清晰地看见,流着泪水的大嫂和红着眼圈的大哥挥舞着手臂,异口同声地喊道:“路上不给春儿喝冷的,吃糯的,到湖北后,赶快来信哦!”车加速了,爬山了,张锐回头望去,见大哥大嫂还依然挥着手,呆呆地站在那里。汽车沿着盘山路,越转越高,直到驶进茫茫的群山之中。
“鸿雁”不停地飞落在黔南山脉和长江三峡两地之间,将汉妹和布依哥嫂的亲情频频传递……
同样也是三月的一天,寒气未尽的春风一阵阵掠过那所幽静的绵羊山学校,正在看书的张锐突然听到喊声:“张老师,快去取挂号信,贵州来的。”一听是贵州来的,她欣喜地放下书,自语道:“布依哥的信,肯定是四娃真的当兵了,有刚入伍的留影,不然,怎么会寄挂号?”
信封上并不是大哥那熟悉的笔痕。却是梅梅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她急忙打开信看:亲爱的姑姑,您好!寄来的挂历和糖果收到了,妈妈催我给你写信,你和我们分别十几年了,可一直都想着我们,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只是今年过年,爸爸没有象往年那样吃着你的糖。他老人家年前因公牺牲了……读到此处,她不相信自己眼睛,又反复读了两遍,脑子里轰轰直响。睛天霹雳!她喃喃道:“不,这不是真的,不会这样,大哥才59岁,还要为寨子里的父老乡亲做许多好事,为山乡四化建设作许多贡献,还答应过到葛洲坝来参观呢!”
站在高高的绵羊山顶,望着西南方向,张锐泪如雨下,她透过翻滚的云层寻觅着黔南山脉中的恩人布依哥。
责任编辑: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