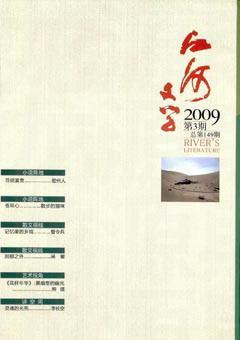记忆里的乡戏
曾令兵
很久以前,家在近郊,桑葚的红紫,杨桃的青绿,茉莉的皎白,菊花的金黄,曾是为我美好童年打底的绚烂,但总是不及村里青石戏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戏曲留下的妖娆。
记忆里最厚重的大戏台是用大石块砌成的,灰白的色调干净而古朴。一旁大榕树的枝桠碰碎了一地的阳光,斑驳的叶影在青石上闪烁着,倒也颇有几分盎然古意。不唱戏的时候,戏台就用来晒粮食,那时,黄澄澄的谷子铺满了整个戏台,粒粒腆着饱满的肚腹静卧在阳光下,一片金黄灿烂,映得路人的眼睛里全都充溢着幸福的黄色调。戏台后面是一座红墙黄瓦的小庙,终日香烟缭绕,总有很多孩子在那里嬉闹,也时常有几个调皮鬼窜到戏台上过过戏瘾,不过从来只有武斗没有文戏。我是从不上去玩的,总觉得一人多高的戏台是需要仰望的,神秘而奇妙,让人轻易接近不得。
不过社戏却始终是亲切的,着实让人喜欢。每逢农历里的大节,悠扬的歌声在清凉的夜风里断断续续地传来,轻敲着耳骨钻进心里,一丝一缕地泅成一片浮动的迷醉时,我就马上明白村里请来的戏班子已开始吊嗓子练唱了。恍惚中,艺人们躲在飘飞水袖后面的差涩笑靥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便万分心急地拉着爷爷去看戏。
有时候去得早了,爷爷在一边摇着大蒲扇打盹儿,我就会悄悄地溜出去和村里的小孩玩,先到不远处的古井边转圈圈,几个人扒着井沿望着玉一般墨绿的井水发愣,或是看着来来去去的村人傻笑。开唱之前艺人们都会在大树下化装,用小巧的竹帘遮着,很是神秘。有时薄薄的竹帘被夜风一掀,便露出了艺人们隐约的容颜,在黄色的灯光下,那斜插入鬓的剑眉与弧度完美的红唇仅仅是惊鸿一瞥,就已让所有的孩子们艳羡无比,特别想摸摸那可以幻化成无限美丽的斑斓油彩和妖娆胭脂。这时,小庙前的空地上也早就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但从不高声说笑,农人们平日里的粗犷全不见了,脸上全无例外地带着幸福的神采,眼角眉梢上写满了认真与期待。此时,脉脉月光下的戏台正浸润在夏夜清冽而洁净的空气里。还弥漫着日间谷子残留的微香,夹杂着泥土和夜雾的味道,轻轻一嗅就舒坦无比。
终于开唱了,师傅们敲着金钹拉着二胡,好听的亲切曲调就飘了出来飞到各个角落,让人们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故乡的乡戏虽然没有吴侬软语的越剧那样珠圆玉润,却带着特有的热情,活泼但不媚俗,平易却又不卑贱,向外散发着它古老而不改蓬勃的生命力。只是年纪尚小,听不全那些时而迅疾时而凝重的台词,总是一知半解地连蒙带猜,也分外关注台上艺人的一颦一笑。不必说孩子们最喜欢的滑稽可笑的丑角,即使是面对拖着长腔的老生也舍不得移开眼去,小小年纪里竟也会随着剧情不时喟然长叹抑或抚掌大笑。
只是黄毛丫头实在无法免俗,最喜欢花旦与小生。记忆里的小生是由女子反串的,那清丽如水的容颜在峨冠博带的映衬下倒也平添几分英气。雪白的扇骨一滑,书生的倜傥潇洒就在风中徐徐绽放。只是那小女子些微的腼腆与羞涩依旧会偶然地在那儒雅的微笑里悄悄显现出来。演花旦的也是极为标致的女子,掩嘴微笑时会忽然满脸绯红,让双颊上的胭脂生动起来,清甜的歌声在那一低头的温柔里慢慢荡漾开去,搅得台下人们的心里荡起一圈圈的涟漪。唱到动情处,她眉尖一蹙,长长的水袖一摆,自是有说不出的妩媚。
故事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落入俗套,俱是花前月下的才子佳人,征战沙场的骠骑女将。但这些全都凝聚着故乡人们的憧憬与希冀,对于善良和正义的坚持与笃信让一切都变得可亲可敬。曲折跌宕的情节也叫人分外着迷,心旌摇动之际就跌入了戏中的情境。为英难早逝扼腕,替美人玉殒心伤。所以,每当爷爷倦了要走我都会固执地留下来,哪怕要独自一人走在归家的夜路上。
多年我还一直认为,戏台上眉分八彩气宇轩昂的俊朗与眉似远山朱唇妙目的俏丽。是生活里难以企及的美好,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拥有那复活瞬间的鲜活和感动。不是吗,那过往的所有就像烟云般散去了,但是只要摇摆的艳丽女人迈着不急不徐的碎步踏上青石戏台,抿嘴微笑或是皱眉轻嗔时,一切就都又骤然苏醒。一点儿也不生涩苍老,仿佛从来没有停顿或消失过。千年的传奇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灞桥折柳的分离一刻。蟾宫折桂的得意之时,全在艺人们动情的表演里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在红艳艳的戏衣翻飞处无限扩大,风流了千年,依旧不改当日的辉煌……
当所有的回忆在五月温暖的阳光中尘埃落定的时候,窗外传来了《西厢记》绵软无奈的歌调:“如潮的掌声留不住戏子笑容,昨夜的莺莺,昨夜的张生,洗去胭脂,何去何从?”他们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唱出生命如戏的悲伤与悲凉。呵呵,其实也不全是这样的,匆匆走过的我们,都在只属于自己的戏里传承着生命里苦痛抑或是幸福的全部美好,有无可奈何,更有不变永恒,而浓缩了芸芸众生生命轨迹的乡戏,将凭借着它绵长而坚忍的生命力。在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向所有憧憬美好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一切美丽的故事……
责任编辑:吴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