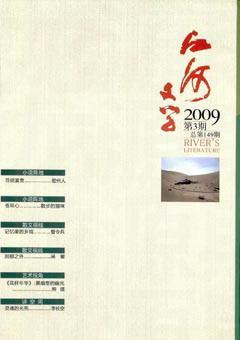苍耳心
散步的猫咪
他说:“我只能承诺不跟你离婚,其他的办不到。”
她生得丑,字亦不识得几个。只因为她爹在一次矿难中救了他爹。五期纸后,他娘上门要了她这个孤儿做儿媳妇。
他不应。
但他孝顺。忤不过娘的以死相挟。
婚终于结了。
洞房花烛夜,他摇晃着单薄的身子,和着浓重的酒气,隔着红盖头指点着她的额,撂下一句:我答应娘不跟你离婚,不过我的事你也别问,这,这是警告。颓然丢下一地呕吐物和顶着红盖头的她和衣睡去。她揭下盖头,心被满屋的喜庆与安静刺得通红。收拾好脏物又打来热水给他擦洗。她想,这是妻子的本分。立在床边看他楚楚朗月似的脸,泪水珍珠般滚过粗糙的双颊,重重落下,激起小小的欢喜的微尘。
日子过得平顺。她整日里低眉顺目,只知清扫煮饭,照料老人,还有一大帮子家畜。似乎,在村人眼里这也是段不错的婚姻。只有他知道自己要的爱情至少是树旁的一株木棉,或者是红玫瑰和白玫瑰。她,于他,只是块丑木,多看一眼,就添厌烦。
终于等来机缘,招聘会过五关斩六将,他在县城小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摆脱了窝窝头和黑咸菜的束缚,摆脱了她唯唯诺诺的阴影,仿佛有了卸去枷锁的轻松。
“我不爱她,从来没有过。”他想。
一扫惯有的慵懒,才华加上勤恳,他在寸尺讲台上神采飞扬。上他的课,成了学生最大的期盼。不久,提了职,分了房。他想接爹娘同住。老人惦念家中几口薄田,不肯。她,守着满腹卑微,踌躇着说不出好,或者不好。他不强求,没有她,更心净。七年,他一直当她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无视,甚至回避她的存在。
成功往往滋生人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有遗憾。于是,他迷恋上红的白的酒精,迷恋上一张张荷花脸和狐狸脸,越陷越深,越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他的绯闻,她不知。就算有人传进她的耳鼓,她也只是打着大大的哈欠说:坑人,坑人。
他轻易不回家,说忙,只按时让人捎来家用。就算回来也跟她无语,更无亲热。而她却不曾有半句怨言。仍旧算好他回来的日子,铺床晒被,洒扫庭院,做他爱吃的蛋炒蒸野菜,一刻不停。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孩子,歇会吧。”她把散落的发丝抿到耳后,说:“娘,不累。”脸上的皱纹笑成一丛杂草,深掩起酸楚麻木的心。
他有风湿。
她哄着六岁的儿子拉他一起去找苍耳籽。
“苍耳能通鼻窍、祛风湿、止痛呢。”她重复着老中医说过的单词。他不知道,为这几个单词,她反复背诵了整整一天,只为怕说错会招来他不屑的冷腔。
这天她少有的欢乐,少有地多言,还在鬓角插一撮淡紫色的野花。用眼角偷偷瞥着他问:“儿子,娘头上的花好看吗?”
九月的正午,阳光温热。她一边在芦席上铺晒苍耳籽,一边听廊下他和儿子说话:“这叫苍耳,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你看,它是什么形状?不对,不对,不是圆的,它是纺锤形,嗯,就像你奶奶以前纺线用过的纺锤”。
她偷偷地想:什么是菊科?什么是草本植物?是不是地里的草都是革本植物?他怎么什么都懂啊?转过身,眼前依旧是记忆里那个书生模样。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视线忽聚忽散,眼角弥漫起幸福的哀伤。他从儿子的眼睛里看到背后的她,突然转过来。四目相对,空气在刹那间凝固。望着她脸上僵硬的笑容,他的心,划过一丝歉疚。抚摸着腿上儿子的头发,儿子黑亮而浓密的头发,像她。这是她身上最美的地方。他说:“孩子该上学了,还是城里的条件好一点,所以,我想让他到城里去读书,你,你也一起去吧,这么多年辛苦了。”他的话音刚落,她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先是憋忍着抽泣,后来声音很大,像打开了洪门,释放出多年的郁气。这是他第一次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说话,是他第一次认可了她的努力。她觉得所有的付出和等待都值了。她使劲地点头。阳光照在她头顶油亮的黑发上,闪出烁烁的一圈光亮。
是不是生活就此转了个弯。她这样想。
当天,她东收拾西收拾忙的不亦乐乎。他看了她的成果,只淡淡地说了声,都扔了吧,用不着。她诺诺地应,仅带走用粗格子布裹着的小小一包苍耳。
坐在后排座上,她沉默着,心随颠簸更加忐忑。倒是儿子,像一只自由的小雀子,兴奋地问这问那,叽喳不停。因紧张而挺直的脊背让她感觉很累,于是,她松开紧绞的手指,缓缓地挪了个姿势,并借此机会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他。他正和儿子高声地交谈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气氛看上去轻松而融洽。她轻轻地吁了口气,却正巧被他捕捉在眼里。他说:“咱们家在三楼,靠近马路。白天会很吵,也没有乡里哪样宽敞。刚开始也许会有些不习惯,但慢慢就好了。”
他说家!是的,他在说家!我和他还有孩子的家!她又一次眼眶湿润起来。这一天美好得如同一场春梦。她深深地喜欢这种感觉,并深深地害怕失去,失去她还未握住的幸福。
她努力地学习如何向小贩砍价;如何跟电视上学做一些光鲜的菜肴;如何捏住粗嗓门装出轻柔的样子和邻居说话;如何熟悉公交车的线路时间表;如何打理孩子和他的衣着;如何礼貌地接电话。为了弄明白家用电器的使用方法,她甚至开始学习文字。她也习惯了当有人在她面前称呼他为沈校长时,要露出标准的八颗白牙;习惯了他的早出晚归,习惯了在他醉酒后的整夜守候,在他翻身要水时,双手奉上一杯温热的蜂蜜茶。她按他的要求烫了发,漂了牙。学会使用一些功能繁杂的化妆品,在自己的头发上、脸上、手上、脖颈上。她甚至喜欢上照镜子,喜欢在家里只剩自己的时候,偷偷地照镜子。仔细地打量,然后很开心地爽声大笑,并深深追忆彼时那个丑陋的乡下妇人的身影。只是,他从不带她出门,从不让她参加孩子的班会,从不和她谈论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以外的生活。她倒也宁愿守在家里,守在等待门铃响起的忙碌里。
分房而居,如大海里两个世界的游鱼。但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对她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赐,她不敢奢求其他,不敢期待着进一步的亲密。
只是,当不经意听他电话里传来的娇媚女声,不经意发现他口袋里的情书。衣领上的唇印时,当他一次次不做说明的未归或深夜外出时,她的心,会扭曲着痛,会害怕。她常常把自己埋在黑暗的角落里,憋屈着,不敢出声,只是大口地吸气,吐气。如同一条离开水的鱼。是啊,他是她的水。他给,她就活;他不给,她只好缺氧地死去。
只是,也有不甘心的时候。她跟踪他。亲眼见证车厢里,一对男女在黑暗掩映下恣意地调情。但是,她不敢上前叫骂,甚至不敢哭出声来。就那样僵直地目睹事情的发生。在头嗡的一声巨响后倒在地上,黑瘦的身子直挺着,如同一条死去许久的鱼。
她依旧沉默。对所有关于他的绯闻不做声息。只是整日微笑着,在灼人的等待中打发时日。
“等他老了,走不动了,他就是我的了。”她想。
他习惯于她的侍奉,习惯于在家庭的宁静中如沐春风。迫于声望,他没有抛弃她。看起来倒像是兑现了婚夜的承诺。只是,他仍
习惯无视她的存在,无视她的喜怒哀乐。
“给你吃喝,给你钱花,给你地位。你应该很满足了吧?”
他这样说的时候,她浅浅地微笑着,正盛满满一碗鸡汤端给他,一条大鸡腿横在碗中央,突兀的很。
他没有听见她心碎的声音。她的心一次又一次在他面前破碎,他却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习惯于她的存在,如同习惯于在空气里呼吸。
她等到了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她满以为有足够的时间等他属于她,却从没想过时间不给她机会。
一夜,他醉醺醺地吆喝着要她倒水。久久不见回应。他心咯噔一声慌乱起来,径直推开她的房门,惨亮的灯光下,她的脸正憋得发紫,狰狞着,手臂在空中抓狂,像是要攥住救命的绳索。他的头脑片刻间麻木,留下短暂的空白,紧接着扑上前,捉住她挥舞的手,大声地叫:“来人,快来人。”已是深夜,老屋里也只剩他和她。
她张大了口,急促地呼吸,像一条因缺氧快要死去的鱼。他俯下身,唇贴上她的唇。他要给她氧气。这不是她一直渴望的吗?她和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给他生儿育女,他却从来没有吻过她,从来没有。现在他却要急切地挽留她,要告诉她自己还没有做好失去的准备,还没有想过没有她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只是,这虚弱的挽留在死亡面前轻薄如烟飘过。
她用力地张了张嘴,终于安静下来。因抽搐而变形的面部肌肉渐渐松弛下来。脸上似乎还带着浅浅的浅浅的微笑,一如今晨她送他出门时的微笑。
他跪在床头,手里紧攥着她的手,呜咽着,不甘地再次吻上她的唇,给她做人工呼吸。眼泪滴落,从她脸上皱纹的沟壑中滑下,连同她唇上的温度正一点点地散去。他嚎啕失声。他知道自己被遗弃了,被一个他从不在意的女人遗弃了。这对他来说是多么荒唐的事。
“世上最爱我的女人去了!”他悲恸地想。他听到有什么东西正在身体里噼啪地破裂,一声声,接连一声声。他突然想起顺治哭董鄂妃的那场戏来,终于明白就算能呼风唤雨也会有上天人地皆无门的时候。像浪子顿悟了往日的混沌,再无风花雪月。他变得安静起来,提前退了休,整日侍弄她留下的那些花草,还有一只瘸腿的卷毛狗。那狗是她从垃圾堆捡来的,那会儿已经奄奄一息,是她执拗地带回家。她说她就像一条可怜的狗,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会毫无准备地就会被人丢弃。他看着她日记上的这句话,泪水喷涌而出。他以为给了她物质上足够的多,这个从黄土坷垃里爬出来的女人一定会对他感激涕零,却从没想过原来她一直生活在忐忑中。他也没想过她竟然不声不响地学会了读书写字,更没想到她会把他的一场场艳遇统统记录下来。而那些女人香艳的名字在纸上横竖交织成一张张哀怨的网,紧紧地缠裹着她,令她不能呼吸。
她说:“我像一个浓妆遮掩下的戏子,舞台上披着人的皮,卸了妆,退回黑暗里,实在是个萎琐的鬼。”他不敢相信这会是那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乡下婆娘的文字,而这些字正如锥刺般狠狠地刺痛他的神经。令他寝食难安。
他用一把重锁将这本厚厚的日记连同那个格子布的包裹一同锁了起来。包裹里是她辛苦采来的已经落尽锋芒的苍耳子。是他不屑服用的苍耳子。
她走了。他开始重新学习家里电器的使用方法,学习如何把饭菜弄熟,记住每个房间开关的位置……他努力地尝试着她刚到这个家时努力学习过的一切。可是,他还是会常常忘记吃药,忘记天冷要加衣,阴天出门要打伞,夜晚要在卧室、客厅、卫生间都留一盏小灯。所以他常常独自哭着吃下夹生的饭粒,常常在做菜时切到手指,常常在夜晚上厕所时跌破膝盖…,,她走了,他才终于悟出她的好,才终于明白这个苍耳般丑陋的女人也有着所有的美,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悲哀:结婚时,他绝望地以为自己得到的是自己不想要的,而现在,却已经永远失去自已想要的了。只是,所有的后悔都已经太迟。
他开始信奉上帝,静夜里他习惯了跪在神像前,一边忏悔,一边流涕。他曾多次祈求上帝让他忘记曾经的浪荡生涯,希望藉此减轻对心灵的折磨。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怜悯,十多年后:他终于得了老年痴呆症。他再不能说话,对种种询问也都沉默不语。他只爱呆呆地靠在医院病床上看天上飘过的云彩。
如此,如此。
经年,经年。
终于,一个雷雨交织的夜,他去了。
他的私人护士说他走的很平静,只是在临终前曾突然坐起来,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大声高呼:“彩云,彩云!”
护士纳闷地向同事说起他的死:“外面漆黑,哪有什么彩云啊?而且,他不是不会说话了吗?”
自此这世上再无人知道她的小名就叫彩云。常彩云!
上帝曾让他忘记人生的繁华喧闹,却唯独没有让他忘记她,没有让他忘记常彩云!没有让他忘记这个被他忽视了一生却又真正爱的女人!不知道这对他来说究竟是惩罚还是成全。
原来,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在一起时不知道我爱你,等失去了才发现不能没有你。
责任编辑,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