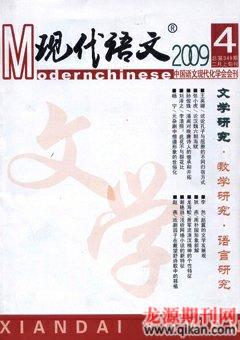戏剧因子在戴望舒诗歌中的移植
赵 燕
摘 要:本文立足于诗歌与戏剧两种文学体裁的相关性,力求探寻戴望舒诗歌中所蕴含的戏剧性因子,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表达个人情感的复杂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对中国新诗做出的积极贡献。
关键词:戴望舒 诗歌 戏剧性因素
在欧洲文学传统中,注重叙事的史诗和戏剧体裁在文坛上占据着主要地位,并且很早就能够相互借鉴,形成了剧诗和诗剧这样特别的文学样式。戏剧可以用诗来写,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诗中更是可以有很多戏剧因素,如歌德的《浮士德》和但丁的《神曲》。苏珊·朗格说:“一切戏剧艺术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正确的表现一首诗——的手段。”[1]袁可嘉也这样说:“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和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2]所以,诗和戏剧并非是两种隔绝的文学体式,它们之间完全可以汲取对方的若干因素为己所用。而中国传统诗歌是以抒情为主,叙述和冲突则很少见。戴望舒在诗歌创作中不但承继了古代诗歌之精华,而且自觉运用了先锋的现代创作技巧,融入了其它文学体裁的表现手段。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他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戏剧因子,如描绘戏剧性的场景,设置戏剧性的情节结构,运用戏剧性的言说和抒情方式等等,使得我国新诗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个人感情的复杂性,以及丰富诗歌的表现性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一、场景和结构,戴诗戏剧因子之一
场景是戏剧叙述故事、展开情节、抒发感情必不可少的表现空间。而戴望舒《雨巷》这首诗一开始“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几句描写就犹如大戏开幕,将舞台背景展现在观众面前一样,为读者创设了一个戏剧性的表演空间:悠长的小巷,青黑的石板、绵绵的细雨,阴郁而孤寂。诗歌主人公“我”也如同戏剧的主人公一样在这个阴郁又孤寂的场境中讲述故事,抒发情感。主人公“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终于,“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和“我”一样凄婉迷茫,随后从“我”身边擦过,又“静默的远了,远了……走尽这雨巷。”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仿佛看到舞台上有一束追光伴随着姑娘出现又消失,又只有“我”还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彷徨……诗歌用文字描绘出这样具有舞台效果的场景,给读者留下了如同看戏一般无尽的回味。
如果说诗歌《雨巷》是在背景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话,那《自家伤感》一诗“怀着热泪来相见,/冀希从头细说,/偏你冷冷无言;/我只合踏着残叶/远去了,自家伤感。/希望今又成虚,/且消受终天长怨。/看风里的蜘蛛,/又可怜地飘断/这一缕零丝残绪。”则淡化了背景,突出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描绘出较为完整的一幅戏剧性场景:“我”怀着美好的希冀,热切的愿望来到恋人身旁,却遭到一番冷遇,只好踏着残叶,带着伤感而去,路上看风里蜘蛛的零丝残絮,慨叹自己希望成虚的悲哀和蜘蛛般飘零的命运,犹如莎士比亚剧中常常出现的人物独白。诗歌中的这种戏剧性场景描写,既方便主人公内心情绪的显露,又能够帮助读者产生画面感和丰富的联想,在这种阅读情景下,诗歌作用于读者的就不仅仅是文字了。
戏剧结构常用的有开放式、回顾式等种类。开放式结构的戏剧总是按照事情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自然时间顺序展开,极少回叙成分,能够让观众非常方便地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了解剧情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国传统戏剧常用这种结构方式,一般由四折构成,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自然顺序来结构。戴望舒的《寻梦者》一诗的即有这样的戏剧结构因子。诗歌选用美丽的象征意象唱出了一首寻梦者灵魂的歌。年轻的他相信美丽的梦一定会“开出娇妍的花”来,但在寻梦的过程中,却要经历非同寻常的艰辛与磨难,“无价的珍宝”隐藏“在青色大海的底里”,得到它需“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旱海”;历尽艰苦寻求获得了“金色的贝”,却并非是寻梦的终点;还要“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这“金色的贝”才会在一个暗夜里“吐出桃色的珠”,可是这时候的寻梦者已经是“鬓发斑斑”、“眼睛朦胧”、“已衰老了的时候”。诗歌借用一个寻梦的过程概括了一个充满理想和不懈追求的人生过程,它有着开端(求无价珍宝的梦)、发展(寻九年、养九年)的过程,也有激动人心的高潮(终于拥有了桃色的珠),还有令人伤感的结局(幸福的快慰是与人生的衰老相与俱来的)。
回顾式的结构是用回顾的方法,将开场前发生的事件和当前的戏剧动作融会在一起,用因为过去事件被揭示造成的“危机”,来显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并迅速将剧情推向高潮。《雷雨》可谓回顾式的经典剧目。戴望舒《过旧居(初稿)》和《过旧居》两首诗就是这种结构形式。经过旧居时诗人忆起了久远以前“尘封的幸福”:“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忽而“有人开了窗,/有人开了门,/走到露台上——/一个陌生人。”旧居物是人非,往事随烟飘散,诗人不愿意又不得不走回现实中来,正视眼前的处境。戏剧常用的开放式和回顾式结构在诗歌中被戴望舒运用的自然娴熟,令人叹服。
二、角色和情节,戴诗戏剧因子之二
角色是戏剧的要素之一,而且必须出现在舞台上。诗歌的主人公则更多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在诗外,甚至可以不出现。戴诗不仅喜欢设置角色,而且经常像戏剧一样让主人公出现在诗中,如《单恋者》《游子谣》《寻梦者》《流浪人的夜歌》等,在题目中就确定了角色身份,犹如戏剧中的角色,成为产生故事、抒发情感的主人公。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题目中体现,但角色感却十分明显,许多时候叙事或抒情主体都是直接介入的。如《寒风中闻雀声》在诗歌的最后一节转换了人称,用第一人称取代第三人称,把角色推到前台,让少年以自我宣叙的方式抒写心境“唱啊,同情的雀儿,/唱破我芬芳的梦境;/吹罢,无情的风儿,/吹断我飘摇的微命。”诗人在《乐园鸟》中不断地发问:乐园鸟,你一年四季永不停息的飞翔中有幸福,也有痛苦吗?在茫茫的路途中,也会感到孤独寂寞吗?亚当、夏娃被逐后天上的伊甸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读着诗歌,我们仿佛看到在舞台中央有一个角色在仰首叩问:苍天哪!谁能告诉我,我如乐园鸟般的追求为什么不能被人理解?谁能回答我,如果天上伊甸园真的已经荒芜,我的不懈追求是否还有价值?诗中的乐园鸟由两个意象组成,即天堂和使者。诗人把两个富有通感的意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孜孜不倦求索者的形象,不断变化着的现代诗情通过角色的塑造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角色之间的关系产生并推进情节,这是戏剧的典型特征。在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诗歌中设置情节是戴望舒诗歌的又一特点。小诗《凝泪出门》,仅仅几行,就有较完整的戏剧性情节。开头两句“昏昏的灯,/溟溟的雨,/沉沉的未晓天”好似一幅愁苦而凄凉的舞台布景,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在这凄凉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物,一是前去告别的“我”,一是酣睡未醒的恋人,“我”无奈地徘徊在恋人的床前,最终独自出门而去;接下来的一幕便是“我”独自坐在远去的车中悄然离去的情景。由于设有具体情节,戴诗避免了早期现代诗歌宣泄式的恣意抒情,给读者留下了更为准确的具象把握,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取得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再如《秋蝇》,以其纷繁多变的意象、众多的隐喻象征和层层推进的情节,成为别具特色的一首诗。戴望舒认为“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3]。所以他调动秋蝇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系统,通过秋蝇对窗外愈来愈昏暗的景物感受,对自身机体渐感沉滞衰亡的体验,创造了一个全官感或超官感“心理格式塔”。并把它和它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用“生(发展)——挣扎(高潮)——死(结局)”这样一个完整的情节反映出来,象征人在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过程,表现人在繁乱冷漠现实世界的挤压下产生的那种无力挣扎着的、痛苦绝望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真实心态。当然,诗歌中虽然有一些戏剧般的角色设置和情节设置,对诗歌的表情达意产生了一定有益的作用,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戏剧中的角色和情节。因为丰富的意象和意象强烈的象征意义仍是“诗”的特权,是其它任何体裁都替代不了的。
三、言说和抒情,戴诗戏剧因子之三
戏剧的表达方式是对话和独白,通过对话来交代人物、推进情节、通过独白来渲染气氛、抒发情感。戴望舒在诗中常常设置的对话与独白就是又一种戏剧因子的体现。他的《残叶之歌》,在结构上就很像诗剧的形式,直接用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及独白构成诗篇。雨后残春,男女主人公伫立树下,凝望雨后的枝头残叶,互道离别的心迹。第一节是男子的咏唱:“你看,湿了雨珠的残叶,/摇摇地停在枝头,/(湿了泪珠的心儿/轻轻地贴在你心头。)”在两句倾诉之后,又用括弧的形式表达他的内心独白,是那样的含蓄而有节制;第二节是女子的诉说:“你看,那小鸟恋过枝叶,/如今却要飘飞无迹。/(我底心儿和残叶一样/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括弧中的两行诗同样是女子的独白,她把自己比作残叶,用独白把微怨埋在心里;第三节是男子的表白“那么,你是叶儿,我是那微风,/我曾爱你在枝上,也爱你在街中。”表达了一种矢志不移的爱恋,男女主人公已经到了心心相印的阶段,于是有了第四节女子的倾诉:“来吧,你把你微风吹起,/我将我残叶的生命还你。”这两情相契、以生命相许的诗情,就通过戏剧性的对话和独白推向了高潮。
另一首《路上的小语》,其言说形式又有不同,全篇直接由少男少女的六段对话组成,虽然没有象剧本那样标明说话者,但能够清楚地辨别出男、女主人公的口吻。燃烧着火热激情的少男是一位主动出击,大胆的求爱者,在一、三、五节里他先是请求姑娘把“发上的小小的青色的花”给他做纪念,进而要求姑娘宝石一样的吻,继而又要求得到姑娘盛满爱情的心。姑娘则柔中见刚,冷中含热,面对少男的步步紧逼,始终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在二、四、六节中有针对性地逐层表明自己的态度。先说青色的花“到处都可以找到”,再说自己的感情还不够成熟,更“不给说慌的孩子”,接着强调自己的爱情要跟真诚的心交换。这首诗明显采用了“戏拟”的手法,选用对话来表达诗意,在反映诗人关于爱情理性思考的同时,塑造出了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戏剧性的对话元素使诗歌抒情具有了独特的效果。
《残花的泪》则是一首典型的独白诗。诗歌的前两句“寂寞的古园中,/明月照幽素”,犹如交代舞台背景。接着,一枝残花的独白构成了诗的全部,残花诉说青春已逝的感伤(我的娇丽已残,/我的芳时已过),回顾自己与蝴蝶之间的爱情经历(我的旖艳与温馨/我的生命与青春/都已为你所有/都已为你消受尽!),抒发蝴蝶移情别恋自己被抛弃的哀怨,并且预示了自己的悲剧结局(你会把我孤凉地抛下,/独自蹁跹地飞去,/又飞到别枝春花上,/依依地将她恋住)。运用“独白”这样的戏剧性言说方式,使诗歌具有了一定的叙事色彩,使情感的表达具有了间接性和客观性的特点。
戴望舒诗歌中蕴含的戏剧性因子,是其诗歌独特艺术质地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不仅有利于诗歌中角色的塑造,情节的展开,诗情的流露,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早期白话新诗中“直白”“滥情”的倾向,为我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探索性的贡献。
注释:
[1][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
[2]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39页。
[3]戴望舒:《戴望舒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赵燕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 0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