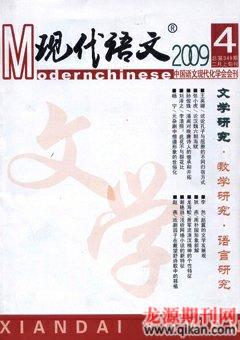关于《荷塘月色》的写作背景
苏 庆
摘 要:对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一文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归于政治因素,有的归于日常家庭生活的因素,这都是源于读者对《荷塘月色》写作背景的看法不同所致。如果客观地分析其写作背景,那么“颇不宁静”的原因应该归于作者面对的复杂社会现实和特殊的家庭现状。
关键词:朱自清 《荷塘月色》 写作背景 颇不宁静 政治 生活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散文,多年来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由于读者对写作背景的理解不尽相同,于是对文中“颇不宁静”缘由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对一些赏析文章的写作背景又有新的看法,分歧也比较大。目前,对“颇不宁静”缘由的看法,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类是完全归因于当时的政治;另一类是归因于日常家庭生活。如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到:“《荷塘月色》于良晨美景之中吐露心中的抑郁和‘不宁,折射出动乱的现实在知识分子精神上引起的忧思。”吴仕文主编的《中国语文多角度解析》中写到:作者的思想状态是‘对现实的不满,思想是矛盾复杂的”。这两种说法都归因于政治。而高远东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书》2001年第一期发表的《〈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让我发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一类观点,他认为:“与其把‘我心绪不宁的原因归于政治,还不如把它归诸这种日常家庭生活更为可信。”基于这一观点,“荷塘月色”添上了“爱欲境界”的色彩。前一类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一些联系,学者基本认同,教学上灌输的也是这种观点。而后一类观点与文章的语言表达有一定的关系,见解独到。但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某一方面,对此,笔者赞成高秀川在《功利性解读与审美的消渴》中的说法:“精神分析学有其文本解读上的独到之处,然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操精神分析之刀不加选择地解析所有文本必然误入歧途。”所以再认识《荷塘月色》的写作背景,有利于正确赏析此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于日常家庭生活。从文章上看,丝毫没有家庭日常生活引起的不愉快的痕迹。“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墙外马路上的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杉,带上门出去。”回来时“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家庭在这月夜里是何等的和谐和静谧:院里乘凉,墙外欢笑,屋内哼眠歌。“悄悄”、“轻轻”表现了作者对家人的体贴入微,哪像因日常家庭生活而引起的“颇不宁静”?如果是根据课文上多次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句子来判断或推测的话,一方面,它与事实不合。高秀川说:就在《荷塘月色》发表的同一天,朱自清作了一首旧体诗《凛凛云暮》,恰是以女性身份曲折地体察来自黑暗社会的威压,来自理想逃亡的迷茫,以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这正好是对“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真正诠释。另一方面,本文采用与女性有关的比喻,暂且别说是传统手法,就朱自清本人写景时也是常常采用的。如他在1924年写的《绿》中,是这样描写梅雨潭的:“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这难道也是“爱欲境界”?再看,引用《采莲赋》和西洲曲的句子,是因为看到眼前的景物而联想到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眼前的静寂、自己的孤独,感到“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他们,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人在此采莲那多好”,所以自然联想到以往一群一群的男女青年在湖里嬉游的情景和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朱自清才29岁,但在这个动乱的年代早已无福消受了,想到以往这些嬉游的无忧无虑的年轻人,让他到底掂着江南了——想起与自己和睦相处、志同道合的好友们,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根据“这几天”而并非“这几个月”来说明是因为家庭日常生活引起的“颇不宁静”,那朱自清怎么要在工作之余,回家之后,而且是在和谐的月夜里“悄悄地披上了大衫,带上门出去”?为什么感觉到“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感到“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所以他的“不宁静”来由已久,并非是这几天的事,而是“这几天”极度烦闷而已。
“颇不宁静”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当时的政治。理由是作家的复杂思想状况。一是来自于当时文学界的政治潮流对他的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促进了许多作家向无产阶级转化。1925年,蒋光慈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沈雁冰发表《论无产阶级的觉悟》,1926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更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郭沫若的文章,还向作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由于当时许多革命家、作家都先后参加了实际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配合无产阶级单独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式,在文学上也要提出鲜明的主张来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一部分动摇、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本身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参加反革命,作为一个作家该何去何从,思想上在作激烈的斗争。二是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想逃避。因为他亲眼目睹过“三·一八”惨案,之后的他感到眼前一片虚无,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血的恐怖面前无情的幻灭,无路可走,于是开始彷徨。写《荷塘月色》的时间是1927年7月,正是国家连续发生重大事件的历史时期。“四·一二”大屠杀刚过不久,5月又发生“马日事变”,6月底国共关系空前紧张,所以这种彷徨在经受1927年接连不断发生重大事件的撞击以后,变得更加严重。而写此文的这几天正是国共关系严重分裂的时候,“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即将爆发,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大地,黑暗的现实、紧张的政治气氛,犹如暴风雨来临前一样,让人沉闷,令人窒息,所以作者“这几天心里”感到“颇不宁静”。三是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想逃避而不能。作为一个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教授,他曾参加过“五·四”运动,耳闻“五卅”事件,目睹“三·一八”惨案。曾在1924年出版诗文集《踪迹》,内容多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也写出对光明和十月革命的向往。在1925年为五卅运动写了《血歌》,强烈控诉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26年为“三·一八”惨案写下了《执政府大屠记》,明显地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爱国作家看到国家动荡不安,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担心不焦虑国家的安危。四是他面对家庭现实的苦恼。他到清华任教才两年,举家迁到清华园才几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告别当东西过日子的生活,可是国家的不安又要影响小家的安宁,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对孩子的教育上,面对家庭的压力他都很苦恼。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当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妻又有身孕了,生活的压力,正如他1928年6月在《儿女》中所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之后又说“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靠我生活”,“还是暂时超然为好”。所以,面对国事和家事,看到革命作家们选择的道路,在1927年9月《一封信》中,把这种心迹继续表露:“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明白。”迫使他与多数文人一样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往哪里走?所以心里“颇不宁静”使他在夜深宁静的夜晚到荷塘去排解烦恼,这种烦恼延续到1928年仍没有得到解决。这年2月写的《哪里走》中仍流露出来:“只有参加革命和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避的一法。”“惶惶然”、“避”继续流露他当时的复杂心态。
综上所述,根据朱自清《荷塘月色》写作背景的复杂性,作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缘由,不完全是政治因素,更不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因素,而应该是作者面对的复杂社会现实和特殊的家庭现状,对民族危难的忧虑与个人处境的艰难所产生的复杂心态,表现出在彷徨苦闷中既想“逃避”、“超然”又想“挣扎”而不能的情绪。
参考文献:
[1]高秀川.功利性解读与审美的消渴[J].语文月刊,2002,(7-8).
[2]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267-272.
(苏庆 贵州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研室 55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