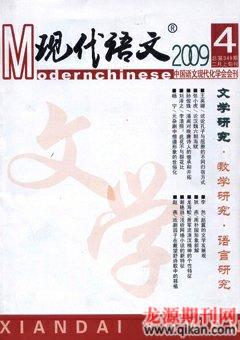元杂剧中僧道形象的世俗化
杨 宁
摘 要:元杂剧作品中的僧道(僧包括和尚、尼姑,道包括道士、道姑)形象不再飘然尘外、清虚自守、慈悲清净,相反他们有着平民百姓的情感和欲望,有着追逐世俗多彩生活的行为表现,甚至于沉溺在酒、色、财、气,人、我、是、非的欲望之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关键词:元杂剧 僧道 世俗化
戏剧艺术与宗教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关于中国戏曲发生发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今人早已有所论及。早就有学者指出,戏曲与宗教的产生都与原始巫术有关。具体到中国道教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戏曲发生发展的关系,康保成考证出宋金杂剧院本演出的最初场所“瓦舍”“勾栏”本意是指“僧房、寺院”以及“寺院中的演出场所”,而戏曲行当之一“净”角的本意也是指出家的僧人[1]。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僧、道在一开始就受到戏曲创作的关照,成为出现相当频繁的一个类群。在元杂剧里僧道人物空前活跃起来,处处可见其踪影,从而形成了庞大的人物群像,这些原本代表着宗教庄严、神圣、不可亵渎的人物身上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无论是天上的仙佛神灵,还是现实中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几乎全都丧失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神性品格,他们不再飘然尘外、清虚自守、慈悲清净,相反,染上了一种浓郁的世俗色彩,沉溺在酒、色、财、气,人、我、是、非的欲望之中,他们有着平民百姓的情感和欲望,有着追逐世俗多彩生活的行为表现,正如郭英德概括的那样:“戏曲中的神佛形象往往是人格化的,三分不像神,七分倒像人。”[2](P12)
一
神仙寄托着剧作者的情怀,神仙现身人间时,无不以凡人的形象出现:吕洞宾喜扮作“穷道人”或“白衣秀士”,钟离权好幻为“疯魔先生”;文质彬彬的是马丹阳,长歌短唱的是铁拐李。他们以人的形貌、动作、语言出现在舞台上,而且充满人的思想、人的情感和人的性格,正如吴梅在《词余讲义序》中所说,元杂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及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以《岳阳楼》为例,吕洞宾虽是神仙,但总是不能忘情于现实,第一折写他化作卖墨先生,登上岳阳楼:“端的是凭凌云汉,映带潇湘。俺这里蹑飞梯,凝望眼,离人间似有三千丈.则好高欢避署,王粱思乡。”这是人世书生而不是天上神仙的感情。剧中吕洞宾以墨换酒情节注入了强烈的对功名误人的愤慨[3]:“[后庭花]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带云]酒保也!(唱)则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肠,在这功名之上。”第一折中还写吕洞宾眺望江山,抒发兴亡之感:“[鹊踏枝]自隋唐,数兴亡。料着这一片青旗,能有的几日秋光。对四面江山浩荡,怎消得我几行儿醉墨淋浪。”沦落江湖的儒生,就像墨一样,而目黧黑,还要承受无数次的磨难。又如第二折云:“[贺新郎]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这种感性无端的歌哭笑骂,包含了强烈的个人情怀,悲伤事业,感叹雄才,一生的壮志化为轻烟,如同往昔的英雄一样不复存在。
再看《黄粱梦》杂剧中的钟离权,表面上虽然一再表示信仰“玄虚为本,清静为门”,似乎淡泊无欲、超然物外,追求“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汉,甚的秦”的神仙境界,但同时又耿耿于怀于“假饶你手段欺韩信,舌辩赛苏秦,到底功名由命不由人”,愤愤不平于“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只敬衣衫不敬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神仙们对于功名利禄、对于自身的社会价值,非但不能超然,反而渴求:而其所谓无欲无念、清净自守的表述,不过是渴望功名而不可得的变态心理的抒发。这种神佛形象,和宗教经典中忘怀世事,心如止水的神佛形象,有着本质区别,显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二
宗教之所以与一般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同,就在于它有神圣的一面,对宗教徒而言,这种神圣的力量和超自然的现象是不能发生怀疑的,因为它们来自于神的启示,是永恒的存在,由之而宋的那些宗教仪式与宗教思想也都具有神圣的一面,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与宗教有关的现象,是不能做出轻易地改变,更不能去放弃!元人张圭的奏议说“僧道出家,屏绝妻攀,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摇役,且处官寺,宜清净绝欲,诵经祝寿。”[4]可见元时对出家人有一系列的清规戒律。但在元杂剧作品中却不乏那些为追求世俗享受而喝酒吃肉、贪财势利、思凡恋世、作奸犯科的出家人形象,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及理想追求都呈现出浓厚的世俗特色。
首先,他们践踏清规,喝酒吃肉。喜好酒肉,几乎成了元杂剧对出家人进行描写的一种基本模式:《裴度还带》中,净行者所谓的斋饭是“小葱儿锅烧肝白肠。”《昊天塔》里的和尚自我表白道:“我做和尚无尘垢,一生不会念经咒。听的看经便头疼,常在山下吃狗肉。”《蒋神灵应》的庙官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这样精彩的介绍:“大人去了也。小道无甚事,捣蒜吃羊头去也。我做道官爱清幽,一生哈答度春秋。捣下青蒜酷下酒,柳蒸狗肉烂羊头。”《留鞋记》中的和尚自我介绍道:“我做和尚年幼,生来不断酒肉。”《圯桥进履》里的乔仙则似乎更喜好狗肉:“施主若来请打蘸,清心洁静更诚坚。未曾看经要吃肉,吃的饱了肚儿圆。平生要吃好狗肉,吃了狗肉念真言。”《度柳翠》中的那位月明和尚,更是一个酒肉不离口的十足滥僧:“[行者云]我教你做好事。[正末云]你几曾做那好事来?我问你,那里有酒么?[行者云]人家做好事,那得有酒。[正末云]有酒我便去,无酒我不去。[行者云]有酒有酒。[正末云]那裹有肉么?[行者云]我说道做好事,那得肉来。[正末云]有肉我便去,无肉我不去。[行者云]有肉有肉。”作为出家人不仅犯戒喝酒吃肉,而且还把要酒要肉作为做好事的条件相要挟,活脱一个世俗小人的形象。
其次,他们贪财势利。《桃花女》中的北斗星官。当彭大依桃花女之计,“办些素果斋食,香花灯烛”,乞求北斗星宫延寿时,七位星官果然心安理得地接受并享用了这些祭品:“今夜吾神当降临凡世,纠察人间善恶,来到此处。不知什么修善之人,虔心敬意,安排下七分香纸花果,明灯净水,接待吾神,合该领受他供养波。[做拂袖科,云〕吾神去也。”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神仙们既然受用了彭大的香灯祭祀,当彭大跳出来讨要阳寿时,星官们替他勾抹该死的册籍也是理所应该。在这里,神仙的赐福变成了与世人的一种交易。《圯桥进履》里的乔仙为了财利甚至于“等的天色将次晚,躲在人家灶火边。若是无人撞入去,偷了东西一道烟。盗了这家十匹布,拿了那家五斤绵。为甚贫道好做贼?皆因也有祖师传”;“家住在深山里头,好吃的是牛肉羊肉,闲来时打家截盗,剜墙□窟,盗马偷牛”。这里的神仙全然没有了他们的神性品格,竟然为了财利去做贼,甚至于还恬不知耻的叫嚣做贼有祖师传。他们不再飘然尘外、清虚自守、慈悲清净,反而比世俗社会的人们更加势利、贪婪,世俗性更浓。
第三、对于世俗情欲,他们更是不能舍弃。无论在佛教还是道教,修行者抛弃世俗情欲,彻底断绝淫念,都是一条起码的戒规,但是,元杂剧中形形色色的宗教形象,却鲜能遵循这条戒规,更多的表现为思凡恋世。如《鸳鸯被》里的小道姑一见小姐就说:“我与你将鸳鸯被儿都铺停当了,则等你来成就亲呵,你休忘了我者……我今日成就了你两个,久后你也与我寻一个好老公。”《竹坞听琴》里的女主人公郑彩鸾,本是着急嫁不了好男人才出家的,一旦与指腹为婚的秀才庵堂相遇,怨女旷夫,“并香肩月下星前,共指三生说誓言”,“我不再绽口念着道德经。坐处坐行处行,情厮投意厮称。到今朝酒半醒,入罗纬掩乡屏。只等得画烛灯昏夜寂静,宝篆氤氲金鼎。枕头儿上那些风流兴,休道俺姑姑们不志诚,便跳出那八洞神仙把我来劝都不省。”小道姑眼见得郑小姐有了好人家,便伤感地说:“小姐还俗去了也。撇得我独自一个,在此孤孤另另,如何度日,不如也寻个小和尚去。”而老道姑一见多年前失散了的老公,说一句“我丢了冠子,脱了布衫,解了环绦,我认了老相公,不强似出家”,立马还俗。《女贞观》中的妙常也是一个敢于追求幸福爱情的年轻女尼,她虽身在冷清的道观,心中却常“暗想分中恩爱,月下姻缘,不知曾了相思债”。因此,面对着风流书生潘必正的试探与勾引,她出于少女的羞涩假意拒绝。在潘必正的热烈追求下,爱才怜才的陈妙常最后陷入了情网之中,庄严的禅房成了他们恋爱的桃花源。
更有淫滥粗鄙、作奸犯科者。例如,《合汗衫》相国寺里的那位主持长老上场诗云:“莫道出家便受戒,那个猫儿不吃腥。”《留鞋记》中相国寺的殿主自我介绍道:“我做和尚年幼,生来不断酒肉。施主请我看经,单把女娘一溜。”《西游记》中,孙悟空未被收服前,即相当好色,娶了美丽的金鼎国王女为妻。唐僧在女儿国国王热情的追求面前,表现得相当软弱无力,只是一味地说“我是出家人”请“孙悟空救我”。只是由于韦驮尊者的帮助,才没有“几毁法体”而孙悟空本想风流,却因为“头上金箍咒儿紧将起来,浑身上下骨节疼痛”才没有成其好事,而“猪八戒呼呼喘,沙和尚悄悄声,上面的紧紧往前挣,下面的款款将腰肢应”,唐僧也并不责备他们。这些描写,都使出家人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们那淫滥的丑恶嘴脸。为甚贫道好做贼,皆因也有祖师传。《勘头巾》中的王知观为了世俗情欲竟然不惜作奸犯科:“[净云]少说少说,杀了刘员外也是我来,和他老婆通奸也是我来。除死无大灾,饶便饶,不饶把俺两口儿就哈喇了罢。大嫂,我和你到阴司下,又无人管,正好的做一对儿美满夫妻,可不自在。”这番话语,将他那淫邪、无耻的流氓本性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元杂剧中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宗教形象—无论是上界己得道的仙佛,还是凡间正在苦苦修炼的宗教信徒—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世俗色彩:大凡世俗凡人所具有的人情和恶习,如贪财、势利、不能舍弃世俗情欲,等等,无不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很明显,这样一种形象特征的出现,同元代的宗教教状况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宗教特性:浓郁的世俗精神、多神崇拜观念、三教合一思想、“惟灵是信”的信仰原则对元杂剧深刻影响的结果,当然也与元杂剧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
注释:
[1]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2]郭英德:《世俗的祭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3]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韩儒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杨宁 驻马店 黄淮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4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