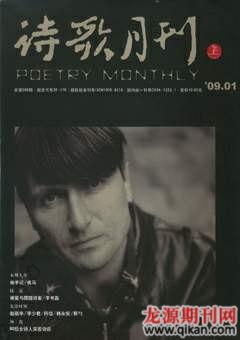亲人谱(组诗)
徐俊国
一个人的三月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潮湿的树桩上
不是读书写诗思考关于腐朽的问题
我想知道一个被砍掉了梦想的人
会不会重新发芽
春暖花开的日子鸟叫也是绿的
需要多少忏悔才能磨亮生锈的誓言
需要多少祭品才能赎回洁净的时光
多少人还在弄脏自己
多少人用曙光清洗一夜的罪责
三月坐在潮湿的树桩上
我看见河流哭着奔向大海
它发抖的缰绳牵着我像牵着知错的豹子
亲人谱
二月耕地看见菜籽要生根
三月修剪桃枝和长发听说燕子要出嫁
七月摇扇子熄灭蝉鸣与肝火
八月割苇十月收谷
白天用太阳夯路基
晚上用月光洗皱纹
我在花蕾中写诗
爱人在落叶中生下双胞胎
风一年年吹
雪一年年下
亲人在变白
时光在变黑
一群佝偻着身子的人头挨着头
用节省下来的泪光给病婴的啼哭照明
失败者
在一群拿着柳条和瓦块的人面前
我是永远的失败者
他们把我的小木枪扔进大沽河
让我目睹自己7岁的自尊被流水冲走
许多次他们逼我在淤泥中爬行
我越陷越深
为没能保护好母亲给我洗净的白衫而啜泣
在青一阵紫一阵的暮色中
我向爱我的那个女孩跪下
抹着鼻涕一遍遍说对不起
她像一位遭受羞辱的公主
愤怒地踢了我一脚
转身消失在1978年的甘蔗林中
留下一个失败者
把舌头嚼出血来
我所理解的死
肉体落地灵魂终于松绑
小鸟飞翔灵魂要回家
如果一个人活了二百岁
就等于肉体耽误了灵魂二百年的路程
死肯定还有别的意思
原谅我只说出这些
回故乡
第一趟回故乡
村长家的樱桃树被雷一劈两半
里面露出一只黄鼠狼
第二趟回故乡
大绳媳妇生了一个没有手脚的肉元宝
自从我听说
憨六子想用藤条勒死他瘫痪了六十年的亲娘
再也没敢回故乡
梅蹄湾
在鹅塘村蔚蓝的天空饱含雷雨麦芒泪斑沙粒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梅蹄湾都像一个埋在时光里的破翁
东西长一百八十二厘米南北宽一百五十七厘米
深的地方睡着千年老鳖
浅的地方看得清红鲤或白鲢的小心脏
春天准时来临毛白杨准时扬穗
毛茸茸的小棒槌垂直落下敲碎水面的平静
白花花的阳光一圈一圈散去
它的荡漾往往波及晚清的贞节烈女沤烂的手帕
和淤泥中下陷的铜耳环
每次回故乡我都要沿着梅蹄湾走上九十九圈
用柳枝在地上写着乳名
高一声低一声地唤回八岁时不慎淹死的魂魄
母亲却安慰道“城里人命硬不会再丢了”
但这些年我依然活得恍恍惚惚
常常半夜惊起虚汗涔涔
是花椒炒蛇皮再用烈酒和处女血浸泡
还是蜂蜜涂苦胆七月的雪花擦洗乡愁的脐带
我病得很重一直找不到根除的药方
炊烟里的谷神
炊烟里的谷神随风巡逻
他肯定能看见我和牛在荒草滩劳动
天已经很晚了
我必须赶在猫头鹰哭泣之前把粪肥耙匀
稍等月光也会凝霜
我的牛累了
它忍着嘴里的白沫努力想跪起来
谷神俯身人间咳出一阵急雨
隐秘之爱
有一些话说出来也无人听懂
有一些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发生
老虎的脑子里藏着暴雨和彩虹
我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有一个爆破手
把导火索缠在迟迟没有开放的花骨朵上
哑孩子抓起一把雷声塞进耳朵
抱着被割掉舌头的羔羊号啕大哭
一只蚂蚁跑累了
它扑腾一声跪在蝴蝶的花裙子下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多么爱你
爱你的翅膀爱你飞累的一生
八万五千公里沧桑”
我握着钢笔写着写着就写到了幸福的最后一笔
血管破了 老处女哭了
泪水漫过纸张 又漫过童年的眠床
一点点逼近爱情的老心脏
代替
走近了才发现
头围黄丝巾腰扎红腰带
穿着这件咖啡色女式风衣的
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
在杭州路与红旗路交叉处
他停了下来
从怀里掏出一个白馍半瓶酒
一叠冥钞和打火机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
穿着亡妻生前最爱穿的衣服祭奠亡妻
亡妻肯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她飘在半空
肯定会看到依然活在尘世的自己
他代替她活着
代替她走没走完的路过没过完的日子
在一个破落的小院子里
在一棵果实落尽的柿子树下
当他替她织完那件粉红色的毛衣
他对着水缸试穿了一下
忽然呜咽道——
老婆我想你哇
最后一首诗
没有什么可给的了
灵魂喂养大的所有马匹
都牵给你们了
只剩下这日益变短的铅笔头
百年之后
它也将写不出天空的蔚蓝大地的荒凉
还有这唱了一百遍的《故乡辞》
你们早厌烦了
没有什么可给的了
如果你们还嫌不够
就把给我做墓碑的那块石料
捐给齐鲁大地上任何一户农家
可以铺地基
也可以挡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