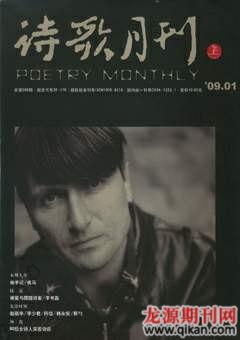侯马访谈录
中 岛
中岛:侯马你好,创作长诗《他手记》,你经历了四年。我在读《他手记》的过程中发现:《他手记》所表达的普通人的细节生活非常多,这种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细节的呈现,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在其他诗人的诗中,是不容易看到的,这也是《他手记》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你是如何进入这种生活状态中的,你又是如何来创作《他手记》的?
侯马 :你一开场就把我的思路打开了。严格来讲,《他手记》创作没有四年,从开始创作到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传播的局面,大概有四年这么长。实际上从开始写《他手记》到《他手记》完稿,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我查了一下,(侯马从皮包里拿出二个小皮本放在桌上)这是原始的,用来创作《他手记》的两个棕黑色的小皮本。一个最早的,2004年12月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开始动笔的,是从昌平回北京的路上,产生了这个念头。实际上,2007年夏天,确切地说是六月的一天,结束了《他手记》的写作,那天也是你去官园看我的时间。
我想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写《他手记》,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原因还是跟“盘峰论争 ”之后这种创作的环境有关系。可以说,在99年的“盘峰”之前,严格讲,是89年开始,我就比较自觉地开始了现代汉诗的创作,89年之前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是一个诗歌学徒,是一个鉴赏者,是一个阅读者。89年以后有了这种自觉的意识,也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寂寞的写作,但是也深深地陶醉在其中。我在很暗的地方,这个过程应该有十年之久。从作品流传这个角度上讲,起码有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写了一些比较像样的作品了,但是得不到传播的机会,也就是偶然的那种不平感。更常有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一想起来自己写出的那么多的诗歌,还算是满意的作品,虽然为外界所不知,但还是感到非常的充实。当时我有一个比喻,有一点像太平洋孤岛上的乌龟,整天躺在那儿晒太阳,特别的自足。很孤独,但是也很自足。可是“盘峰”之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是作为新锐,作为青年诗人,被埋没以后,推出来的局面,作品引起一种广泛的关注。
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再这么写下去有什么意义?你觉得写什么自己都难以容忍,重复自己更难忍受,而且觉得以前写的东西可疑。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人批评我,说侯马写来写去写不透,不由得会心一笑,这人说中要害了。怎样才会有一些崭新的表达,当时确实成为一种困惑。一直持续到2002年,也就是到荷兰去以前,这个阶段也写了一些诗歌作品,包括《九三年》都是这个时候写出来的,但是总体上作品量不大。出国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沉寂期,基本上没有动笔。但是,我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思考的人,就是脑子不停的在那儿转,在那儿想,所以到了2004年年底,我突然意识到,我脑子里日思夜想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好像就是这个事,本来是一个明摆的事,但是确实就没有想到过,也没有受到什么样的触动。我就决定把这些,经常想的东西,记下来,而且我瞬间感觉到这是特别适合我的创作状态、思考状态和我诗歌追求的一种诗歌创作方式、诗歌体例,可以说是爆发了。
这里面,一个是因为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很难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来营造那样一个心境,去写下一首单独的作品。那我这个手记,时间是片断的,作品一条一条的,这跟工作跟生活不矛盾。实际上大量的这种作品都是在路上,在开会的间隙,甚至有时候在饭局中,随手就在本子上记下来了。我也专门用了这样一个本,你看这个本,这个本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合带在口袋里。可以说这几年以来,我都随身携带着这个本,我有可能忘记带身份证,忘记带钥匙,忘记带钱,但是我不会忘记带这样一个《他手记》的创作本。写完了一个,用另外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同时,我也感觉到我这种状态,永远是思考的状况,实际上,是在提供了一种很客观的立场,就是旁观者的立场。仿佛我在生活,又有一个我在看着我,所以有一种强烈的第三者立场。“他”这个人物,这个形象就诞生了。他就是我。沈浩波在一个访谈中很敏锐地指出来这一点,并且说只有感觉到他就是我的时候,手记的作品才更有冲击力。策略地讲“他”也是提供了一个伪装,更真实地解剖自已,涂了保护色。但是就算他是我,也绝对不是一个具体的我,一个照搬的我。也恐怕是一具有同时代人的立场,具有历史发展观的这种我。也是一环,一个环节当中的我。也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我的爱人和敌人,甚至是通过我看到的芸芸众生,毕竟是在我的脑子里反映的。“他”把我的诗激活了。同时这个手记,这种体例,手记一条条的记,也是强调人的色彩:诗是用手写出来的。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说他——手记,也可以说是他手——记,这个诗不是我的手写出来的,是他手。我假借他人之手,或者诗神假借我的手,或者是上帝假借我的手。总而言之,这个话题说到这儿,明确的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场者,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当下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我要代一代人,首先代我自己,“活着,感受以及表达。”(早期诗集《顺便吻一下》序言标题)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代表人类的一个活法。这也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真正诗歌的源头在哪儿?就在你自己。这样一个创新怎么来?创新就在于当代性。
中岛:你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比如说你的很多生活,你看到的很多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内容和感受是可以入诗的?
侯马 :我觉得,实际上什么都可以入诗,简单来说,怎么去选择,我主要是呈现 “不一样”的表达。尽管不一样,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个色的,不是很张狂的那种,他那种咄咄逼人是用亲和的语气说出来的。这是对真实无限的,带着怀疑的眼光寻求真实的过程。我对于一个事物,对于一个事件要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话,恐怕也就是那个什么了,恐怕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中岛:在读《他手记》的时候,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在读的时候,都说他们在你的诗歌里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生活真实,这是一种亲近感和记忆感,里面的很多元素都是十分具有时代特征的。因此我认为,评判一个诗人,就要看他诗歌的内在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诗歌非常简单,非常细致地体现了诗歌的价值所在。读其他一百首诗,可能都没有感觉,没有一点生活内容。而你的诗完全来源于生活,体现那种生活的细节,并且用诗性的光芒来打磨,而这种光芒一旦触到了读者的心灵上,就会有深刻的共鸣。你的这种诗歌创造方式非常的独特,我觉得你应该谈谈这个问题,这些是你诗歌文本价值非常大的地方。
侯马 :这里面可能有几块。比较多的,很大的一块,是童年的经历,这可能很多评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童年发生的事情,已经经过了漫长的三、四十年,你没有忘记。而且在你后来的生活当中,随着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你对童年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你经历那么漫长的时光,你刚刚明白,那个时候所具有的价值,刚刚明白那会儿具有的诗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刻骨铭心的。而且这些原型,这种模式都在里面了。这一点是我涉及比较多的一块,很大的题材。应该说咱们中国人,太蔑视儿童了。所有这些都是刻骨铭心的,原来这些事情我自己并不知道记不记得。也可以说是诗歌唤醒了这些记忆。有的事情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记得的,可能在生活中受到一个触动,瞬间就想起来了。我的儿子夏尔的许多言行就让我突然看到童年的自己。就是这种原型,写诗。
还有一块,实际上是情感上的冲突。作为今天的你,作为一个欲望的人,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每个人尤其面临的就是这种冲突。虽然说人生活在各自的时代,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带来了这种变化太深刻了,这种变化太大了。我不知道,可能1860年后,那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建国前后,那个时候价值观念可能冲击的大一些,还有一个什么历史时刻,这么大一个冲击。所以今天你作为一个人活着,好像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实际上变得更艰难了。这种冲突聚集到个人的情感上,个人欲望上,个人功名利禄之心的波澜起伏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诗歌的所谓的自我教育,诗歌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诗歌是一种信仰,我想主要是这个意义上的。
还有很大一块,就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觉得,我尤其有责任去写这样的诗歌。因为我没有更多创作时间,不能像其他的同行一样,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诗歌,去研究诗学。据我这么几年的观察,我觉得像诗人伊沙、徐江他们,我的老朋友对诗歌的这种敬意之深,对诗艺的这种苛刻、自律前所未有。他们的贡献是历史性的。许多优秀的诗人,使诗歌在当代非常有尊严,有品质,表现出很不“当代”的高级。
但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我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面,要反映出我没创作的时间,社会、人生的痕迹,就是其余的时间我不能白活了。而这个,是其他的诗人很少接触的。因为工作原因,我对社会的观察,理解,真实之处,隐晦之处,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的接触。所以我要把这块呈现出来。我想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块。这个绝对不是怜悯,也不是草根,你对他们了解的深了,或者这么说吧,当你发现自己完全置身其中,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你就明白你是注定的,你认为没那么高贵的血也流在你的血管里,你的口音里面有祖先,也有乡亲们。这可能是一大块。
还有一块是对诗学的研讨。因为我们文学史的观念都很强烈,不是说先写作,先选择写作这种职业或命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多是对文学有很深的一种修养,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和教育之后,自觉的投身的。所以带着这样背景写作的人,这种文学史观,就比较强烈一些。所以说,我在创作当中,用诗歌来钻研诗歌,用诗歌来探讨文学艺术,这是很大一块。所以有很多诗歌实际上是创作观,是诗学,但是是用诗歌的手段来表现的。所以基本上大的分类就这几块。
中岛:长诗《他手记》的发表,包括《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十月》,《十月》也获得一个奖。但很多人都不能体会到你在创作时内心的一些认知高度。你写家庭的也好,写兄弟也好,写感情的也好,写残酷的现实生活也好,也包括写情绪的,我体会其中有很强的人文色彩。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他被时间用完了:再给一秒钟,他就可以点燃一只香烟……”时间用完了,没有了时间。但是如果给我一点时间,还能点着一支烟,这种内心的表现,能说明了什么?
侯马 :这首我有印象,这个是写死神拿走了他的最后一秒钟。如果给他一秒钟的话,他还能点亮一支烟。就是对死亡的一种研究吧。死亡的话题,就是说不到了一定的时候,是很难深入研究地。不知死,焉知生?死亡是非常重大的话题。
中岛:这种感觉是很有诗意的感觉,诗性的感觉。它表达的是内心的什么东西?仅仅是死亡吗?
侯马 :主要还是死亡。是死亡、是尸体,是那些烟。实际上这个诗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就是蹲在立交桥下的尸体,瞬间一个活人成为一具尸体,实际上这个东西对我的触动更大。
刚才你说到获奖发表的情况。我最满意的发表,就是在《诗参考》上的系列发表,我觉得诗歌有它的缘分。《诗参考》23期发表《他手记》第一辑,这是05年末的事,24期发表第二辑,这是06年末的事,那么07年末,25期,就把第三辑、第四辑全部发出。就等于说,我的《他手记》全文在《诗参考》上都登出来了。任何一个刊物,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说民刊生生不息,为什么说好诗在民间,因为跟信仰有关,跟良知有关,跟责任有关。
最早也是你坐公共汽车到昌平那么远去取稿子。应该说这个事情也是触动了我,所以我才拿回来了。拿出来以后,加速了后面《他手记》写作的密度,提速了,再有一些反馈,也对《他手记》的写作有所调整,也都渗透进去了。
《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最后是《十月》,在2007年同一年,先后用了较大的篇幅选发了《他手记》,我非常感激这样的眼光和勇气。《他手记》不是人人喊好的货色。我新听了一个词叫煤层气,能源的未来,大概类似瓦斯吧,会爆炸的毒气,但是收集起来就是宝贵的能源。《他手记》也有毒,通过适合的传播管道,不同的肠胃能吸收各自所需。
中岛:实际上,你的这种写作和思维的方式,很震动人。作品中有一种对人的打压和磨砺,特别大的冲击着读者。这种创作,在某种程度,肯定有很高的一种写作技巧,很独特的艺术观,这不是一般的诗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你能否谈一下这个方面感受?
侯马 :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这也是一个创作观的变化。可能过去太注重单首作品的推敲了,好比一个匠人要精雕细刻出一件艺术品来,就打磨它。现在有点像创立一门武学一样,要的是通透感,要的是连贯、气,所以可能就是说,现在谈起创作来,更多是讲它的整体,如果要分到一个具体的作品,我更愿意用诗来说话,《他手记》有480首,最后结集出版的时候,这个数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这480首诗歌,我觉得都是平等的,全是用“他”这样一种强大的视觉力量,强大的人性力量,强大的语言和构架能力去贯穿这个东西,打通了一个东西。我更愿意这样去看待这些作品。
中岛:在我记忆当中,还有一首写用鼻子来闻臭鞋的诗,那么在生活当中,这样的生活场景是不能入诗的,很多诗人感觉也是这样。还有一首诗,写关于孝顺不孝顺,就是大脚拇趾长还是二脚拇趾长。我觉得你的这一类诗,就是别人不敢去写,但是你能够写出来,写出来看了又挺舒服的,这种诗可能最经典,我觉得很经典。你写了很多龌龊的东西。
侯马 :我也追求这样的视角,不要被文化的,观念的,约定俗成的东西遮蔽,努力在最不经意的事物中提炼这种又悲又喜,让你陶醉、迷恋,但是又冷峻,让人有距离感,错综复杂的感情、感觉。我觉得这也是现代诗的一个特征。我比较注意突出的去辨析这些东西。
中岛:《他手记》中有一首传播非常广的诗《哦,雨加雪》,有些读者包括我都一致认为,可以进入中国诗歌历史以来最好的100首诗之列。在阅读中,我们会跟着你的生命情绪走,并且与你深度的矛盾内心发生交流,像在场,像观看,看你的痛苦、你的焦躁、你的失声和你莫名其妙的身体的舞动,潇洒而又凄凉,愤怒而又矜持,这种生命交错的行为心理和放荡自如的表达,也充分体现你压抑的情感内心正处在强烈的爆发的状态中,这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人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因此这种共鸣是不言而逾的,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这首诗的?
侯马 :实际上雨夹雪比较传统,不是很典型的他手记风格。总体说来,我在他手记中追求涩,追求不动声色,以显厚实和意味深长。而雨夹雪非常流畅、喷薄,确实是爆发,写的时候一气呵成。这首诗我什么情况下完成的?就是你说的压抑情况吧,冷热交加地抒了一把情。
中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必谈不可,回避不了。就是不分行的形式问题。我注意到,《他手记》最早网上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传播过程,《新京报》登后,网上有一些引用,也有一些评论,刚开始的时候,评论的人不多,置疑的人不少,主要是置疑这种形式。
侯马:这种形式也是我有意的,可以说是对那些年创作那种诗的风尚做的一种抵抗。诗意荡然无存,只剩下分行。所以我说,决定一首诗是不是诗,它最重要的东西,是有一个诗的本核,诗的核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写诗核,如果别人是在写糖水,我连糖都不写,我就写糖精,我要提炼糖精,甚至都不是糖精,是糖核弹,我要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分不分行,你可以放到脑子里去分,你随便怎么分,它都是一首杰出的诗。不分行增加了诗歌的难度,就是强迫自已回到起点,你必须是一种本质上的诗,才能构成一首诗。
这点是我一个刻意的追求,但是也是跟当时的时尚,相对抗的一种态度。应该说其实放在一个大背景,又过了这么几年,这个也不是说特别的必要,也不是说我就不分行,没关系,重要的不在这个。还有一个技术因素,我觉得挺有意思,当我在公共场合,比如在开会的时候,拿个小本,在那儿一句一句写的时候,如果不分行,还更象做记录,你一行一行分,一看就是开小差。所以我觉得不分行的东西更少让人脸红。这个我觉得是很愿意做一个说明。
中岛:你写的不分行体诗,现在有很多人模仿你这种形态,这种形式去写,你的这种诗歌创造,是不是对中国的诗歌发展具有一定的深远的文本意义?
侯马:没那么严重,也只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样品吧。应该说,这种写作方式的人自古就有。夏尔小时候不会打字,乱按键盘敲出了一段不知所云的文字,他说那是《论语》。文无定法,诗有别材。互相学习吧,我重视的是互相学习的人。
中岛:实际上《他手记》也进入一个诗歌的体系,你那种写法,现在也是一种诗歌的新体系了。
侯马:嗯。
中岛:你从语言上谈谈你的创作吧?
侯马:语言我追求清晰,有力。清晰就必须准确。准确极难,不可能做到,只有写出了内在的深刻矛盾,才能最大限度的接近准确。简单而深邃,复杂而清晰,这样的准确性还要求一种可被阅读的质感,所以我觉得我总体上来说,还是口语。但属于千锤百炼的口语,精雕细刻的口语,雅词、生僻的词不避讳,俚语俗语皆入诗。我下意识地用了很多山西方言,但是这是可被感知的,不是去卖弄。这样的口语与精神和品质骨肉相联,就叫新口语吧。口语不能太白了,但是也不能让人不知道说什么。让人不知道说什么的东西,我不反对,关键是作者本人想清楚了没有,不能用语言的模糊和歧义来掩盖认知的含混。语言上的追求大体上是这样,我自己感觉我不是一个语言特别有天赋的人,我说不清语言上的事。
中岛:那你还不是说清楚了吗?
侯马:把语言说得那么悬而又悬,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份,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中岛:从你现在来讲,你对你的诗歌,认定你的诗是一种新口语。这种新口语和口语是怎样界定呢?
侯马:我说不能把语言说的太悬,但也不能简单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口语简单化。这与这个词的世俗意义带来的浅薄有关系。这是从潮流上讲的。我觉得如果就叫口语的话,自己也标榜口语,追求口语,恐怕不自觉地你会限制你的语言范畴。不能放弃语言的追求,不能轻易地放弃,不能简单的只用一个诗意来取代一首诗,只用一段叙述来替代一首诗,涵盖自觉的语言追求。把人性想明白不是想简单,观念极端化不代表真正的力量。想诗想多了,想来想去也还是想语言,语言的品质就是诗歌的品质。
中岛:《他手记》把大题材形象化了,把平白的语言专业化了,把诗细节化了,那么多光彩的片段。
侯马:“一地碎银子”(报人黄集伟语)。你说的那个大题材,我愿意理解为精神追求。我对精神这东西有点耿耿于怀,大概文以载道的意识还比较强烈。特别是诗歌对于国人,当然是首先对我自已,现代精神的塑造,义不容辞吧。传统精神如何现代化,人性、人权、人的尊严这种新价值观如何确立,是《他手记》的底色。我不刻意表达政治正确和伦理正确的原因,不是惧怕先锋的歧视,是因为通常那更难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我追求正直的诗歌,诗歌的正直是本质的正直,是人类的精神之“铀”。
中岛:你讲得比较精辟。从你这块来讲,你说这个,突然引来一句话,包括我,也包括有些人,觉得《他手记》,不可替代的在20世纪的这个历史阶段,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一段心灵史,一段诗史。从现代诗歌开始到现在,《他手记》也会列入其中的著名作品之一,你对这个怎么看?
侯马:如果这首诗没写好,就赖我,赖我水平不高。作为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这几年我的思考我已经做完了,做得不好也就只能对不起这段历史了,也就这样了。我希望我以后有更好的更深的思考,带着今天的这个遗产,在明天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杰出的表达。
(《他手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